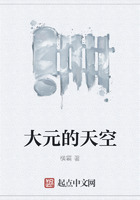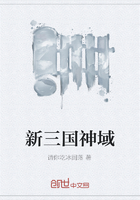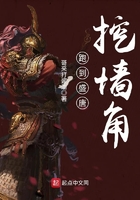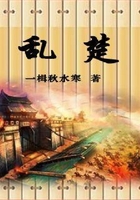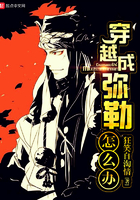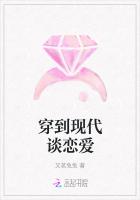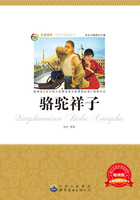■拜根兴
安史之乱后,随着唐中央政权的衰微,其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隔海相望的新罗国,却一直和唐朝维持藩属友好关系。关于此一时期唐朝和新罗的交往,学界对入唐新罗使者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对唐朝前往新罗的册封、吊祭、告哀诸使虽亦有涉及,但对现存中韩双方史料差异,唐朝赴新罗使节的行次及在新罗的活动,出使前的准备事项及唐廷对出使者采取的政策,以及运用新发现的赴新罗唐使者墓志资料诸方面,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笔者以为,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可以补充上述研究中的未备之处,并有助于了解唐中后期与新罗关系的各个层面。
赴新罗使节关联史料考辨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的唐中后期,应当从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的代宗大历年间开始。据中国侧史料记载,唐朝最后一次遣使赴新罗为会昌元年(841年),使者为归国新罗官僚,前入新罗宣慰使、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但韩国史书《三国史记》却记载了唐朝灭亡的前一年,仍派遣入唐新罗人金文蔚,册封已继位十年的新罗王。就是说,从唐代宗大历初到唐昭宗天祐年间长达130余年中,唐朝先后遣使22次。值得注意的是,现存中外史书对一些使者出使的时间、出使缘由等问题,要么记载存在差异或抵牾,要么对新出现的金石墓志注意不够,故很有考辨论证的必要。
宦官武自和出使新罗的时间。武自和,其事迹不见于《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卷六六九有相关记载。据墓志铭文所载,武自和元和年间曾担任福建地方监军使,返回朝廷后为殿前内养。可能在唐穆宗篡位过程中起过作用,因而“赐绿衣,官授登仕郎,内侍省内府局丞”。关于武自和出使新罗,墓志铭文没有说明出使的时间,但其中有“至宝历三年,文宗嗣位,选充山陵修筑判官”。而且,其出使名目为“奉诏充新罗宣慰告哀等使”。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武自和出使新罗在宝历三年(827年)之前。其二,其出使是向新罗传达唐皇帝驾崩的消息。宝历二年十二月唐敬宗卒,从时间推算,武自和不可能很快往返新罗。所以,其出使新罗只能是唐穆宗或唐宪宗驾崩之时。从墓志铭记载看,宪宗死后,武氏被任命新职,似乎前往新罗告哀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样,其出使新罗唯一可能就是在唐穆宗死后,即长庆四年(824年)。另外,《册府元龟》卷六六九记载了武自和随同另一宦官吐突士昕前往新罗取鹰鹞事件,而且确定出使时间为宝历二年(826年)。这里可能会产生疑问,前面界定的长庆四年出使新罗是否和这次出使为同一次?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一,墓志铭中明确记载长庆四年出使为“奉诏充新罗宣慰告哀等使”,而且按照此前惯例,唐皇帝驾崩,需要向藩属国新罗传达消息。其二,如果真是取鹰鹞,墓志铭文中却写成宣慰告哀等使,虽然是在出使十余年之后,但出使新罗,返回被流贬的事实朝野共知,墓志铭文撰者“将仕郎试太子通事舍人张模”不可能对此置若罔闻。笔者认为,正因为长庆四年出使新罗得到好评,武自和其人也可能大谈在新罗的各种见闻,喜欢玩耍的唐敬宗才会再次派他与吐突士昕赴新罗取鹰鹞。当然,返回时朝野政情变化,唐敬宗被杀,宦官中新一轮倾轧开始,两人因所属原宦官集团的失利,其被流贬也是可以想象的。至于墓志铭文中谈及宝历三年(该年二月改元太和),武自和被“选充山陵修筑判官”,当是被重新启用。从记载中可知,吐突士昕被流配于洛阳附近的唐高宗太子李弘恭陵,武自和则是在长安“配南衙”,两人处分的轻重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宫闱扃令充阁门使朱朝政出使新罗的时间。同样,朱朝政其人不见正史载录,他的事迹只见于其母亲赵氏墓志铭文。墓志铭载:赵氏太和八年(834年)十一月中旬去世,去世前朱朝政已经从新罗返回。就是说,朱朝政出使新罗时间当在太和八年之前。其次,从墓志铭文的行文看,似乎朱朝政返回不久,赵氏就悲喜过度,捐弃人世。另外,朱朝政奉命出使新罗,并不是常见的册封、告哀、吊唁等,而且在新罗居留三年,其具体公干不明。上述宦官吐突士昕与武自和曾赴新罗取鹰鹞,推测朱朝政奉使大概也是和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也就是说,这次出使具有随意性特点。而此时正值新罗兴德王(826—836年)在位,兴德王和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新罗曾七次派使节到唐朝贡,唐朝亦遣使赴新罗行使册封、吊祭等。值得注意的是,828年,入唐的新罗使节金大廉将茶种带回新罗,开启了新罗栽培茶叶的历史。这样,朱朝政出使新罗的时间,应当是从834年向前推三年,即约在831年前后。
太子赞善大夫,充册立副使苗弘本出使新罗的时间。苗弘本其人事迹亦不见史载。然而,苗氏出使新罗表现突出,新发现的墓志铭提供了重要资料。苗氏作为唐朝副使渡海前往新罗,册封继立的新罗王。可能正使不能承受航海劳顿,或在异域不习水土,导致他乡染病身故,苗氏因而“专其礼,上下之分,皎然无违,夷人祗畏而且欢戴不足”。但是,查阅现存各种史料,并未发现赴新罗使节病死当地的记载。只是韩国史书《海东绎史》卷37记载云:“武宗会昌中,以左庶子薛宜僚充新罗册赠使。宜僚到外国,未行册礼,旋染疾而卒,判官苗甲摄大使行礼。”此史料出自《女侠传》。从上述记载考察,似乎其与墓志铭文所及相仿佛,但墓志铭文载苗弘本为副使,而上及《海东绎史》则记载为“判官”;《海东绎史》明确记载唐朝所派正使是薛宜僚,苗弘本则记为“苗甲”(甲是否为苗弘本的字?因没有史料证明,不得而知),这些在墓志铭文中则看不到。其中差异之处也是明显的。无论如何,墓志铭文提供了以往史书缺载的新资料(只是没有记载具体的出使时间)。如此,结合韩国史书《海东绎史》的记载,苗氏一行出使新罗的时间可能在武宗会昌年间。
中、韩史书记载差异。首先,关于崔廷出使新罗的时间差异。《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载:元和七年七月条载唐朝册新罗宪德王金彦昇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执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鸡林州刺史兼宁海军使、上柱国,封新罗王;仍册彦昇妻贞氏为妃。《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新罗》、《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新罗》、《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唐会要》卷九五等史书记载相同,只是后面均加上了“兼命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崔廷持节吊祭册立,以其质子金士信副之”相类似之内容。朝鲜后期学者韩致渊《海东绎史》卷三七中,因编撰体例是以辑录中国史书史料为主,故也采用中国侧史书观点。就是说,中国方面史书均记载元和七年唐朝派使节前往新罗,行施宗主国册封之权力。然而,韩国现存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卷一〇、《三国史记》卷三一,以及《三国遗事》卷一均记载809年,即元和四年,新罗上大等金彦昇从侄儿手中夺得王位,遣使入唐告哀并请求册封,唐宪宗派遣职方员外郎兼御史中丞崔廷前往新罗,册立金彦昇为新罗王。也就是说,中韩史书关于唐使臣崔廷前往新罗册封的时间正好相差三年。笔者以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探明崔廷出使新罗前的行迹,如果其元和四年至七年间仍在唐朝任职,或者因其他事情不可能离开唐境,那么韩国现存史料的信凭性就值得怀疑,反之,元和四年说就应当予以肯定。据上述《唐故朝散大夫光禄卿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崔公(廷)墓志铭并序》载:崔氏贞元初进士及第,随后被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辟为从事,先后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监察御史。严震贞元十五年(799年)死,继任者严砺上闻朝廷,请转崔廷为侍御史。元和初年,严砺移镇剑南东川,复表奏崔廷为检校刑部员外郎监领州事;严砺死后,“朝廷因加宠命,俾辅藩国,遂拜珍王府谘议。”另据《旧唐书》卷一一七《严砺传》载严砺元和四年三月死,因其在任内贪赃枉法,唐廷派监察御史元稹奉使按察。时崔廷为严砺判官,亦受到弹劾,是谓“名叨参佐,非道容身,……,但以罪非首坐,法合会恩,亦以恩后加征,又亦去官停职,俾从宽宥”。就是说,元和四年三月之后,崔廷因此前担当剑南东川节度使判官,曾受到唐廷御史台派员调查,按照一般情况以及崔廷在严砺属下举足轻重的地位,接受调查肯定也需要一段时间。另外,墓志铭提到崔廷从剑南东川回到长安后,曾担任珍王府谘议。王府谘议参军事,正五品上,而此后担当使节赴新罗时官任御史中丞,其官品也是正五品上,可见只是平级移动。不过,严砺三月份去世,随后监察御史元稹奉使剑南东川按察,经过查证,崔廷受到宽大处理,完成交接手续经蜀道回到长安,又经过相关部门考察审议,被委任为珍王府谘议,而且还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成绩并受到皇帝的赏识,进而被选任出使异域使节。
无疑,上述各个环节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均需要一定的时间。也就是说,从三月滞留剑南东川到七月从长安出发去新罗,其间四个月时间,要经历如此多的事情,从时间上看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上述崔廷夫人墓志铭中有崔廷赴新罗前曾“位陪省署”,即还担当中央省署官员,时间是在“元和中”。如此,崔廷元和四年担当使节赴新罗实际上没有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中叶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以及13世纪末一然和尚撰写《三国遗事》当时,上述中国方面的史书均可看到,对于新罗宪德王何时发动兵变取得王位,崔廷一行何时到达新罗行施册封,韩国方面的《古记》等史书一定也有所记载。按一般情况,对于各方面的记载,作为谨严持重的史学家,金富轼及一然肯定都会有所比较和取舍,但也不排除出现判断错误或者排比失检的可能性;他们最后认定宪德王取得王位、崔廷一行到达新罗的时间为元和四年,可能都有其根据。只是《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对此并没有做出相应的注解,即为什么要选择元和四年,而不选元和七年?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基于以上诸因素综合考察,笔者暂且认为崔廷出使新罗的时间为元和七年。当然,通过韩国现存其他可资证明的史料,论证金彦昇发动政变到底是哪一年,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探索途径。如此看来,发掘新史料,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和崔廷一同出使,金士信或金沔担当副使问题。如上所述,元和七年唐朝派崔廷为使节,册封新罗宪德王金彦昇,与崔廷同赴新罗的副使担当者,《旧唐书》、《三国史记》记为新罗人质子金士信,《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却记载“新罗质子试卫尉少卿赐紫金鱼袋金沔为试光禄少卿,充吊祭册立副使”。这次赴新罗的副使到底是金士信还是金沔,此前未见有研究者论及。值得庆幸的是,元和十五年金士信曾上奏状,言及新罗质子充当副使时云:“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如果元和七年金士信已经回去过一次,仅仅过了七八年时间,他会再次提出担当册立副使,似乎有点勉强,因为当时在唐如金士信境遇的新罗人人数可观。鉴于此,笔者以为元和七年随崔廷出使新罗担当册立副使的可能是金沔和唐人殿中侍御史李汭。就是说,《册府元龟》的记载值得信赖。第三,据史料记载:大和五年(831年),新罗王金彦昇卒,嗣子金景徽继立,“命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节吊祭册立”。“彦昇死,子景徽立。大和五年,以太子左谕德源寂册吊如仪”。然而,《三国史记》卷一〇依据新罗自己的史书《新罗古记》的记载,认定金彦昇宝历二年(826年)年卒,唐朝派遣的册封吊祭使节源寂,其赴新罗的时间应当是宝历三年(827年)。《三国史记》撰者金富轼在注释中提到《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诸史书的记载,推测其中可能出错。鉴于此,笔者以为,金富轼在编纂《三国史记》时已经注意到此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疑惑,而《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诸史书的记载也不尽相同,所以,还是应当以韩国方面的记载为准。
对个别史料的解读。其一,关于孟元昌与盖埙出使问题。《册府元龟》卷九六五载,贞元元年,唐德宗任命秘书丞孟元昌为国子司业兼御史中丞吊祭册立使。言及建中四年,新罗王金乾运死,国人推其上相金良相为王云云。但是,依据韩国史料记载,建中四年死亡的恰是新罗宣德王金良相,继立的则是元圣王金敬信;而且,建中四年唐朝已经派遣户部郎中盖埙持节册立金良相为新罗王,不可能两次册立同一个人。所以,秘书丞孟元昌前去册立的应是新罗元圣王金敬信,而非已经死亡的宪德王金良相。
其二,据《旧唐书》卷一九九载,开成五年(840年),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150人,并放还”。原来,开成三年(838年),新罗上大等金明兴兵作乱,僖康王金悌隆被迫自杀,金明随即继位,是为闵哀王。日本僧人圆仁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到达登州牟平县界,“闻大唐天子为新罗王子赐王位,差使拟遣新罗,排比其船,兼赐禄了”,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大唐天子差入新罗慰问新即位王之使”。黎虎先生依据韩国史书记载,认为是因新罗闵哀王死(839年闰正月死于兵变),唐朝派使节当是册封继立的神武王,这是可以认定的。同时,通过圆仁日记,也可看出唐朝派使节出使新罗之前,登州当地经过了相当充分地准备。然而,登上王位的神武王在位半年,于开成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病亡,其子文圣王金庆膺继立。这样,新罗派使者入唐告哀。另据韩国学者权惪永的研究,新罗都城庆州到达唐京师长安的路程,按一般情形推算,往返需要六个月左右,而单程则需要三个月上下,就是说,新罗告哀使到达长安最早也是十月中旬。那么,为什么直到次年四月,鸿胪寺才将此事报告唐皇帝本人呢?原来,唐文宗开成五年正月辛巳已经去世,在此前后,文宗已经患病,针对皇位继承问题,宦官势力与朝臣争执不休,直到唐武宗继立,这种争执才宣告结束。因而,《旧唐书》言鸿胪寺迟迟没有上报,事出有因,其上奏对象也应是唐武宗,而非唐文宗。按照惯例,唐朝廷应派使节赴新罗告哀。如此,宦官王文擀备选告哀等使,前往新罗宣敕。同时,如上所述,唐朝向新罗派遣告哀、吊祭、册封等使已成惯例,是行施宗主国的权力和义务。这样,会昌元年,唐武宗敕令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为淄州刺史,担当大使,赴新罗册封新罗王。新罗质子及其届满应当归国的学生共150人,当是与金云卿一行同时出发返回新罗的。
除以上史料辩证之外,据上述日本请益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大中元年)闰三月十日,(圆仁)闻入新罗告哀兼吊祭册立等副使,试太子通事舍人赐绯鱼袋金简中,判官王朴等,到当州牟平县南界乳山浦,上船过海”。按: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三月驾崩,次年三月赴新罗告哀也还说得过去,但所谓吊祭、册立就谈不上了。因为新罗文圣王839—857年在位,这期间唐朝不可能再派使节吊祭、册立。圆仁仓皇回国,听到有关唐朝派使赴新罗的消息,但具体是什么名义,圆仁并未亲身历见。故笔者认为,此次派使节很可能是告哀使,而非所谓的吊祭、册立使。还有,《三国史记》卷一一、卷一二分别记载了咸通六年(865年)、乾符元年(874年)、五年(878年),以及唐昭宗天祐三年(906年),唐朝派使节赴新罗册封或宣谕等史实,但中国方面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均未记载以上事件。可能高丽时代编纂《三国史记》之时,依据新罗流传下来的资料补充撰写,因而,其史料记载值得信赖。当然,唐昭宗时回新罗实施册封礼仪的新罗人金文蔚(宾贡进士),其返回新罗的行动令人生疑,因为在唐朝灭亡的前一年,唐昭宗受军阀朱全忠挟持,唐朝境内藩镇混战不息,此时还能想起派使册封已经继位10年的新罗王,实在有点蹊跷。《太平广记》卷四八一载:“六军使西门思恭尝衔命使于新罗”。宦官西门思恭约生活于唐宣宗、懿宗、僖宗在位期间,其出使新罗可能亦在这一时期,但具体的时间并不明确。
在唐新罗人受命出使新罗
上文业已提及,唐中后期,在唐的新罗人质子金沔(或金士信)、金云卿、金允夫、金文蔚、金夷吾等人,担当唐朝出使新罗使节或副使,前往故国新罗,行使宗主国的告哀、册封、吊祭等使命。唐朝为什么要派遣新罗人担当如此重任?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
首先,此反映了唐与新罗双方在宗藩框架下的友好关系。早在唐高宗时代,因唐朝与新罗缔结藩属同盟关系,在唐新罗质子宿卫者就频繁来往于二者之间。罗唐联合征伐百济,新罗在唐宿卫(新罗王子)金仁问即担当征讨副大总管;灭亡百济之后,唐高宗召见新罗王子金仁问,敕令其返回,传达唐高宗旨意,令新罗协助唐朝征伐高句丽。就是说,7世纪6年代,新罗在唐宿卫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已经接受唐朝派遣,赴新罗传达敕令,即已带有充当唐朝使节的雏形。现在看到最早记载在唐新罗人担当出使新罗使命者,为元和七年随崔廷出使新罗的新罗质子金沔(一说为金士信)。元和十五年(820年),新罗质子金士信上奏:“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藩,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证明以新罗质子充当赴新罗副使早就有之,而且已经形成惯例。以质子或宿卫者担当出使新罗使节或副使,体现了唐与新罗密切的宗藩关系。
其次,在唐新罗质子或宿卫者均乐于担当使节,以便利用此机会回到故国,探省亲人;同时,完成使命后还可以加官晋爵。如唐敬宗宝历初,“鸡林人前右监门卫率府兵曹参军金云卿进状,请允入本国宣慰副使,从之”。上文提到的金士信亦说“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而金允夫其人曾三次担当副使出使新罗,返回唐朝后,要求唐廷授予其相应的官职。还有,唐人许棠《送金夷吾侍御奉使日东》中有“还乡兼作使,到日倍荣亲。向化虽多国,如公有几人”句,亦可说明这个问题。在唐朝的其他藩国也有相类似的情况,但只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如唐中宗神龙二年命右屯卫大将军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充使册立突骑施乌质勤之子娑葛为怀德郡王。当然,作为唐朝廷来说,虽然鸿胪寺中有专门的译语人才,但熟悉新罗国内情况,准确翻译唐朝诏敕,在唐生活若干年的新罗宿卫者当是首选。上引金士信奏言中就有“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之语;金允夫亦有“中使入蕃,便充副使,同到本国,译诏书”的请求。可见,由新罗质子或宿卫者充任副使,实际上就是担当翻译诏书,协调唐朝使节到达目的地后与新罗方面的联络。唐朝290年历史中,作为唯一和唐朝保持长久友好关系的藩属国新罗,其派往唐朝的质子或宿卫者,长期接受唐朝的笼络和恩惠,成为双方建立长期稳固关系的桥梁。唐朝利用他们的独特身份,派遣他们担当出使故国的使命,不仅可以发挥其特长,安抚其思乡的眷眷情怀,而且可以保证双方关系的持久友好发展。在这一点上,唐统治者的处置无疑是比较高明的。
第三,在唐新罗质子或宿卫者,弥补了唐后期涉海出使新罗后继乏人之缺憾。唐中后期政权衰微,盛唐时代效死边疆的群体豪情已一去不复返,加之当时人们对潮汐及航海技术掌握的欠缺,以及对到达新罗后处境的忧虑,对唐政府来说,遣派富有健康体魄和非凡才干的使节赴新罗并非易事。大历初年,派遣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归崇敬等人出使新罗,“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但终化险为夷。元和七年崔廷出使新罗,“虽泛沧溟,叱驭而往,朝廷以为难,实由夫人以事君之理助焉”。即朝廷对于出使人选颇感踌躇,多亏崔廷夫人从中晓以情理,崔廷才踏上出使的征程。崔廷、朱朝政出使新罗三年,崔廷的夫人郑氏“自始去至于言旋,蓬首濡脸,艰意空门,求福佑以助行,果安逸而速返”;朱朝政的母亲赵氏“以嗣子奉命鸡林三岁,然复疚心疾首,六时礼念,冥期佑助,以福后光。果符神力,保全以归”。即夜以继日地向佛祖祷告,祈求神灵保佑。值得庆幸的是,两人虽历经艰险,但均安全返回。而有的使节就没有如此幸运。宦官王文擀一行,“王事斯毕,回橹累程,潮退反风,征帆阻驻,未达本国,恐惧在舟。夜耿耿而罔为,魂营营而至曙。呜呼!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及其不测,妖怪竞生。波滉瀁而滔天,云叆叇而蔽日。介副相失,舟楫差池,毒恶相仍,疾从此起。扶持归国,寝膳稍微,药石无功,奄至殂谢,享年五十有三”。太子赞善大夫苗弘本,“副新罗使立其嗣,将命至其国,使病死,公专其礼,……”《太平广记》中也记载了多起朝廷或民间前往新罗,途中受困,以及被海流漂向他处的事件。有如此事件发生,加之中唐以后东北亚国际关系复杂多变,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对唐朝向新罗行使所谓宗主权力产生影响。而在唐新罗质子或宿卫者恰好具备这种能力和要求。如同安史乱前任用藩将捍御边疆一样,派他们担当出使新罗使节或副使,成为中唐以后政府处理与藩属国新罗关系的一种特殊诉求。这样,会昌元年、天祐元年唐朝分别派遣新罗宿卫者金云卿、金文蔚担当使节,元和七年、元和十五年、宝历二年分别遣派金沔、金士信、金允夫担当副使,不仅保证了每次出使任务的圆满顺利,而且对于唐朝行使宗主国权力,继续唐初以来实行的质子制度不无益处。
赴新罗使节相关问题考辨
唐朝对出使新罗使节出使费用政策的变化。唐政府对漂洋过海出使异域的使者执行什么样政策,都有那些优待?因史书记载简略,以往研究者虽有所涉及但因所论主旨和范畴的不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仍很有必要。
唐朝对出使异域的使节,有一整套的奖励方法。贞元十六年(800年),新罗元圣王金敬信卒,其子金俊邕继立。唐派遣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鱼韦丹率使团前往吊祭、册立。“故事,使外国者常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义,以便其私,号私觌官。”虽然韦丹使团最终因新立的新罗王很快丧命,韦丹到达山东郓州即依诏返回,但唐中后期对出使外国者提供的优厚待遇,以及筹措出使费用手段的不合理可窥一斑。其一,之所以成为“故事”,说明是此前形成的惯例,已执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至于此惯例形成的具体时间,未见史书有相应记载。其二,唐政府为出使外国者“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义,以便其私,号私觌官”。即出使者可将此十员州县官名额变卖,所得钱款由出使者本人支配,以弥补路途及到达目的地各种费用的不足,其中大量的余额亦归为出使者所有。看来,唐朝可能是基于经济诸方面原因,才实施这种一定程度上损害政府形象的做法。同时,从这种优待出使者措施,可以推测当时肯舍弃安逸、甘冒生命危险飘洋过海出使异域者可能并不多。其三,具体到出使新罗,因为从长安到山东半岛或者今江苏沿海地区,须经过长路漫漫的陆上旅程,接着又要横渡大海备受艰险,到达新罗后还要适应和内陆完全不同的气候环境,一些人不幸中道毙命,一些人葬身茫茫大海,还有一些人在新罗染病不治客死他乡。所以,唐政府想通过提高出使者的待遇,使其从中得到好处,鼓励更多的官员踊跃前往,为国家出力。然而,唐朝廷采取这种私觌官优待处置措施,对唐朝的长治久安来说,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学者认为当时所谓随使国信礼、私觌礼已成风气,“此种礼节物化趋势,既显示政府之间交往的增多,也是外交经费在财政管理上逐渐完善的标志”。其中并未涉及私觌卖官鬻爵弊政之实质,以及对当时朝野风气的负面影响,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私觌官优待奖励措施,在唐中后期历经兴废过程。如上所述,这种奖励措施起于何时,未见史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工部尚书李暠担当入吐蕃使时,其中就利用私觌两千匹。韦丹赴新罗前,也对“私觌官”处置措施提出质疑,认为:“‘吾天子吏,使海外国不足于资,宜上请,安由卖官以受钱耶?’即具疏所以。上以为贤,命有司与其费。”就是说,出使外国的一切费用应该由唐政府按照实际支出拨付,不应采取卖官鬻爵下策。唐德宗非常赞赏韦丹的做法,令有关部门拨付其费用。但这种“私觌官”惯例并未因此而终止。元和七年(812年),唐宪宗诏令“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量别支给以充私觌。旧使绝域者,许卖正员官十余员,取货以备私觌,虽优假远使,殊非典法,故革之。”元和九年(814年),胡证对此也提出质疑,并以身作则,请求改变这种有碍国政的政策,但唐穆宗继位又有反复,并确定使回纥、吐蕃者私觌官具体数目。直到唐文宗继立,唐朝廷才下《停私觌官员诏》,云:“仕杂工商,实因鬻爵,尚须命使,改以赐财。其入蕃使旧例与私觌官十员宜停。别与钱五十贯文,令度支分付,永为定例。”废除了这种以出卖官爵,换取出使费用的做法,并永为定例,解决了长期以来有碍唐政府声誉的私觌官问题。
出使新罗使节的活动及贪求财货、私贸易问题。出使异域,历经艰险,但正是通过双方使者相互来往,延续并保持唐与新罗持续友好的宗藩关系。然而,一些出使者趁机将唐朝物资或钱帛携带至新罗,与当地人交易,以便获得巨额利益,进而成为出使新罗的公开秘密。如大历二年(767年)归崇敬出使新罗,在同僚官员纷纷赋诗送别,表示良好的祝愿和安慰的同时,史载:“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崇敬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既然已经约定俗成,说明唐与新罗之间,既有官方的朝贡——赏赐贸易,以及民间的往来和贸易,又有担当出使任务使者的私贸易。归崇敬虽然没有步其后尘,但并未能改变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这种官方贸易之外的私贸易,风行于当时双方交往之始终。应当提及的是,由于这种交易的隐密性和交易的个体特性,使得涉及私贸易的记载并不多,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也不过是有限的几条,因而对这种私贸易数量的大小、交易品种的多少、各个时期交易的差别等问题的探讨,就很难有明确并量化的结论。另外,担任册立副使的顾愔,出使返回后,根据所见所闻,撰写了《新罗国记》一书;长庆年间赴新罗使源寂,看到新罗当地文人“传写讽诵”冯定所作的《黑水碑》、《画鹤记》。相信唐使者滞留新罗期间,通过自己的眼睛,对新罗都城以及沿途的环境、风俗都有相当的了解。还有,因为唐朝文化的先进,唐朝使节到达新罗,往往成为当地的一件大事,赠送钱财者亦不乏其人。盛唐时代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善棋者杨季应随邢瓙出使新罗,“至彼,大为蕃人所敬爱,厚赂而还”。山东登州商人马行余,乘船到桐庐经商,结果被西风吹到新罗国。新罗国王接以宾礼,言道:“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与马行余谈论儒家经典。马行余对儒家经典一窍不通,新罗王非常惊讶并疑惑不解。对唐商人都如此礼敬,更何况唐朝廷派遣的使臣。可能正是如此,加深了出使者的自大妄为。上引史料中“至海东多有所求”就能说明问题。中唐以前,因出使前皇帝及鸿胪寺的约束,贪求财货者可能还有所收敛,能够体现宗主国使节的气度和品德;中唐以后,随着出使者成分的复杂化,像归崇敬注重宗主国形象者可能就很少见了,以至于出现上文提到的宦官吐突士昕、武自和贪求财货,接受新罗的财物,拒不交公事件。
唐朝使者在新罗逗留的时间。按常理推想,唐赴新罗使节应当是吊唁、告哀或册封使命完成之后,在短时间内返回。然而,在特殊的情况下,唐使节亦不得不滞留新罗。贞元二十一年〔此年八月改元永贞,是为永贞元年(805年)〕唐德宗崩,唐顺宗遣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元季方前往新罗告哀,并册封金俊邕子金重熙为新罗王。但是,三月继位的唐顺宗,八月初即下诰自称太上皇,皇太子李纯继位,是为唐宪宗。唐顺宗于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崩逝。一年内皇位几易其主,加之朝野暗流涌动,在唐境内及周边地区引起极度不安。这样,“新罗闻中国丧,不时遣,供馈乏,季方正色责之,闭户绝食待死,夷人悔谢,结欢乃还”。就是说,新罗冷眼观望唐朝政局变化,对前往新罗的唐使节不以礼待,既不供给相应的生活所需,又在告哀、册封使命完成后不予遣送。最后,在元季方义正辞严、冒死抗争,加之唐内部形势亦渐趋稳定的情况下,新罗才将元季方一行依礼送还。新发现的墓志铭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信息。《朱公故夫人赵氏墓志铭》载赵氏嗣子(即宦官朱朝政)“奉命鸡林三岁,然复疚心疾首,六时礼念,冥期佑助,以福后光”。《崔廷墓志铭》载崔氏元和七年(812年),“会新罗王死,选可以宣达国命抚柔外夷者,由是擢拜公为尚书职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吊祭册封使。期年而返”。这里的期年,即三年(也有认为一年的见解)。其妻郑氏墓志铭则明确记崔廷充“吊祭于乐浪国”使节,“往返三岁”。就是说,上述三通墓志均载唐使臣出使新罗来回费时三年,前者未明出使时期及出使名目,后者明确说明是“充吊祭册立使”。唐咸通年间进士李昌符有《送人入新罗使》诗云:“鸡林君欲去,立册付星轺。越海难计程,征帆影自飘。望乡当落日,怀阙羡回潮。宿雾蒙青嶂,惊波荡碧霄。春生阳气早,天接祖州遥。愁约三年外,相迎上石桥。”诗最后两句,亦有“三年”字样。在长达三年时间内,唐使者滞留新罗干什么?是否只是吊祭、册立使停留时间长(上述开成五年出使新罗者王文擀,即是办完事就返回)?因缺乏相应的史料佐证,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来日。
(涉及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的纪传,以及《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书的记载,金石资料取自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17)。相信实际前往新罗的唐朝使者,一定会比上述人物还要多。而归崇敬、盖埙、韦丹、元季方、崔廷、源寂诸人,《旧唐书》、《新唐书》相关传记中有记载;韦丹、崔廷两人的墓志铭文中也有论述。但是,宦官王文擀、武自和、朱朝政三人,以及苗弘本、孟元昌两人,其赴新罗册命或公干事迹正史中却不见记载,其生平也不甚明了,我们只有从其本人墓志铭文,或与其相关人物墓志铭文中得其事迹之点滴,但这却是相当有价值的东西。赵恭事迹亦不见于中国侧史书,而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中却记载了赵恭赴新罗传达敕令之事件。另外,新罗在唐留学生或宿卫金沔、金士信、金允夫、金文蔚、金夷吾等人出使新罗,其双重身份和担当的使命令人注目,这也是唐中后期东北亚地区交涉史的一个独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