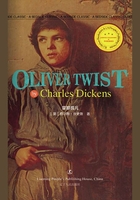那年的夏季,我正独自走在去澜沧的路上。后背上的背囊,松松垮垮晃了晃荡。
关卡多起来,空气里飘浮着紧张的分子,和雨一起飘落,呼吸湿重。
据说,这一时期的贩毒分子相当猖獗,有的地方开始荷枪实弹武装押送。也有的把毒品塞在汽油桶、轮胎里,开着车直奔昆明。
也听说,戒毒所里人满为患。
我却是欣喜,因为这里过了北回归线了。过了北回归线,就意味着下面的天地不同一般,今后的风雨不同一般。
一边走一边哼叽,两百公里后,词有了,曲也有了,是很平俗的那种。
当我咀嚼橄榄里的记忆,
当我聆听睫毛下的雨滴,
思念你,思念你,思念你,
思念你,苦涩泥泞的雨季。
编唱出这一段时我刚到阿佤山,那里有不少人鼓囔着嘴巴在嚼槟榔。妇女大娘居多,嚼得牙黑唇紫。后来我在野山老沟里发现了橄榄,是那种小小的青青的野橄榄,比葡萄珠儿大不了许多,吃到口里涩涩的。但只要有丁点儿水,不仅解渴,还凉甜咝咝。那种滋味让我回味至今。
当我咀嚼橄榄里的记忆,
当我聆听睫毛下的雨滴,
我不能,我不能,不能归去,
我不能再走进,虚伪的甜蜜。
哼全这一节,是从沧源到澜沧的山间路上,在茅草屋的窗下躲雨。微弱的烛光,像屋里男女的窃窃低语,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最后熄灭。雨水从屋沿刺探着的草梢流淌,滴滴答答,简洁没有变奏。我在这个大睫毛下,缩成了一个瞳人。那夜,我也睁大眼睛,听了一宿,看了一宿,没有一点敲门的欲望。天亮,我继续向南赶路。
当我咀嚼橄榄里的记忆,
当我聆听睫毛下的雨滴,
我的心,我的爱,已经有了归宿,
我的心,我的爱,是流浪的步履。
走着,我常常回头,幽静空荡没人。这令我常常疑虑,自己是不是这条路上的最后一个人?也怪,那时我没想过,这路上的第一人是谁?
更多的时间,我把上路叫赶路。把路赶得乱跑,东一条西一条。不管多少,我只选择面前的这条。左右分岔出去的,我看也不看。
当然面前的这一条,不一定是阔达的,不一定是平坦的。心思不定,平的也不坦,阔的也不达。
路这家伙其实比我走得快,有时晃晃悠悠慢条斯理;有时颠颠跳跳一路小跑;有时伤心得千疮百孔;有时一览无余平铺直叙;也有时一闪而过距离远了,细细得看不清楚,可山口一转弯又见到。此刻我就会比平时更加用些脚力,相见总是兴奋的。
路有四季,路的四季是泥泞,是雪滑,是干渴皱裂的长舌,是落叶枯黄的铺垫。
但路没有家。
路有湿淋,像一个恸哭的孩子,泪花闪烁,汪着淌着。只有风,只有阳光,才能让它慢慢舒畅。路有时仰起疙疙瘩瘩的脸,和你对话。你攀爬的腿脚就会酸痛,缓下速度。
但你尽管乐哈哈地记住,有上坡就有下坡,慢慢来,甭着急。
路可以青春不衰,路能往复来回。低去了你下,高上了你上。雪域峡谷,由你凭你。路因为自由,所以神往,所以天助。
路的脚印重叠,厚厚的一层,有向前的,有去后的。横穿的,间杂在其中,是走兽零乱的爪子。
路也有突然夭折,突然阻断,突然不知所向,突然茫茫不知道所以。是一个悬崖绝壁,一个策马勒缰,一个巨大的感叹标志。隆隆高天,还在升起的太阳,牵引着目光和你的双膝。
路有阴晴有飘忽有粉碎。在狭窄的隧道,在无垠的草场,旱獭叼进洞穴,蜂鸟衔在空中;羊群咩咩滚过,马蹄哒哒飞扬。
路有悲欢离合,路有分道扬镳。路熟悉天熟悉地,熟悉每一块岩石每一棵青草,每一条江河每一座峻岭。路不仅是人的写照,路还是自然的写照。路的发展是陌生的,蹂躏的,践踏的,有时是血肉横飞的。路就改变了别人的模样,完整了自己。
路的陌生,是延续的面前,延续的身下。
路,没有朋友,路相识在岔口就要分手;即便有,老远也是影影绰绰,老死不相往来;交合的时候只是刹那,交合得看不出是你还是我。它们只是延续,延续到消失,延续到不能再延续。
直到有一天出现了城市,出现了立交。路也只能出现在上边,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或穿行在下边,我走我的你走你的。
与其这样,不如在旷野,不如在山川,不如跋山涉水,不如曲曲弯弯,不如被风沙遮蔽,不如被洪水冲刷。但路是丰富的,是五颜六色的,也会身不由己地赶一赶时髦:白的是水泥,黑的是柏油,黄的是暂停,红的是禁止。
我一直不停地赶下去,把路赶得扭来扭去;赶得丢出了视野;赶得我去找,像路一样茫茫然然;赶得我找见了却又丢;赶得我丢了又去找。
好几次,你想多几条路,让自己选择一下,可你脚下偏偏就这么一条。当然,这样一来也挺好。你大可不必多虑,一门心思,伸你孤独的腿,一门心思迈你孤独的脚。
有时你以为你在赶路,可实际上路在赶你。
直到有一天在旷寥的山洼洼里,碰到一个身穿蓑衣赶牛的婆婆,她说:“噢,你是路人。”
我才意识到,我并没走出多远,一点儿都不孤独。
啊!路在远方。啊!路在延续。啊!路是风雨。啊!路是崎岖。
路——是天意!
我给这歌起的名字叫:《北回归》,北回归而不归,一直南行。
哼着小曲,腿就开始懒散。
看天色,该找个歇脚过夜的地方了。便在孟朗转了转,寻到个清静的鸡毛小店。
办好手续,找到房号,敲了屋门。开门的却是个头发散乱的妇女,正愣,里边床上一个老头说话了:“进来吧!”
摘下背包,扔在一个空床上,我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臭咸带鱼味。
老头像个熟客,床头床下桌子上,放着零零乱乱许多过日子的东西:掉了把柄的小饭锅,喝干净的酒瓶子,半罐咸菜辣酱,断了炉丝的小电炉子。
床帮上,老爷子靠着屁股,系着裤子,趿拉着一双破布鞋。估摸有六十几,身材笔直,光裸的膀子松懈的肉。他在床上黑兮兮的被子下,抻出件褪了色的卡叽布蓝中山装披上。精神气饱满,口音亮堂,不像本地的。
给他递上香烟,扯了几句闲篇子,才知道他是陕西黄陵人,跑江湖卖跌打药的。我想跑江湖的,除了有些真假功夫外,阅历应是极丰富,都是爷,便出门买了瓶糯米白酒,一块卤牛肉,半包花生米。
也借机会,给他和那女人收拾收拾自己的时间。出门在外,得学会体谅,不难为自己,也别难为别人。
再回来,女人走了。我就和老人喝起酒。他告诉我他姓齐,是齐天大圣的齐。我当时愣没反应出齐天大圣的“齐”怎么写。脑袋里,总想骑马的骑。这是那女人留下的暗示。
我尽管喊他齐大爷。
一大束阳光,从脸盆大的西窗户拥挤进屋,落在桌子上。花生米成了金豆子,碗里酒,成了琼浆玉液。
齐大爷喝到兴头,下了炕,从铺底下取出一块灰瓦来,扣在桌子上。在屋子中央站直,运了一阵儿气,伸出胳膊,用中指在瓦上,轻轻钻了几下,瓦就被钻出了个窟窿。
我惊喜地跳起,幸运自己碰上了高人。
齐大爷说,雕虫小技,你若想学,随时可以教你。
我似信非信,就劝他喝酒,我却拿过那块瓦翻来覆去地看。好歹也得两公分厚呀。再看看他的手指,跟我的也差不多,真神了。齐大爷也不理我,一直到把酒全喝干。
齐大爷抓了把花生豆扔进嘴里,起身从铺下又找出一块瓦扣在桌面。一手扶我的肩,一手攥着我的手指按在瓦上,然后发功把气力传给我的指尖。
我虽然不大相信,但还是随他试着。仅仅几下,竟然手指钻透过去。高兴得我把齐大爷改叫齐师傅了。
齐师傅抹擦着花白的胡碴儿咂着嘴,笑着说,你自己在外瞎摸乱闯,不如跟我走江湖卖艺、卖药,如何?保你吃香喝辣!
说正格的,这种生活对我着实诱惑,可眼下不成。
我就说我自己要干吗干吗,不能半途而废,不能不持之以恒。说我在这里待不了两天,后边的路还老远老远。说我特愿意拜您为师,有朝一日去陕西黄陵龙爪树东坡岭去看您。说我二哥1968年曾听毛主席的话,在黄陵县龙爪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了十几年知青。还说了这是缘分什么的,说完便跪下拜了师傅。
师傅放开嗓门,舒朗地笑了好一阵,然后扶起我,在屋中来回踱着步子说:找不找我都一样,我已经几十年没回家了,也不打算回去了。但你这徒弟我收了,我教你几手,一来师傅别白当,二来你今后没饭辙的时候,也可以用用。拉拉场子,邪虎邪虎人,混口饭吃什么的。
说着像个小孩子,钻到他睡的铺下,鞋掉了也顾不上,两条光腿露在外边,翻腾起来。猛然他好似随口问了一句:你二哥叫什么?
我说,叫曾廉,廉洁的廉。
唔。他好像在铺底下想着什么。
师傅再爬出来时,左手拿着袋灰粉面,说是用那瓦片磨的;右手举着个瓶子,说里边不是酒是醋。他告诉我,灰粉面子兑醋,调成泥膏,抹在瓦片的洞洞上,处理平整,明日干了就可以再用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齐师傅是个江湖骗子。但不知道为什么,骗子的骗术戳穿在眼前,而崇敬之心,并没有因此减少。
都收拾利落,我又递上一根“云雾山”香烟。师傅照常麻利地把过滤嘴撅下,从兜里掏出个挖耳勺,揉揉烟卷挠出了一半烟丝,又从怀中拿出个小瓶子,跟筷子头差不多,把里面的白粉蒯进一点儿,再把烟丝塞上,揉弹揉弹。最后用舌头舔湿烟卷一侧,点着。
这过程我说得啰嗦,其实很快。
“抽过吗?”师傅长吸了一口问。
“什么东西?”我虽然明白是毒品,但假装。
“白面,少抽没事儿的!”说完递给我。
我嘬了一口,屋里弥漫起臭咸海鱼味道。这东西虽然我是第一次抽,可我知道它的厉害。
它可不比我在新疆抽的麻烟,制幻力相当大。
我就跟他讲在新疆抽麻烟,整宿地听奏十二姆卡木,看维吾尔族男人跳舞,一点儿不瞌睡,大天亮了还兴致勃勃。又煽惑,麻烟香香的,好闻,掺在莫合里,是一种特殊的味道,现在还想,等等等等。
师傅说抽过麻烟。话语中对那东西有点不屑。他说严格意义上说,麻烟不算毒品,不像白面,几回就上瘾。
他说:“这白粉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看你自己怎么调教它,控制它。”
“能调教,能控制?”这我是第一次听说。若能的话,怎么还能叫海洛因,叫毒品?
师傅见我拿着烟,没意思给他,自己又装上一根儿抽起来:“当然我抽得少,总抽这些,不增加量,对身体对精神都好!你看我这岁数,昨晚那女人,我一宿没让她睡。”
我心中一抖,觉出这烟不是味道了,便扔在地上踩灭。能让人放纵一宿的东西,可得小心。
一旦放纵了,怎么能抑制得了?整宿的折腾,几天下来,还不成了管痨!
师傅看着地上的烟,不高兴了,指着装白粉的小瓶说:“你知道这东西多值钱?在孟朗一管已经卖到了四十块。”
“都是从缅甸过来的吧?”我有些歉意。
“是。那边是便宜,可就是再便宜,也是钱啊!再说,带这东西过边境线,都是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危险,光是一个钱的事儿吗?”
索性,我拉上师傅,说请他去吃拜师宴。实在的说,我的确心里很难为情。这样的人,我可不想得罪。
“师傅说你两句是应该的,别往心里去!”他掩饰不住脸上的笑。
天虽然黑了,小街上还挺热闹,店铺门上都亮着灯。高挑着的红灯笼,黑字清晰个“酒”。铺子里边倒清静,我俩拣了个角落坐下。
店小二手脚利索,只两趟,酒、菜上齐。
先干了一杯,我就开始说了一些蜜话。类似师徒如父子;一朝为师终身为父;一年半载我回到北京后,师傅也去京城住住玩玩,逛逛四九城:故宫、煤山、后海、天坛等。
师傅高兴,几杯酒下肚话语滔滔:“北京那地方,我这种人不能去,那叫行骗,对吧?抓住没好,锒铛入大狱呗,是吧!可我挣足了钱,可以到北京找你耍,是吧!咱只耍耍,不拉场子,不骗人,行吧?”
“当然,一定!”我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给他。他看了又看,然后小心地装好。其实他不识几个大字。
“也到天子脚下,皇城内外,溜达一圈,死也闭上我这双狗眼。我爹妈早死,又无儿无女。哎,像我这种人,肯定是惨死他乡的命。”说着师傅滚落两颗浑浊的泪珠,然后用秦腔乱弹或许叫同州梆子什么的,唱了一句《赵氏孤儿》。文词本是豪放,却唱得声音凄婉,备感天涯苍凉。
我的眼眶里,也湿润润了。
我这师傅,十八岁上娶了个媳妇,可婚后六个月就生出个娃娃。他觉得窑里窑外没脸见人,就甩了手,填了水窖,炸塌了土窑,跑出了老家。年轻时贩过马,挖过煤,采过石头,最后睡了蒙古女人,让人家追杀到银川。有一年,在中卫沙坡头大漠里,他三天三夜,背出了一个老乞丐。又三天三夜,喂水喂饭救活过来。
活过来的老人,每日早起第一句话:“恩人,万福。”然后以身传授,教了他一些江湖手艺、功夫秘诀。师傅的生活才算有了着落,稳定下来。
“师傅还是早点来北京吧,我刚才说过师傅亲如父。我的条件虽然有限,但管您仨饱一倒,逛遍京城,绝没问题。”
师傅兴奋得又装上烟递我:“再抽根儿?”
我笑着接过说:“那老乞丐呢?”
“死啦!”师傅说。
“怎么好好的,又死啦?”
师傅说:“人,哪有不死的,但他人死得蹊跷。也没跟我招呼一声,就走啦。我顺着脚印在沙漠里找见,沙子已埋到他脖颈子了。一副乐呵呵的嘴脸,也不知他在乐呵啥。其实要想死,不用什么道理,死就是道理。”
“您咋不进银川城,找个事儿做?”
“机会有,可我就是个流浪的命。”说着他就给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当年,师傅贩马挣了大钱,在宁夏的黄河边买了一片草场,养了五匹黑马五匹白马,过上了清静舒心的日子。
这天,马场草地呱呱铁蹄疾响,来了个背长枪的大汉子。刚到他的土屋前,四腿闪失,马就跌倒了,再没爬起来。人也滚翻在马架子下。
大汉黑不溜秋,身上枪伤、刀伤,伤痕累累,奄奄一息要断气。师傅把他背到土炕上,伺候着,治疗着。好吃好喝好待遇,留在家里养了大半个月。来自何方?怎么伤成这样?是何身份?师傅一概不问。
痊愈了,黑汉子要走。走就走吧,男爷们长的两条腿,就是走路用的。走时,师傅送了他一匹黑马。那人骑上马,大叫一声“恩人!来日报答,后会有期”跑马远去。远去了,师傅抱着双手,站在草原上,发了好一会儿愣。然后回屋收拾,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几个月后,师傅的马场又来了个小瘦白脸汉子。青衣青裤,挎着手枪,是从黄河滩头爬过来的。
师傅把他背回,屋前马架子上吊起。银元抠开嘴巴,控出的绿水,淌成河流子,呛死一窝草鼠。又是好吃好喝好待遇,缓过了精气神儿。他只说,有匪人追杀,才跳了黄河。师傅也没再问。
十天后,白脸汉子要走,师傅送了他一匹白马。小个汉子翻蹬上鞍,手举头顶一个敬礼说:“终身不忘,恩人!”蹬磕马肚,飞驰而去。
师傅就有了预感,是那种让人不踏实忐忑不安的预感。这预感常常让他头疼,一天几次要向草原上望上几眼,侧耳听上几回。
草原上很静,午间的阳光很厚很沉重,照射在一片片倒伏的黄草上。从坡头看去,像一个个金色的陷阱,还打着旋涡。花季已过,偶尔可见一两株蓓蕾,也是藏在稀疏背阴处的草叶下。为了盛开,顽强地成长。
到了秋上,河滩刮起了一大团土风。师傅正纳闷,烟尘中跑出一队快骑。有白马,有黑马。马上的人唔呀呀乱叫,举着马刀冲来,还有枪子嗖嗖乱飞。
师傅慌乱了,师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个僻静之地,也会搅进战事。师傅放弃了膘肥体壮的马,和归置得挺好的场子房屋,抱着羊皮筏子,跳进了黄河,漂到了对岸。
顺着岸,师傅漓漓落落一边逆水往回走着,一边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人,把马全牵走了,还给了一把火,烧了他的房子。
窝没了,师傅又开始流浪。师傅也没打听,抢他烧他的是些什么人。反正跑不出强盗土匪。
多年后,师傅流落到同心县城(我去过那里,印象很深)。在一个集会上,他遇到在他马场住过的那个小汉子。一点儿没变,白脸瘦瘦的。当时正站在舞台边上,威风凛凛的派头。挎着短枪,戴着新军帽,衣褂周整,像个当官的。
来凑热闹的老百姓呼漾呼漾的,好像是抗美援朝的什么会。师傅就朝前挤了挤,想让那个小汉子看到自己。他不好意思先跟人家招呼。
舞台上有人讲完话,一帮子男男女女跑上去,开始演活报剧。一个美国佬戴顶高帽子,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人们喊他“肚驴门”。
演着演着,台下的战士愤怒了,举着胳膊呼喊着狂叫着。师傅身边有个战士,义愤填膺,喊哑了嗓子,喊不出了声,就顺势摘下大杆枪,端起,拉栓,给了“肚驴门”一枪。好在师傅清醒着明白,不是秦腔梆子也是演戏啊兄弟。就去夺,枪子就打歪了,打在一个看戏的小伙子胸口,当场死亡。师傅也被吓傻了眼儿,坐在暴腾狼烟的灰土地上,不只该咋办。
后来那个开枪的战士,被判了死刑。可死者家属,却在军队执行的时候,愣劫了法场,给抢走了。军民经过交涉,死罪赦免,活罪不饶。那个战士是个山东人,他为了报恩,认死者的爹妈为自己的再生父母;认死者的祖父,为自己的爷爷。后来这家人,把这个战士送去了朝鲜战场,让他戴罪立功。
这都是小汉子军官事后告诉师傅的。师傅见到他时,他说:“老弟,是你呀!你避免了一次恶性事件的发生。”说完高兴地把师傅抱在怀里很久,师傅激动得也落了泪。回到屋,军官扑通跪下,“恩人恩人”地叫。叫的师傅也只好跪在地上,陪着。
小汉子军官是个汉人,住的很阔气。大砖房不说,高台阶的门口,还有人戳着大杆枪站守着。在那之前,师傅从没进过这么讲究的院落,兴奋得不知道咋好,一个劲儿地搓挠手心。
军官扶着师傅坐下,立码就有个当兵的小鬼,端来八宝盖碗茶,还放里两大块冰糖。桌子还有很多东西,油香馓子、面辣酱、头茬子羊羔肉。
吃过肉,擦着嘴,师傅看到桌上放着一张人画像。他眼熟,像是在马场住过的那个黑大汉子。师傅就拿起细看,嗯,没错,是他。
小汉子问,你认识?师傅点了头。师傅点头时啥也不明白,当然更不明白,小汉子为啥再不让他走了。顿顿酒肉,睡的被子松松软软安逸极了,一沾脑袋就睡着。白天,还尽他去街上玩耍。小汉子说,有恩不报非君子。师傅想了想,这话挺熟,好像是这么说。
正是年节,城里街上格外热闹。男人小圆帽,白生生;女人白盖头,新崭崭。一看就知道,方圆几十里,山沟里峁塬上的,都来了。
师傅个头不矮,稍一踮脚,就可瞅到密密麻麻攒动的人群头顶。师傅游手好闲地逛着,他什么也不想买。一个个摊子看过来,也是享受。渴了就喝碗茶,接着溜达。从大清真寺门口过去时,人群成了疙瘩,好不容易才挤出来。
挤出来,师傅再朝人头上扫一眼,原本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可这一瞅,就瞅见熟悉打眼,打眼熟悉,瞅见了冒出人群老高的胡碴儿黑脑袋,师傅认出是黑大汉,就喊,兴奋得两张脸往一堆挤凑。俩人挺费劲儿地抓唠到一起。黑大汉刚给师傅磕完头,没说上半句,他扭脸分开人就跑。
原来是小汉子军官,带着几个端枪的士兵冲了上来。师傅糊里糊涂地害怕起来,莫名其妙地也跟着黑大汉跑。
跑出土围子,两人又往山沟跑。
枪响了,黑大汉停了下来,对师傅说:“恩人老弟,你前边跑,我断后。”他说完刚转到师傅背后,一颗枪子打进他后脑勺,就倒下了。重重的身体把地砸出山响,砸起高高的土灰。
师傅吓得腿肚子转了筋,再挪不开脚,被五花大绑了。
再没见小汉子军官。
一个月后,师傅才被放出来,又开始流浪。
师傅说,那天吓得他尿没丁点糟蹋,全泡了裤裆。他这一辈子,最明白了一个大道理,肉忒熟了没滋味,人忒熟了要出事儿。生人不知道深浅没关系,陌路相见,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熟人不成,熟人你俩在一堆,心就没了设防。跳进陷阱,你还不知道沟沿在哪搭。
我抽着,听着,精神很是亢奋。坐不住,就在地上来回转着。亢奋不是师傅的故事造成的,是我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在闹。闹得我坐立不安,便随口问道:“我来时,见的那个女人是谁?”
“管她是谁?是女人不就得了。怎么,想女人了吧?”
我点头。
“走,我们回去!”
我俩就一人提着半瓶酒往回走。快到旅店的院子,大老远就看见院门灯下站着几个女人。
并不妖艳,也没打扮什么。似乎就是街头巷尾看到的那些,不知干什么的。
到了跟前儿,师傅并没说话,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用舌尖舔了一下,叼在嘴上。女人们就呼啦围了上来。师傅向我说,选一个吧?我就挑了一个个头高高、嘴唇稍红的。
我要进屋时,师傅说,我在外边守着,踏踏实实整你的,整糊涂算。
一进屋,灯没开,那女人就把我掀翻在床。昏天黑地,没头没脑,没上没下,没里没外。
该流的流过,不该流的也流,该进的进了,不该进的也进,没完没了。几次从床上掉到地下,又双双爬上去。
最后搞得我大叫,像要去杀人,却被她紧紧箍住,像根儿绳子在勒,勒酥了我的骨头,勒断我的喊叫。可这样一来,我就更想喊了。
等我喊透了歇息,师傅进来,开了灯说:“好徒弟,你他娘的像头牲口,跟我家的老黑驴一样。棒棒,真不赖呆!”
女人并不避讳,找到我的衣服,乱摸。师傅从兜里掏出一管白面扔给她。她就赤裸裸下了床,拿了烟盒拽出锡纸。师傅兴冲冲过去,踢了她屁股一脚说:“滚,外边抽去!”
女人抱着衣服就跑掉。
我说:“师傅我也要抽!”
师傅把手伸进兜,转过身。我凑到他跟前。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突然回手,给了我一个狠狠的、响亮的耳光。这个嘴巴,打得我一阵儿昏眩,晕头转向,更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师傅这是怎么啦?我捂着脸问。
他的嗓门更让我全身发抖:“跪下!”
我真是摔进了烟云雾里,但还是屈膝在地。火辣辣的面孔,把我从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中,慢慢拽回到臭烘烘的小旅店来。
“为什么打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
“现在你已经快上毒瘾了,知道不!听好,从今往后,你死也不能再抽了,能记住吗?”
师傅揉着手掌。
“那您当初,为什么教我抽?”
“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后边的路上险恶。不光是贼人强盗,更多的是扯你拉你的,用毒品诱惑你的。我是先让你过了这道神秘的鬼门关。以后我不在了,你就得自己管束自己了。否则,甭说回北京见你爹娘了,就是云南,你也走不出去。记性在吗?”
“在,在,记住了!”
“我跟你有缘分,知道吗?”他抽起烟来。“这地方的白市张狂得很,像你这等路数鸟人,什么都要见识,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琢磨着玩玩,什么都咂摸着想尝尝的主儿。玩着玩着,咂摸咂摸着就玩进去啦,你不是出来作死的吧!”他破口大骂,双目圆瞪,浊泪汩汩。“哎,收你这么个徒弟,也真够我费神儿的,多少年了我还没操心过什么。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明儿就要分手了,你也给不了我什么,我也教不了你什么。我只给你留下这个嘴巴子,让你记住我一辈子。我今儿要不为你关了白粉这门,敢说你走不出西双版纳,就沁透了毒品。那时想戒,你都戒不了了。我敢说。给。”他递给我一包白面。
“还让我抽啊!?”我莫名其妙,没敢伸手。
“傻蛋!不是抽的,是洗鸡巴用的。快去,染上病,也照样要你兔崽子的小命。大意不得。”那一宿觉,是我有生以来最舒服,最轻松,最沉静的,或说那才叫睡觉。没了天,没了地,没了鸡毛小店,没了世界。
第二天起床,我把这种感觉告诉师傅,师傅说:“是毒品的作用,什么叫毒,这就是毒。先让你知道知道它是好东西,上了瘾,再控制你,这是最毒的。所以你要记住,向我发誓,时刻想着我留给你的嘴巴。嘴馋了,就摸摸脸蛋子。去,好生上路吧!”
我出门,一个女人进了屋,师傅把门插上。
上了山间的路,空气爽朗。路两边尽是盛开着红花的凤凰树,间杂着油棕和蒲葵。周身轻松无比,也不拦车了,甩着步子向北走下去。轻松得好像一下子我能走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