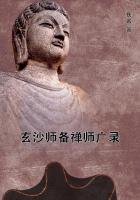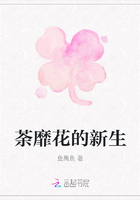樊 星
“汉味小说”,即以具有浓郁的武汉地方风味的文学语言描绘武汉风土人情的小说,它无疑已成为当代地域文化小说、当代城市文学总格局中颇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方方、池莉两位女作家便是“汉味小说”的代表作家。
方方和池莉,分别以《风景》和《烦恼人生》取得了“轰动效应”,其时在1987年,“寻根热”和“新潮小说热”已经由热转冷,作家们又在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评论家也由谈论“伪现代派”进而思索“当代中国作家的选择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品格”这样的时代课题。《桑树坪记事》获得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人们关于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又一次讨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景》和《烦恼人生》偶然也是必然地问世了,轰动了。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远超过了这两位作家以前的任何作品。一时间,评论家们纷纷争说“展示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新潮流,的确,这两部中篇极其朴素又极其深刻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平民百姓毫无诗意的艰难人生,比起学习西方现代派手法,以夸张、变形手段揭示人生悲剧本质的作品,自有更触目惊心的震撼力。而两位作家的创作谈也是这么表达她们的情感和她们所意识到的主题的——方方写道:“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和“拼命奋斗”的艰难,产生了七哥那样的人物,“他们采用了别具一格的奋斗方式和生存技巧”,“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26]这番话中有深长的叹息、真挚的情感。而池莉,也努力要通过印家厚的形象塑造表达这样的感悟:“我们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坚韧的生活力量。用‘我们不可能主宰生活中的一切,但将竭尽全力去做’的信条来面对烦恼,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27]。——这一切,是对小说的社会意义的深刻阐释。
但显然还有另一面,对于武汉的读者,“河南棚子”、长江轮渡、武汉方言,比起《桑树坪记事》那样的作品,无疑更多一层亲切感。外地的读者也会从小说中感受到武汉人特有的脾性和风俗。这,便是小说的地域文化意义了:独特的风俗人情,独特的方言,对于优秀的地域文化小说,绝不仅仅是某种点缀,某种类似于调味品或舞台道具的东西。事实上,它们对于营造小说的氛围、塑造人物的特性、传达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常常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老舍的“北京故事”、赵树理的“山西农村小说”……这些各具鲜明特色的文学世界之所以在文坛上成就独特,绝不仅仅因为主题提炼、题材剪裁、技巧适用的各具匠心,还因为作家们把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的独特脾性(如湘西人的坦荡野性、北京的人淳朴知足、山西人的幽默精明等)以及孕育出那独特脾性的水土之性(湘西的青山绿水、北京的逼仄胡同、山西的厚厚黄土)也活生生地揭示了出来。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神采各异的民风民俗,不同的民风导致了不同的文风——这也算一条文学的定律吧。(至于同一地方作家风格的不同与作家主体选择的微妙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了。笔者无意做“地域文化决定论”者。)
因此,《风景》中的河南棚子地带人的粗糙人生既具有对国民劣根性乃至人的本性的冷峻逼视的社会意义,也是对武汉人民风粗鄙层面的描绘。《烦恼人生》中印家厚那时而忧愁时而欣慰的心理曲线既是对普通人平庸人生的生动揭示(读这部作品时,我常常不禁想到莫泊桑、契诃夫笔下那些浑浑噩噩又令人同情的“小人物”),也传达出武汉人善于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的民风气息。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女作家对此缺乏足够自觉的意识罢了。这一点,有她们的创作谈做证。还有她们的作品——毕竟,与她们稍后写出的“汉味”更浓的《黑洞》《落日》和《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作品相比,《风景》和《烦恼人生》的“汉味”就淡多了。由此可见,有没有充分自觉的地域文化意识,对于作家能否充分展示独特的地域风情,颇为重要。当然没有必要要求作家都树立自觉的地域文化观,许多艺术精品也与地域文化意识无关,例如老舍的《猫城记》、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那样的作品。但写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富于诱惑力的话题。况且当代文坛上自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和贾平凹的“商州世界”别开生面以来,各地作家经营地域文化小说,已成空前盛况:文学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期如80年代的中国文坛这样有如此多的作家创作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地域风情图卷。
但这一切很快就变了。1988年,方方的《黑洞》发表。这篇小说的主题与《风景》一样,写小市民生存的艰难,但《黑洞》中的“汉味”就浓多了:陆建桥们的粗鄙与幽默和小说语言的俏皮,是地道的武汉特产。《黑洞》的风格不似《风景》那么凝重,与浓郁的“汉味幽默”——那化烦恼为俏皮话的怪味幽默——有密切关系。1989年,池莉的《不谈爱情》问世。此篇仍然是“烦恼人生”的社会主题,但“花楼街文化”的描写使全篇平添了“汉味”——花楼街的“风骚劲儿”、花楼街人的精明与泼辣……《不谈爱情》因此比《烦恼人生》更多了一层文化氛围。1990年,池莉的《太阳出世》和方方的《落日》相继在《钟山》上亮相,前者写了小人物的生活烦恼,也写了武汉人喜欢显、性情浮躁的一面,后者写了一出家庭悲剧,还写了武汉人暴躁又俏皮、精明也散淡的风习。尤其《落日》,堪称“汉味小说”的典范:一部长篇,写了形形色色的武汉市民,写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繁华、热闹又粗俗的“四官殿—六渡桥文化”,而且,通篇以纯熟的“汉腔”写成。到了1991年,池莉又推出了《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此篇一改“烦恼人生”的主题,画出了一幅轻快、幽默、富于喜剧色彩的“武汉市民消夏图”,从武汉的酷暑写到武汉的小吃,从市民酷暑中的俏皮闲聊写到街头的乘凉大军……在“汉味小说”中也独树一帜。
这样,就有了“汉味小说”的话题。方方、池莉,还有擅长写“汉正街文化”的吕运斌、王仁昌(任常)以武汉作家特有的风格创造了小说世界的新品种——“汉味小说”,填补了中国小说画廊中的一个空白,也使“汉味小说”成为与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王朔的“京味小说”,王安忆、程乃珊、俞天白的“海味小说”,冯骥才、林希的“津味小说”,叶兆言的“宁味小说”争奇斗艳的又一枝奇葩。这样,当理论家们今后再谈论“城市文学”这个似乎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话题时,他们便有了“绚丽多彩的中国城市文学”的大量资料了……
汉味(一):“九头鸟性格”
武汉的评论家们在探讨武汉文化的特性时,常有“不好把握”的叹喟。有的干脆以“没有特色”作结。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武汉地处“九省通衢”,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居民来自八方,自然难显纯色。一套“民居”邮票十几枚,有北京、上海,有湖南、安徽……偏没有湖北武汉。
但武汉人又毕竟与众不同。这就奇了。
常言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说的是湖北人精明,好像比别人多几个脑袋一样。当代作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中有一节《白浪街》,写一条街分为三省,三省人有三省人的特性:河南人“勤苦而不恋家,强悍却又狡慧”,陕西人勤劳、保守,而湖北人呢?则是“待人和气,处事机灵……一张嘴使他们财源茂盛。”这便与“九头鸟”的精明契合了。武汉是著名的商埠,商业文化必然在武汉人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吕运斌、王仁昌的“汉正街风情”专写全国闻名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主人公、那些精明能干的个体户(如王仁昌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风流巨贾》),就十分突出地显示了武汉商业文化的本色。方方、池莉的小说中的故事,多以汉口闹市区为背景,人物除了产业工人,多在肉食店、照相馆、公共汽车上供职。这样,他们的口语中颇有商业文化色彩,也就很自然了,例如:“找老婆就得找这样的。不光自己吃不了亏,而且还能占到别人的便宜。”(《黑洞》),“也不晓得丑卖几多钱一斤?”“弄不好他把你卖了,你还得帮他数钱。”“淡淡得如同哗哗的自来水,八分钱一吨,流走算了。”(《落日》)武汉人精明,会算计——吉玲的母亲“具备了几种面目”,该撒泼就撒泼,该体面也能体面,软硬兼施,降服了女婿庄建非(《不谈爱情》);丁如龙抛弃生身老母,却常有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点拨乃兄也用的是“引而不发”的招数,精明得到了阴险歹毒的地步(《落日》)……精明用于经商,是生财之道;用于处世,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算计,甚至是夫妻之间、兄弟之间、母子之间的算计,这就可悲了。
但又有一句话,叫作“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下江佬。”论精明,论做大生意,武汉人比不上江浙人。江浙一带自古出名士,也出富商。武汉不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或许是:武汉人身上除了南方的精明,还有另一面,那便是北方人的泼辣。武汉人脾气暴躁,好骂人,是出了名的,有俗语为证:“湖北的老子,四川的娃子”。武汉人性格中的大怒大喜、忽暴躁忽幽默、能屈能伸、能干能湿、“高级宾馆进得,大马路睡得”的泼辣劲似乎与武汉地区的天气时冷时热、晴则久晴、雨则淫雨有关。你看印家厚:一会儿为烦恼人生长吁短叹,一会儿又以忆苦思甜自我安慰,而且,从沮丧的深渊到愉悦的峰顶的循环周期极短,频率极快;陆建桥亦然:牢骚劲上来了就“想站在江汉路的立交桥上顶天立地地骂一通娘”,不是吗?“汉口人到哪儿不都骂骂咧咧的?要不岂不枉为汉口人?”作为服务员,“哪个没同顾客吵过架?全武汉能找出一个这样的不?……他若对顾客热情得如一盆火,顾客不把他当神经病才怪。顾客早就被吼惯了,怠慢惯了”。但这又并不妨碍他与女同事打情骂俏、“骂骂咧咧、说说笑笑”(《黑洞》);赵胜天、李小兰办喜事,婚礼尽量豪华,看似高雅其实俗不可耐,游行显派的路上与人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更叫人啼笑皆非,恩爱起来如胶似漆,烦恼一上来就闹着离婚(《太阳出世》);丁如虎刚才“拍腿跌脚地骂了老娘”,一转身又心安理得地打起了呼噜,丁家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祖孙之间,成天骂骂咧咧,以此转嫁烦恼也以此彼此开心,多少年如一日地打发光阴(《落日》);甚至爱人之间的亲热、邻里之间的玩笑、同事之间的调侃,也无不粗鄙得惊人、粗鄙得可笑(例如《落日》中成成与汉琴的拌嘴——“放你妈的屁!”“我妈早死了,没得屁可放得。”)《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邻居女人们夸猫子好,“又体贴人又勤快,又不赌不嫖”。猫子答:“你们又不接客,么样得我不嫖啊?”以及《黑洞》中陆建桥与柳红叶的粗鄙调侃,虽常常围绕性语码展开,但因出于率真粗鄙的习惯,又加上并无“理论联系实际”之举,因而虽不堪入耳却也足以令人捧腹……至于武汉人的言行举止呢,一是嘴巴厉害,好生了得:“一张利嘴不好惹”,“损起人来……凭着那两片薄唇,活生生地能刮下对方的皮”(《黑洞》),吵起架来,“话来得比曹正兴的菜刀还厉害”,而且可以惊心动魄到“死人翻船”的地步(《落日》);二是动作夸张,身手不凡:“拍腿跌脚”地骂人,“恨不能用砍柴刀劈死”对手(《落日》),待起客来则是“大碟小碟上个不完”(《不谈爱情》);三是喜欢热闹,乐此不疲:“人活着就得热闹,不热闹闹的跟躺在棺材里有么事区别?”《落日》所以办婚事就要“显”(《太阳出世》),就要“豪办阔娶”,“人不就是争口气么?”(《不谈爱情》)办喜事讲究热闹,办丧事亦然。(《落日》)中有生动的描绘:又是大宴宾客,又是放哀乐、致悼词;还有夏夜乘凉的盛况:“长长一条街,一条街的胳膊大腿,男女区别不大,明晃晃全是肉。”(《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下棋也好,聊天也好,总是人声鼎沸、豪兴大发、昏天黑地。嘴巴厉害,动作夸张,既是商业文化的熏陶塑就,也是湖北人“好战喜斗”的风俗遗传使然[28]。
武汉人是精明的:他们善于吸纳八方奇气(武汉小吃便是典范:江浙的甜食、湖南的辣味、北方的面食、四川的特产……蔚为大观),他们擅长谋划算计,为达目的削尖了脑袋钻营——这一点上,颇像江浙人。
武汉人又是泼辣的:他们的吃苦耐劳,能为了生存去做一切卑微的苦活,粗犷豪放地干活、吃喝、骂人、斗狠——这一点又很像河南、山东人。
武汉人是务实的:他们都怀有极实际的目标,为了发财、为了房子、为了升官、为了后代,一点一点地积聚力量、精神抖擞地投入竞争——这一点颇近湖南民风。
武汉人又是洒脱的:他们一面奋斗,一面把面子、生死这些神圣的东西看得很穿——“汉口街上常能见到的那种最不知忧愁的一类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什么事都能想得开。怄气永远都怄不长。随和得仿佛没得主张。但实际上他是极聪明的……”(《落日》)印家厚、陆建桥、丁如虎父子对奖金、处分、婚姻、牢骚,都有这么一种既重视又不执着的洒脱劲儿,似乎与“阿Q精神”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也的确是烦恼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心理调节机制。于是有了别具一格的“汉味幽默”,变烦恼为笑料,化平庸成神奇。——这方面,又与四川人的“川味幽默”相通。
这便有了武汉人的多副面孔、多重性格。便有了武汉民风的“杂糅”特色。也许唯有这种能苦能乐、能干能湿、刚柔兼济、进退自如的多重性格,才能适应在这“九省通衢”世界的生存吧。又精明又粗鄙、也泼辣也幽默——该如何给这种民风民性一个精确而形象的概括呢?想来想去,还是称之为“九头鸟性格”吧。九头鸟,除了精明的原义以外,不是也给人以某种奇特、怪异的感觉吗?九头,转而比喻多副面孔,好像也说得过去吧。更何况武汉人素好“九头鸟”的称谓,以至它成了报刊专栏、酒家饭馆和某些商品的响亮大号呢!
汉味(二):“汉腔”
武汉人的独特民性使武汉方言也极有特色。常言道:“京油子,卫嘴子。”北方城市语言中的油滑感、尖刻感,是城市市民文化特质的自然表现——那份找乐心态、那股哗众取宠的风骚劲儿、那种耍贫嘴的粗俗味儿,在邓友梅的《那五》《烟壶》,冯骥才的《怪世奇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武汉方言,也颇有那份油滑感、尖刻感。所以,武汉方言的粗鄙特质,与北方方言相近而与同一纬度上的“苏白”[29]相去甚远。
方方、池莉经营“汉味小说”,一方面直接从武汉平民生活中汲取活生生的方言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对话,给人以在生活的原质感,另一方面努力自然地化方言为别具表现力的“汉味文学语言”。试分述如下:
1.武汉人精明又粗鄙,而且泼辣也幽默,这一切在人物对话中体现了出来:
《落日》中的祖母看不惯孙媳汉琴的风骚,跺脚骂她像花楼街的婊子,汉琴的回答是:“我是婊子,那你的孙子是嫖客,你是嫖客他太,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既是反击,又并不直露,而是很快按照逻辑作出令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推论。使对手气上加气又无懈可击。武汉人吵架,惯于施行这一伎俩:“你骂人其实是连带骂了自己”,这样的语言够得上艺术了。
《黑洞》中柳红叶与陆建桥的打情骂俏亦然:
柳:“去你妈的,邪贷萎子,一肚子坏水。”陆:“多少讲点精神文明嘛。再就是要注意选择器物。坏水装在萎子里,百分之百漏得精光。”柳:“你那张嘴今天早上搽了几两油?”陆:“油没搽,但是昨晚同老婆练习了一夜。”
一切都是合乎逻辑推理又叫人感到荒诞不经的。一切都相当粗俗又十分俏皮。而在这种“逻辑推理法”和“跳跃性思维”中,不就显出了粗鄙中的精明么?上一节所引猫子与邻居女人于“嫖”的一段玩笑话,亦具异曲同工之妙。
甚至在极严峻的场合也自然而然地玩起了幽默——《落日》中的成成这么劝说祖母放弃自杀的念头:“太,莫说得骇老百姓。要我说呀,死活都差不多的。实在想不开,长江也没盖盖子,江边也没得警察守着不让去。就怕太一看,好大的水呀,骇不过,又跑回来了。”笔者加了着重号的话在武汉已成人们的口头语,多用来气人、激人,但这些口头语本身所具备的幽默意味又是以令人解颐。而当丁如虎、丁如龙兄弟在面临害母事发的关头,彼此推诿责任时,丁如龙的比喻也是不伦不类又无懈可击的:“建议是我提的,但你是长子,决定权是你啊?如果有人建议中国把云南广西送给越南人,中国政府同意了,你说是建议的人有错还是同意的人有错?”武汉人是颇擅长讲无懈可击的歪理、作啼笑皆非的比喻的。实在是粗鄙,又实在是精明。而这种精明、这种幽默、这种油滑、这号洒脱,又颇与“川味幽默”(其典范是“谐剧”)一脉相通,也与海派文化、吴越文化因子中“对一切正统的一种调侃,一种挑战”[30]的幽默腔相应。但“川味幽默”和“吴越幽默”又没有“汉味幽默”那么粗俗、率真到无遮掩的地步,叫人听了又气恼又忍俊不禁,这一点,从“汉味幽默”中的粗话特别露就不难窥见一斑。
2.为了表现“汉味”,作家们自然要创造一种“汉味文学语言”——既有原质原味的“汉腔”,又能具有文学的品格,使外地读者也能读懂。这方面,除了对某些地域性特别强的方言俗语加上必要的注释,就要看作家提炼方言、使方言与普通文学语言水乳交融方面下的功夫了。
《黑洞》中这么描写陆建桥的眼睛充血:“眼白上的红丝像地图中的公路线。”《落日》中这么写王加英的繁忙:“她像个陀螺,一天到晚地转个不停。”《不谈爱情》中这么形容白裁缝夫妇的老迈:“老得像对虾米。”——这种夸张的比喻在武汉人品评人物时是极其普通的:它折射出武汉人善于比喻、善于夸张、善于取乐的民风。有那么点“损”,但也实在传神。
《落日》中这么写成成“坐山观虎斗”(武汉人的说法是:“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理:“成成性情豁达开朗,不管祖母跟汉琴吵到什么地步,都影响不了他的情绪。成成觉得女人在一起天生就是吵架的命,就跟好斗的公鸡关在一起一样。成成想女人若不吵架肯定会浑身筋骨酸痛,所以一旦吵开来,成成便只当她们在治疗自身的筋骨。既如此,有什么可烦恼的?成成很善于为别人想。”把女人吵嘴比作公鸡好斗,把闲事不管比成善解人意:这便是“汉味幽默”的魅力。这样的心理描写语言极好地传达出了武汉人洒脱、幽默的心境。
再看《落日》中一段写武汉人情绪的文字:“汉口的夏天,热得人们几欲扒皮。……人若在这样的室内住一个汉口的七月之夜,第二天除了被蒸闷熟了之外,恐怕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还有《黑洞》中的一段:“车船挤得让人觉出全武汉三镇的人都在距离自己最远的地方工作。若能在这些人中找出一个不骂武汉交通的人那才是比建造金字塔还大的奇迹。倘有一任市长能解决武汉的交通问题,百姓们把他当祖宗供起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本正经的夸张,想象奇特而新颖,也许舍此便不足以表达武汉人好“显”、善夸张、情绪强烈的民气吧。
油滑又俏皮、尖刻又传神、夸张又新颖:这便是“汉味文学语言”的特色所在。比起冯骥才、林希的“津味文学语言”来,各有特色:冯骥才、林希的语言更富于说书人“口若悬河”的铺排,方方、池莉的语言则更平实、更富于日常生活的情趣些。将武汉方言化入文学作品,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更富于俏皮、夸张、想象新颖、比喻奇特的生动色彩无疑是“汉味小说”对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可贵的贡献。
上海作家程乃珊曾对“海派腔”作过这样的表述:请听下面一段对话,并加以比较:
“‘今天的活动怎么安排?’这是正宗的讲法。”“‘今朝啥节目?’典型的海派腔。”[31]善于调侃,化严肃为幽默,变烦恼作笑料,这是“海派腔”的特点。“汉腔”有过之而无不及。
遇到挤时,北京人习惯说:“借光、借光!”叫人听了舒坦:因为话中透着谦虚、厚道。而武汉人的习惯则是扯着嗓门大吼:“擦油!擦油!”吓得人避之唯恐不及,但回头看,吼者其实身上并无油污、手中也没有油瓶。他不过是为了争一分空间而制造一点惊慌而已。一旦目的达到,他便什么都不计较了。
汉味(三):武汉风景
对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现常常与描绘地方特产、风物分不开。沈从文、老舍、汪曾祺、贾平凹各有千秋的地域小说中都有大段大段关于地方风景、历史掌故、民俗民风、特产器物的精彩描写,这些描写既营造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时间的流逝,天灾人祸,每天都在冲刷着文化遗产、毁坏着历史的面容。到了20世纪,现代化浪潮在将享受带给世界的同时也对绚丽多彩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以至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成了20世纪的一个文化主题。尽管如此,许多遗产已随风而逝了。许多作家只好在寻根的过程中凭想象去留住那一份传统的辉煌。当代地域文化小说的优秀之作都既有对人的命运的深思,又有对地域风物的描绘——《那五》《烟壶》《美食家》《夜泊秦淮》《供春变色壶》《横活》《斗鸡》《商州》《商州初录》……莫不如此。
“汉味小说”中,《风景》写了“河南棚子”的粗糙、阴暗,基调最暗。除此而外,《不谈爱情》写花楼街(“从前它曾粉香脂浓,莺歌燕舞,是汉口繁华的标志。如今朱栏已旧,红颜已老……花楼街始终弥漫着一种破落气氛,流露出一种不知羞耻的风骚劲儿”);《落日》写武汉昔日的繁华(“茶馆有等级之分:上流人物去怡心楼、忠信楼、汉南春、洞天居,下等人呢?收荒货的去宝善堂茶馆,挑粪的去流通巷,车夫去铁路外”;四官殿一带“扎灯扎花的手艺人极多”;江汉路、六渡桥“新市场”的热闹繁华……);《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写武汉人的时令小菜、十多家的有名小吃……都写得各具情致:或破败巷凉,或追怀忆旧,或胃口大开,都写出了武汉人喜热闹、爱繁华、图嘴巴快活的特性。遗憾的只是写得太少、太略,不如《烟壶》《商州》那么浑厚、精细,在这方面,还有待于武汉作家努力。
“花楼街文化”“六渡桥—四官殿文化”,加上王仁昌的“汉正街文化”,无论是“玩文化”,还是“个体户文化”,都是武汉人爱热闹、慕繁华、粗鄙又精明的民性的证明。瞧,原来“武汉文化”也包含了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多的分支!由此想开去……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也是与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关的地方。武汉的风云历史与武汉人民风的强悍、务实、躁动之间,该有多少人间活剧可写!还有武昌的黄鹤楼、东湖风景区,还有汉阳的归元寺,还有那些喧哗又宁静的小巷,还有许多也许只属于武汉的传说与掌故……是的,还有许多空白可填。再过五年、十年,“汉味小说”会有怎样的新收获呢?毕竟,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汉味小说”已迈出了可惊喜的一大步……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