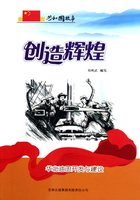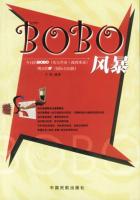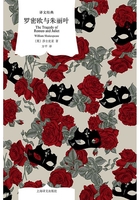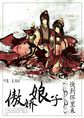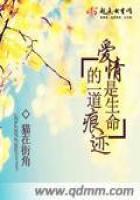王春林
对方方《乌泥湖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的解读必须从她发表于1990年的中篇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起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祖父在父亲心中》乃是《乌泥湖年谱》的雏形。将二者作一粗略的比较,即不难发现《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的“父亲”与处于《乌泥湖年谱》中心位置的丁子恒的一致性。丁子恒与“父亲”一样生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与最小的女孩,且最小的女孩,即《乌泥湖年谱》中的嘟嘟与《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的叙述者“我”都出生于1955年;丁子恒与“父亲”一样都是从长江下游局调至武汉的高级工程师,且都一样地喜欢古诗词有着较为深厚的古诗词修养;丁子恒与“父亲”一样都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侥幸漏网者,且原因都一样地是因为名额已满之故。在《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父亲”虽然一次也未被批斗过,但却被一个叫王洪昌的同事领头抄过家,《乌泥湖年谱》中的丁子恒也同样未被批斗过,但却被一个叫王志福的同事领头抄过家;父亲曾经在小哥哥的自行车上写了语录牌,而三毛则在丁子恒的自行车前嵌上了语录牌;“父亲”与丁子恒都曾经在被抄家前让二哥亦即二毛把相册上有可能被指责为罪证的相片全部撕下焚烧。从以上所罗列的两个小说文本大致相似的情形,的确可以发现《乌泥湖年谱》与此前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存在着相当重要的内在联系。从方方的小说创作历程看,可以说对知识分子内在精神世界的探寻与表现始终是她极为关注的重要思想命题之一。此处所提及的两部作品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小说文本。应该说,在方方的小说写作历程中,《祖父在父亲心中》是一篇相当重要的小说。原因就在于,在这篇小说中,通过“祖父”与“父亲”形象的反衬对比,方方继她曾引起极大反响的以探究表现市民生存境遇而格外引人注意的《风景》之后,首次将自己的笔触伸向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在“祖父”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高贵气节的映衬下,“父亲”精神世界之猥琐怯弱就显得相当突出了。然而问题在于,在血管里流淌着“祖父”血液的“父亲”竟何以会与自己的前辈形成如此之鲜明的反差呢?答案当然离不开“父亲”所置身于其中的一种相对畸形的社会文化语境,而《祖父在父亲心中》这一小说也已经在这一方面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挖掘探寻与艺术表现。然而,或许是因为受制于中篇小说这种篇幅较小的文体制约的缘故,更或者是因为写作《祖父在父亲心中》时的方方自身对自己所欲探究表现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这一命题的思考认识尚未成熟的缘故,《祖父在父亲心中》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探索实际上并未达到透彻的尽如人意的地步。但从《祖父在父亲心中》与《乌泥湖年谱》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点上,则可以说其实在写作发表了《祖父在父亲心中》之后一直到动笔写作《乌泥湖年谱》这一几乎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方方其实一直没有放弃过对知识分子精神命题的深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可以武断地说,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探究与思考业已构成了方方无以脱解的一种思想与艺术情结。在这个角度上,则又可以把《祖父在父亲心中》看作是《乌泥湖年谱》的前奏曲,在《祖父在父亲心中》中首次郑重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问题只有在写出《乌泥湖年谱》之后才算得到了一种较为圆满的解答。假如依照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父亲”这一形象约略地等同于丁子恒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认真地读过《乌泥湖年谱》之后,我们才可以真正地明白“父亲”也即丁子恒的精神世界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猥琐与怯弱的。然而《祖父在父亲心中》很可能是由于中篇小说这种文体形式制约的缘故,作品以与“祖父”形象相对比的方式只是集中着力于“父亲”形象的展示与刻画,到了《乌泥湖年谱》中,虽然丁子恒依然处身于文本的中心位置,但小说所描写展示的生活场面与涉略塑造的人物形象却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扩增。在这个意义上,则可以说只有到写作《乌泥湖年谱》的时候,方方关于知识分子精神命题的思考才呈现出了某种成熟的姿态,只有在完成了这部近期内难得的小说力作之后,方方意欲以“年谱”的形式梳理展示,并表现当代知识分子生存困境与精神谱系的创作意图才得到了一种相对完满的实现。
在“文革”后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方方《乌泥湖年谱》所明确标示的1957年至1966年十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进行反思表现的小说作品是层出不穷的。1957年至1966年,方方以年谱形式记录的这十年,对于如丁子恒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异常残酷无情的严冬季节,是他们从肉体到精神惨遭蹂躏糟践且不复再有人格尊严的一个时期。虽然说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被贬抑并非起始于1957年,虽然从作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背景的整风运动起始,知识分子就早已踏上了一种万劫不复的苦难历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惨痛人生经历才为作家对之进行存在性的审视与表现并从中透视出丰富复杂的人性形态与人性内涵提供了艺术探询的可能性。唯其如此,“文革”结束后的小说界才会大量地涌现出许多探寻表现当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作品来。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许多表现当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小说作者中绝大多数都曾经如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有过类似的现实遭际。这也就是说,他们乃是基于自身的生存经验而进行自身文学世界的构建的。在这一方面,右派作家的小说写作乃是一片极其突出的艺术风景。应该说,由于这些作家一种惨痛的亲历性经验存在的缘故,他们的创作显得格外地真切而又沉痛异常,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受其亲历性经验制约的缘故,这些右派作家们在写作中又会自觉其实更多是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进行一种自我矫饰与自我美化。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一种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文化心理将自己美化为某种苦难的基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倒产生了一种美化苦难并进而消解苦难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自审性文化心理的匮乏乃是从根本上制约这些右派作家(此处必须强调一点,上述推论只是针对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右派作家群而言的,我们同时也并不能否认其实仍有个别作为特例的作家,比如王蒙的客观存在。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试图进行抽象的文化或文学概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点,诚如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所言:“黑格尔曾说具体的普遍性不同于抽象的普遍性,前者可以将特殊性和个体性统摄于自身之内。我认为这只是存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而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实际上,普遍性愈大,它所能概括的特殊性和个体性是愈少。”)[47](信哉斯言!)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无法在小说写作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原因所在。而这,也就为后来一些作家在这一方面的非亲历性写作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一种艺术可能性,虽然这一方面的小说文本在迄今为止的文坛上还甚为罕见。就笔者所涉略的阅读范围而言,在这一方面最早作出尝试的乃是两位女作家,一位是方方,另一位是王安忆。方方《祖父在父亲心中》发表于《上海文学》1990年第4期,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则刊发于《收获》1990年第6期。虽然从发表时间看方方似乎略早于王安忆,但在社会上形成更大影响的却是《叔叔的故事》。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借助于较叔叔低一辈的叙述者“我”带有强烈审视色彩的视角对在“文革”后一度成为汹涌大潮的右派作家们小说中的右派自身形象进行了彻底颠覆性的全新观照与塑造。在这一小说文本中,在右派作家笔下几乎形成一种模式化形象系列的右派知识分子自身类乎于苦难基督般的神圣色彩几被完全消解。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的自身形象遭受了一次事后很难再重新得以复原的致命伤。或者说,正是方方与王安忆(值得注意的一点乃是王安忆的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她们这两部中篇的写作,才把已基本定型化了的右派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与艺术蕴含又向纵深处推进了一步。之后出现的另一部值得注意的非亲历性右派知识分子小说乃是尤凤伟的中篇小说《蛇会不会毒死自己》(载《收获》1998年第4期)。在发表的当时,该小说就曾以其对右派知识分子迥异于其他亲历性作品的独特勘探与表现引起批评界的注意[48]。现在当笔者正在写作此文的时候,谈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国1957》,方才知晓《蛇会不会毒死自己》乃是尤凤伟这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中国1957》当然也是取非亲历性视角(虽然作品采用的乃是虚构出来的一种足以乱真的第一人称自传方式)表现右派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与精神世界的一部重要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该小说与我们此处所主要谈论的《乌泥湖年谱》乃构成了2000年度以非亲历性方式创作的以探究表现右派知识分子的生活其实更主要却是精神心理发展历程的长篇“双璧”。由于篇幅的关系,此处不准备过多地讨论《中国1957》,但对包括该小说在内的这些非亲历性右派知识分子小说阅读的一个直接结果,却使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类作品与那些有着右派生活体验的右派作家们的亲历性作品显著的区别差异的存在。在我看来,亲历性写作最值得肯定的乃是作家一种生存体验的真切性,这种真切性因为作家自己所确有过的切肤之痛而往往可以轻易地牵制打动读者的心灵。但另一个方面,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有着一种个体所独有的一己的生存体验,所以这种体验却又往往会不自觉地遮蔽生活的普遍性,遮蔽其他有类似经历者肯定迥异于作家自己的另外的生存体验,并因了这种体验局限制约的缘故,而无法跳出自身之外取别一种更阔大的视野来对自我的经历与体验作更深刻的观察与反思,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与此相反,非亲历性写作虽然似乎少了一种体验的真切性,似乎丧失了一种实在的切肤之痛,但却可能因为置身于事外因为某种必然的距离存在而对事物本身产生一种更为全面立体也更具普遍性的观察与反思。与亲历性写作相比较,非亲历性写作对事物的表现既可能更为客观冷静,同时也有可能对事物进行一种因避免了自我因素的缠绕而更加冷峻透彻的独具一种清明理性的批判审视。我们在此处不准备也无必要对亲历性写作与非亲历性写作作一种高下优劣的判断,而事实上,从中外文学史的实践情形看,则应该承认,无论是亲历性写作还是非亲历性写作,都产生优秀的文学精品,这也就是说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对这两种写作方式来作一种优劣高下之比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比较意义上,辨明这两种写作方式所各自具备的特征或优势而已。但就本文所讨论的以探究表现右派知识分子生活为基本主旨的小说范畴而言,则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亲历性写作,而只有到晚近一个时期才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非亲历性写作,而这些非亲历性写作与此前盛行之亲历性写作相比,又确实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乃构成了对右派知识分子小说写作向纵深度的拓进的一种有力推动,因而其意义上与价值也必须得到充分的认识与估价。而这,也正构成了我们进一步探究这部《乌泥湖年谱》的一个基本前提。
读《乌泥湖年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强烈荒诞感的存在,虽然《乌泥湖年谱》并非一部荒诞小说,虽然方方所采用的也确是一种客观冷静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之所以会有强烈荒诞感的产生,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作品所欲探究表现的现实生活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感。那么一群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怀抱着修建世界上第一大坝——三峡工程的美好憧憬,从全国各地集聚到武汉,集聚到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把自己全部的热情和聪明才智都投到了这一伟大的工程的建设过程之中。却谁知满腔心血皆付之东流,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文革”开始时,不仅期待中的三峡工程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且活动于小说中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这些预期中三峡的主要设计与建设者们,则不仅壮志未酬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且还几乎全部无以逃脱地陷入了由于政治运动的数度介入干扰而形成的巨大人生苦难之中。挣扎于专业志向的追求与现实生活中不断袭扰着的政治运动这二者的尖锐矛盾冲突之间的不可逃脱的现实生存处境也就内在地规定着他们的灵魂与精神那或彻底毁灭或彻底异化的必然归宿。苏非聪,一个仅仅因为讲错一句话就成为右派的天真直率的知识分子。本来,同在总工室工作的王志福已差不多被内定为右派,但苏非聪却因为对划右派分子都要规定指标名额的反感而“愤然”地发了一句牢骚。不料这牢骚却被急欲“立功赎罪”的王志福揭发了出来,结果反而是苏非聪自己因这句不慎之言而罹祸成为乌泥湖家属区最早的右派之一。林嘉禾,同样是一位正直热情且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即使被打成了右派,还关心着工程建设,在被监督劳动三年之后重见丁子恒时,仍然询问探讨着坝址合适与否的问题。位卑未敢忘国忧,林嘉禾的行为典型地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传沿已久的优良传统。然而,林嘉禾的右派身份不仅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自己的儿子林问天的生命历程。孔繁正,是被林院长特地从北京请来的地质专家,本来在1957年时并未被打成右派,但却因为他1960年在目睹了“哀鸿遍野”的生存现状之后,率直反对三峡工程在这样一种并未具备上马经济条件的时候匆促上马,而被扣上了“比右派更反动”的“右倾保守主义”帽子,被打入另册,最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送到陆水工地劳动改造”。上述置身于苦难中的这几位知识分子罹难的共同原因,都在于他们对于自我人格尊严,对于自己所追求事业的一种出乎本能的自觉维护。在这一维护过程中,自然表现出了对于不合理政治运动的强烈抗争精神,他们之惨遭厄运也正与此直接相关。所以不仅自身罹祸,连自己的家人子女也都未能幸免。但是,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刻画并非《乌泥湖年谱》最值得肯定的成功所在,虽然这些形象的出现对于方方从整体意义上完成对以多样态方式呈现的当代知识分子复杂精神构成的描写表现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根本原因在于,如苏非聪林嘉禾这样的形象,在右派作家们的亲历性写作中已经为我们所司空见惯了。小说最有创造性价值的乃是对诸如丁子恒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同时也需要强调一点,除了如苏非聪丁子恒们这样作家明显持赞同或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之外,小说中也出现了诸如王志福与何民友这样的知识分子败类形象。这样一些形象在右派作家的亲历性写作是甚为少见的,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方方的独特创造。然而,从小说文本实际看,可能是由于作家潜意识一种对此类形象难以排解的厌恶反感发生作用的缘故,作家未能更理性地深入到此类人物的内心世界中,未能展示表现出此类人物其实同样应该是十分复杂的精神构成,令人遗憾地把他们写成了福斯特所谓的“扁平型”人物。这样,此类人物形象审美价值之受到损害也就势在必然了)的成功塑造。
《乌泥湖年谱》之艺术成功,与丁子恒这一人物的设计塑造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小说题名曰“年谱”,而这“年谱”的记述撰写者,实际上就是丁子恒。虽然小说并未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叙述模式,但从文本实际考察,却不难发现,对于现代小说而言至为关键的叙事视点的设定,乃具体地体现在了丁子恒这一人物身上。这也就是说,对于小说中的一系列人和事而言,丁子恒是旁观者评价者,也是见证者。小说中若干重要的人与事,都是经由丁子恒这一中介的一重过滤之后才传达给读者的(此处必须辨明的一点乃是,从西方严格的叙述学理论来看,《乌泥湖年谱》中的丁子恒并不能被看作故事的传达者,亦即他并非小说文本的叙述者,因为小说中的许多人和事是丁子恒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他所无法感知的。但作家的具体文本操作并不一定非得恪守某种严格的叙述学理论,作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择定自己特定的叙事方式。在《乌泥湖年谱》叙事视点的设定上,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方方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智慧的继承与沿用。在中国小说传统的叙事方式中,类乎于丁子恒这样并不十分严格带有一定游移性质的叙事视点的叙事手法,并不少见。比如《红楼梦》,即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从小说艺术的表达层面来看,丁子恒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丁子恒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他是观察与见证者,更在于他本人也是故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参与者。在小说中,丁子恒的结构性作用也是异常明显的。假若舍却了丁子恒,那么小说所欲达到的梳理表现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写作意图的最后实现,则是很难想象的。在某种意义上,丁子恒是一个幸运者,当他的那些知识分子同伴们在1957年至1966年这十年间因各种原因纷纷遭遇厄运的时候,丁子恒却勉强维持了自己那还算自由的身与那还算圆满的家。但也正是为了这一切,丁子恒所付出的禁锢自我心灵压抑自我感情乃至放弃自我尊严的代价同样是极为惨重的。在某种意义上,小说中所呈现的丁子恒的这一段心灵历程简直可以被称为炼狱之旅。丁子恒的精神畸变开始于1957年。1957年,在批判李琛明的时候,丁子恒作了一个揭发,结果批判便因了他的揭发而升级,乃至最后使李成为右派。这是丁子恒第一次违背并出卖自己的良知,这第一次使“两个最可鄙的字从辞海里跳到他的眼前:出卖。他自己被这两个无情之字震撼得目瞪口呆”。然后便是路遇时李琛明那轻蔑不屑的目光了:“这道目光充满蔑视和厌恶,有如一把犀利尖刀,直插丁子恒的心灵,将他的自尊切割得鲜血淋漓,令丁子恒永生难忘。……丁子恒知道,这道目光将永远同他的噩梦纠缠在一起了。”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此后长达十年的时光里,丁子恒还将目睹更多类乎李琛明这样自己同伴们的悲剧,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埋葬自己的良知。小说中曾经写道:“丁子恒在如此消息面前手脚发凉。……他想,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我必须克制自己,我必须尽可能沉默。……我若要对得起良心,就会对不起我的妻儿。像苏非聪,像林嘉禾,像孔繁正,等等等等,都是多么可怕的例子呀。”丁子恒的此种心态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正是在自己的同类一再惨遭的无情政治打击的刺激影响下,正是在一种狐死兔悲的心态情绪的笼罩下,更多的如丁子恒这样的知识分子才逐渐地放弃了自我的人格尊严与人性良知,逐渐地由被迫的他者阉割变为了主动的自我阉割,逐渐地由一种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种心灵猥琐不堪的精神侏儒。而放弃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如同奴隶般的苟活:“因为对政治一无所知,你只想做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单纯的工具。然而连这样的微小的目标你都无法达到,迎面向你走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羞辱和全体亲人的背叛。在所有人的目光里,你只有弓下身低下头,承认自己连狗都不如。”“一个不知为何而活,也不知自己会活成怎样的人,一个每日里心下茫然着来来去去的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自己思想的人,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没有了表达自己欲望的欲望的人,与行尸走肉何异?”而导致这所有一切精神畸变的根本原因却在于秉承领导者意志的反复无常的政治运动,正是这频仍异常的政治运动给知识分子乃至整个国人的精神世界以毁灭性的打击。在目睹了林正锋院长被批斗的场景后,丁子恒想:“现在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人了,无论是被游街的还是领着游街的。”被游街者当然是斯文扫地的知识分子,但领着游街者呢?在那种时候,充斥于此类人心目中的其实乃是被当时的一种意识形态氛围被政治运动所诱导出来的无以自抑的十足兽性。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在目睹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乌泥湖生活”之后,丁子恒居然发现自己既不能死却也无法生:“他不能死,因为他的身后有柔弱的妻子雯颖和四个孩子,他没有死的权利。但是,他也无法活,因为他的心和他的意志,都承受不了凌辱,做人而没有一点尊严,比死去更为痛苦。”哈姆莱特王子为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苦恼犹豫,丁子恒的处境居然是既不能死也无法生,这样一种生死均不能的生存状况的苦处也大概只有经历过1957年以来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才能领会并咀嚼况味的。应该说,通过丁子恒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方把她那犀利的精神解剖刀切入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黑洞之中,探测出了其人性构成的复杂与深邃程度。必须承认,正是极大地依凭了方方这样一种非亲历性的写作方式,《乌泥湖年谱》才圆满地完成了对丁子恒形象的刻画塑造。很显然,丁子恒是介乎于苏非聪们与王志福们之间的一类更加复杂真实因而也更具普遍性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右派作家的亲历性写作中,因了作家自身差不多就等同于小说主人公这样一种情形存在的缘故,作家便无法以一种严格自审的方式对待人物,自然也就很难发现其精神构成中负面因素的存在。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遮蔽心态存在并作用的结果就是如丁子恒王志福这样的形象绝难诞生于右派作家笔下。然而,丁子恒却又并不类同于王志福这样的败类,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乃在于作家方方对丁子恒内在心理的同情性理解。方方能有对丁子恒的同情性理解的前提,是方方自己与《乌泥湖年谱》中的嘟嘟亦即《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的“我”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把方方直接理解为“我”或嘟嘟。这样,“父亲”或者丁子恒身上所凝聚着的其实正是方方对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父亲一种理解认识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作家才能既对丁子恒精神的萎缩畸变进行不失严峻的批判性审视,同时也能从人性本身既有的软弱脆弱的一面出发对丁子恒懦弱的明哲保身行为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作出的也正是类似于丁子恒这样的人生与精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丁子恒这一形象的涵盖象征意义其实是最为普遍广泛的。
行文至此,再来品味《乌泥湖年谱》书前所引读者非常熟悉的曹操名作《短歌行》,即可悟出方方的深刻寄寓所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诗句所道出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真实的精神状况。因了自身文化土壤的缘故,自屈原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过如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一种独立不倚的人格建构,长期以来的政治与文化境况就决定了某种依附人格的存在。对于骨子里流淌着中国文化血液的知识分子而言,但求政治清明,但求能有一个恰切宽松的环境能使自己一展抱负与胸怀。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种理想追求也往往是无法实现的,也常常因这种追求而与现实政治文化环境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尖锐冲突。《乌泥湖年谱》中的丁子恒们所追求的也不过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尽快更好地建成三峡大坝而已,但当时不正常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偏是形成种种阻隔,偏是百般地阻挠他们的理想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丁子恒们确也如那些“绕树三匝”的乌鹊一样,不仅寻找不到自己“可依”之“枝”,而且还遭受了令人无法想象的肉体与精神折磨。曹操诗作向有慷慨悲凉的称誉,读《乌泥湖年谱》,也同样有慷慨悲凉之感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以慷慨悲凉寄寓深沉来概括《乌泥湖年谱》的总体风格,也是相当得体适宜的。在当前许多女性作家都以兜售自我隐私的所谓“私人化写作”风行一时的文化语境中,同为女性作家的方方能深思如此沉重的人生存在命题,且其小说风格显得格外地慷慨悲凉沉郁顿挫,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其价值意义绝对不可低估。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