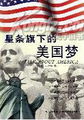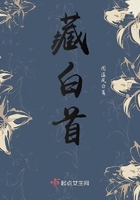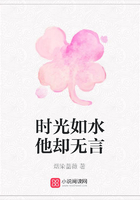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世界”的知识框架是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搭建起来的。“世界”被假定为一个合理的知识系统的表征,而“我们”中国固有的阐释方式是充满谬误的、不合理的。新时期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以对“世界”知识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为自己的基本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过程,在总体上可以说是“走向世界”的过程。“走向世界”凸显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的中国急欲融入世界,追赶西方“先进”潮流的渴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呼吁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对冲出自我封闭、迈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诉求。在全中国“走向世界”的合奏声中,走向“世界文学”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推动力”。由此,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努力以中国之外“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方法为基础,以国外引进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起点,经过1984年的反思、1985年的“方法论年”,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得到了最广泛的介绍和运用,最终从根本上引导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潮。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以中国之外的“世界”文学的情形为参照对象的,比较文学威为理所当然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式,该研究领域汇集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实力强大的学者,中国学术界在此贡献出了自己最重要的成果。新时朗中国学人重提“比较文学”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我们称之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热热闹闹地搞了十多年,各种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都‘红’过一阵子。‘热’过一阵子,但‘年终结账’,细细一核算,我认为在这十几年中扎根扎得最深,基础奠定得最牢固,发展得最坚实,取得的成就最大的,还是最初‘红’过一阵而后来已被多数人习焉不察的比较文学。”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设立了以“世界”文学现有发展状态为自己未来目标的潜在意向,并由此建立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书不仅囊括了当时新近涌现、后来成为本学科主力的大多数学者,集中展示了那一时期的主力学者面对“走向世界”这一时代主题的精彩发言,而且以整整4万5千余字的“导论”充分提炼和发挥了“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根据。更年轻一代的学人对于马克思、歌德“世界文学”著名预言的接受,对于“走向世界”这一诉求的认同,都与曾小逸的这篇“导论”大有关系。一时间,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讨论问题已经变成了保守封闭的象征,而只有跨出中国、融入“世界”、追逐世界——前进的步伐,我们才可能有新的未来。
1990年代以来,我们重新质疑了这样将“中国”自绝于“世界”之外的思想方式,更质疑了以“西方”为“世界”,并且迷信“世界”永远“进化”的观念。然而,无论我们后来的质疑具有多少的合理性,都不得不承认,一个或许充满认知谬误的“世界”概念与知识,恰恰最大限度地打破了闭锁的思维,让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架构中来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与生命遭遇。这就如同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重启“世界”的概念,第一次获得新的“世界”的知识那样。“世界”一词,本源自佛经。《楞严经》云:“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也就是说,“世”为时间,“界”为空间,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参禅论道,“世界”一词并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描述他们现实感受的普遍用语。不过,在近代日本,“世界”却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描述其地理空间感受的新语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及日本见闻的时候,也就将“世界”引入文中,例如王韬的《扶桑游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20世纪初,留日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日书中译的高潮,其中,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占了相当的数量,“大部分地理学译著的原本也是来自日本”。随着中国留学生陆续释译的《世界地理》《世界地理志》等著作的广泛传播,“世界”成为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基本语汇。“世界”一词回传中国、成为近现代中国基本语汇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知现实的基本框架——地理空间观念发生巨大改变的过程: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是的,在100年前,正是中国中心的破灭,才诞生了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空间的概念,才有了引进“非中国”的“世界”知识的必要,尽管“中国”与“世界”在概念和知识上被作了如此不尽合理的“分裂”,但“分裂”的结果却是对盲目自大的终结,是对我们认识能力的极大的扩展。这,大概不能被我们轻易否定。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反思,这些以西方化的“世界”知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压抑和遮蔽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特色?我们是否就会在不断的“世界化”追逐中沦落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对象?
其实,100余年前,“世界”知识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事实:所谓外来的(西方的)“世界”知识的丰富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壮大,本土的、地方的知识恰恰也获得了生长的可能。100余年前的留日中国学生在获得“世界”知识的同时,也升起了强烈“乡土关怀”。本土经验的挖掘、“地方知识”的建构与“世界”知识的引入一样令人瞩目。他们纷纷创办的反映其新思想的杂志,绝大多数均以各自的家乡命名,《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洞庭波》《鹃声》《豫报》《云南》《晋乘》《关陇》《江西》《四川》《滇话》《河南》,等等。在这些以“地方性”命名的思想表达中,已经没有了传统士人的缠绵乡愁,倒是充满了重审乡土空间的冷峻、重估乡土价值的理性以及突破既有空间束缚的激情。我们所看到的分明是一次次的精神的“还乡”,他们在精神上重返自己原初的生存世界,以新的目光审视它,以新的理性剖析它,又以新的热情激活它。
出于对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批判立场,克利福德·格尔兹教授(Clifford Geertz)提出了“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并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有过深刻的表述。“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视域等。”它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在作为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强调的是那种有别于统一性、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的知识创造与知识批判。虽然我们没有必要用这样的论述来比附百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的萌发,但是,在对西方现代化的物质主义保持批判性立场中讨论中国“问题”,这却是像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基本选择。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诸多的地方“问题”之时,他们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展示自己的地方“独特性”,而是表达自己所领悟和思考着的一种由特定区域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价值追求。而任何一个不带偏见地阅读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些价值追求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翻版,也不是地方历史的简单堆积,它们属于一种建构中的“新型的知识观念”。
所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依托地方生存感受与乡土时政经验的思想表达分明不能被我们简单视作是“外来”知识的移植和模仿,更不属于所谓“文化殖民”的内容。同样,在新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在重点展示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方法热”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寻根”,虽然后来我们对这样的“寻根”还有诸多的不满;1990年代以降,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走向。竭力倡导“走向世界”的现代学人同样没有忽视中国文学研究的地方资源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质疑“现代性”、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质疑西方文化霸权的中国影响之前,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地方性”的独特价值。198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苏州年会就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作为议题之一,在学者看来:“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在中国当代批评家的眼中,引入“地方性”视野既是一种“丰富”,也是一种“尊严”,正如学者樊星所概括的那样:“在谈论‘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这些话题时,我们便不会再迷失在空论的云雾中——因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了我们无比丰富的启迪。”“当现代化大潮正在冲刷着传统文化的记忆时,文学却捍卫着记忆的尊严。”在这里,“地方性”背景已经成为中国学者自觉反思“现代化大潮”的参照。
以上的历史过程似乎告诉我们:“世界知识”与“地方知识”完全可以摆脱“二元对立”的状态,而呈现出彼此激发、相互支撑的关系,中国文学从近代到当代的演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穿越了这些表层的知识对立,形成着更内在的连接和共谋呢?我认为是作为“知识”创造主体的人本身,具体而言,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建构能力,在“知识社会学”盛行的今天,我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言必称“知识考古”,但离开了人的精神发展史进行客观的“考古”其实并不能洞察问题的本质。
考察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演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知识”与“地方知识”相互支持的关系构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的成长。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自我意识的饱满和发展是发现和提炼全新的艺术感受的基础,只有善于发现和提炼新的艺术感受的文学批评才能推动人类精神的总体成长,才能促进人生价值新的挖掘和发扬。在辨别种种“知识”姓“西”姓“中”,或者“外来”与“本土”之前,更重要的是考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将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以及是否将人的主体性作为自觉的追求。换句话说,在“知识”层面将“世界”与“本土”暂时“割裂”并不要紧,引进某些“外来”的偏激“观念”也不要紧,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知识创造者的我们是否获得了自我精神的丰富与成长,或者说自我精神的成长是否成为一种更自觉的追求,如果这一切得以完成,那么未来的新的“知识”的创造便是尽可期待的,从“世界知识”的引入到“地方知识”的重新创造,也自然属于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这样的“地方知识”理所当然也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从“世界知识”的看似偏颇的输入到“地方知识”的开放式生长,这样的过程原本没有矛盾,因为知识主体的自我意识被开发了,自我创造的活性被激发了。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演变中,浸润于日本“世界知识”的鲁迅主张“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恢主己”,即返回到人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不无偏颇的“方法热”催生了文学“主体性”的命题:“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入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虽然那场讨论尚不及深入展开。
过于重视“知识”本身的辨别和分析,极大地忽略了“知识”流变背后人的精神形态的更重要的改变,处于这样的思维定势的我们常常陷入中/外、东/西、西方/本土的无休止的纠缠争论中,恰恰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家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过程并没有得到更仔细、更具有耐性的观察和有说服力量的阐释,其精神创造的成果没有得到足够的总结,其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入细致的分析。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知识”“地方知识”的关系又属于一种独特的“依托一超越”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精神创造活动都不能不是以“知识”为背景的,是新知识的输入激活了我们创造的可能,但文学作为一种更复杂更细微的精神现象,特别是它充满变幻的生长“过程”,却又不是理性的稳定的“知识”系统所能够完全解释的,对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考察描述,既要能够“知识考古”,又要善于“感性超越”,既要有“知识学”的理性,又要有“生命体验”的激情,作为文学的学术研究,则更需要有对这些不规则、不稳定、充满偏颇的“感性”与“激情”的理解力与阐释力。
人类不仅是逻辑的知性的存在物,也是信仰的存在物,是充满感性冲动与生命体验的复杂存在。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曾经长期受制于对中国作家理性知识的清理和分析,严重忽略了知识分子作为感性生命存在的种种体验,更因此忽视了以这些生命体验为基础所产生的艺术的创造能力。其实,“体验”更直接地联系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包括美学趣味、文学选择在内的人类文化现象的转变,归根结底可以说就是体验——包括体验内涵与体验方式——的转变,这正是西方20世纪思想家与美学家的一个重要发现。
自近代、现代到当代,中国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不仅是与新“知识”的输入与传播有关,更与“知识”的流转,与中国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理解”有关。我们今天考察这样一段历史,不仅仅需要清理这些客观的知识本身,更要分析和追踪这些“知识”的演化过程,挖掘作为“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知识”的特殊感受、领悟与修改。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更需要的不是对影响中国文学的这些“中外知识”的知识论式的理解,而是厘清种种“知识”与现代中国人特殊生存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创造主体的种种心态、体验与审美活动,所谓的“知识”也不单是客观不变的,它本身也必须重新加以复述,加以“考古”的观察。这一切的背后,都一再提醒我们特别注意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感受、自我生成着的精神世界。正如康德对文艺活动中自由“精神”意义的描述那样:“精神(灵魂)在审美的意义里就是那心意付予对象以生存的原理。而这原理所凭借来使心灵生动的,即它为此目的所运用的素材,把心意诸力合目的地推入跃动之中,这就是推入那样一种自由活动,这活动由自身持续着并加强着心意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