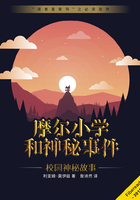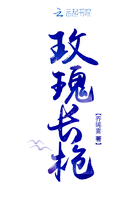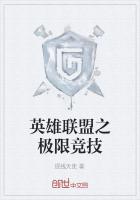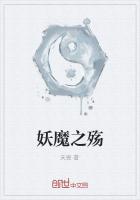一
我知道,我会在这间房间里,这间完完全全地压迫着我的房间里,一直坐到这一切结束。
一间逼仄的病房,三个迷乱的夜晚,《夜逝之时》(Meean nóttin líeur,1990)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主人公尼娜,在母亲的临终床边焦躁地等待:等待母亲死去,等待这一切结束——期待,却也恐惧。
女儿送别母亲。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Fríea á.Sigureardóttir,1940—2010)曾在采访中提到,1973年母亲去世时,自己便决意写作这样一部作品。彼时弗丽达身患顽疾,于医院住院治疗,未能给母亲送终,故而愿以一部小说来悼念母亲[1]。弗丽达生于冰岛西部峡湾豪斯川迪尔半岛(Hornstrandir)的海斯泰里村(Hesteyri),在13个孩子中排行倒数第二。弗丽达的姐姐雅科比娜·西古尔达多蒂尔(Jakobína Sigureardóttir,1918—1994)是冰岛著名作家。豪斯川迪尔是冰岛最为偏僻亦最为壮丽的地区之一。几世纪以来,变幻莫测的自然是豪斯川迪尔居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因山势险峻、地貌崎岖,当地农业发展极为有限,人们的食物主要是悬崖上的鸟蛋与海洋中的鱼类;而入冬后,雪花如席,各农场间便几乎无法通行,北极熊不时还会侵袭农场。二战及战后时期,豪斯川迪尔的农场全部被废弃,居民全部迁徙至首都雷克雅未克等城镇地区。1945年,弗丽达一家也从海斯泰里搬迁至首都附近的凯夫拉维克(Keflavík)。这场“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徙贯穿了冰岛整个20世纪的历史,深刻改变了冰岛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面貌,在20世纪中后期的冰岛文学作品中,乡村与城市这组二元对立不断复现。
19岁时,弗丽达便嫁给了丈夫贡纳尔,开始在雷克雅未克生活,而她并未放弃学业与工作,于1961年高中毕业,1971年获冰岛大学冰岛语本科学位,1979年获冰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论约库尔·雅各布松的剧作》(Leikrit Jokuls Jakobssonar,1980)收入“冰岛学丛书”(Studia Islandica)。弗丽达曾任冰岛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冰岛大学教师等职,1978年后才正式开始专职写作。198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Tetta er ekkert alvarlegt)是她的首部作品。集子里的六篇故事,大多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当代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具有浓郁的社会批判色彩;而弗丽达在这组短篇小说中试验了多种叙事形式:独白与对话的构建、梦境与现实的糅合、转换不停的聚焦……弗丽达对叙事形式的重视可见一斑。六篇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因心生感触,而回忆起从前人生的某些片段,不妨说这六篇故事都是主人公人生传记的片段[2]。这种为人物立传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是弗丽达作品的鲜明特征之一。
在弗丽达的作品中,人物常常被丢置于压迫感极强的陌生环境之中[3],换言之,这些作品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实验意味:逼仄的空间迫使小说人物直视自身,直面过去、现实乃至未来,在塑造其身体体验的同时,也对叙事行为本身产生具体的影响。弗丽达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与阴影》(Sólin og skugginn,1981)是一部医院文学。主人公西格伦患上一种医生无法确诊的奇特病症,在漫长的等待后,西格伦终于排到了医院的住院床位,开始入院接受检查与治疗。作品有三条线索:一条以侦探小说般的写法,探寻西格伦的真正病因;一条颇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展现西格伦与医院体系的权力斗争;最后一条是西格伦与众多女性、男性病友的亲密交往,以心理现实主义勾勒西格伦直面生命与死亡的心路历程。以小见大、以医院反映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一线广受评论家赞誉[4],这部作品也与弗丽达的生命体验紧密交织:冰岛医生也一直未能确诊她所患的病症。20世纪70年代,冰岛涌现出一众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作品,被文学史家称为“新现实主义”(nyraunsai)。《太阳与阴影》被誉为新现实主义文学中难能可贵的佳作,西格伦这一坚强、机智、不畏权威的女斗士形象也极富典型意义[5]。
医生最终也未能确认西格伦的真正病因,甚至认为,她只是患了女人身上常见的歇斯底里。小说却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西格伦在丈夫的陪同下离开医院,充满了面对生活、对抗疾病的信心,因为在那逼仄的病房中,西格伦已经收获了对生活、对生死的全新领悟。
《太阳与阴影》是传统的第三人称过去时叙事,而弗丽达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像海一样》(Eins og hafie,1986),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景观。这是一部人物、场景、聚焦不停转换的“群体小说”,或曰“群像小说”(kollektiv roman)[6]。弗丽达的小说作品都算不得大篇幅,却从来以群像式的繁多人物著称;她对“群体小说”的运用与发展,在20世纪末的冰岛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
冰岛一处海边城镇里,一座古老而破旧的房子赫然耸立,与其他房屋格格不入;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这栋房子里的十二位居民。依然是弗丽达式的封闭空间,而这一次小说人物们要面对的,则是新与旧、现实与梦境、理智与情感的激烈冲突。房屋是冰岛文学中的关键意象,经常作为现代性暴力的发生场所出现。例如在斯瓦瓦·雅各布斯多蒂尔(Svava Jakobsdóttir,1930—2004)的名作《租客》(Leigjandinn,1969)的结尾,女人的手在试图开门时石化粉碎;而在埃纳尔·茂尔·古德蒙德松(Einar Már Guemundsson,1954— )的《旋转楼梯的骑士们》(Riddarar hringstigans,1982)中,一个小男孩摔下楼梯,梦幻的童真世界因男孩的死亡而破灭。相比之下,《像海一样》的叙事声音与故事情节更为柔和,却不无汹涌,因为“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7]——或许爱就如大海一样,或平和或汹涌,柔情中藏匿着危险。澎湃的情感使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鲜活无比,人物的内在思绪与外在现实水乳交融,诗意与梦幻的氛围油然而生,叙述者娴熟的意识切换与时空拼贴都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格局,而弗丽达的上一部短篇小说集《临窗》(Vie gluggann,1984)[8]中就有对此等叙事技术的精湛运用。
现代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新旧冲突是弗丽达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弗丽达在《像海一样》中构造了一片“完整”的文学空间、一个拟真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小说也因此充满了自揭虚构般的“建构感”,在追寻真实的同时,实则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圭臬。有评论家指出,《像海一样》或许与马尔克斯的名作《百年孤独》一脉相承[9]。而在弗丽达此后的作品中,我们会不断看到她对现实主义文学观、对建构世界的可能性的超越与解构;在弗丽达的文学世界中,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10]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模式渐渐弥散开来。
弗丽达接下来的三部长篇小说《夜逝之时》、《封闭世界中》(í luktum heimi,1994)、《马利亚之窗》(Maríuglugginn,1998)被评论家视为一组三部曲,关乎时间与记忆、关乎现实与虚构、关乎过去之于现代的意义[11]。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现代都市人,而在与记忆与历史对视之时,其自我认知却逐步瓦解。在一个个密闭空间中,小说叙事愈发破碎,叙述人丧失了对所述故事的完全掌控,身体与精神的痛苦频频打断叙事进程。《马利亚之窗》中一男一女两位人物以第一人称轮流发言,二人却鲜有交流,双线叙事直至结尾方才合流;《封闭世界中》是一部日记体小说,读者的阅读过程有如在泥潭中蹚行,叙事一度近乎“瘫痪”,而男主人公的迷茫与痛苦也恰恰体现于此。对幽邃意识的书写也为叙事蒙上黑暗、迷离甚而恐怖的悬疑之纱。可以说,弗丽达对于叙事形式的探索并非空洞的文体试验,她始终在寻找最符合故事质感的文体与形式。
弗丽达的所有作品中都有关于家庭的情节[12]:《太阳与阴影》中核心家庭因妻子患病而碎解;《像海一样》述说了多个家庭的命运故事;《夜逝之时》是一部六代女性的史诗;《封闭世界中》则是一部男性史诗——弗丽达跨越生理性别,描摹男性心理,聚焦家族中男人间的交往;《马利亚之窗》的两位主人公是一对艺术家恋人,却因艺术追求并未组建家庭;《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临窗》以及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夏日布鲁斯》(Sumarblús,2000)中都有多篇描写家庭成员冲突的作品。弗丽达的最后一部长篇《尤利娅房中》(í húsi Júlíu,2006)亦是一部庞杂的女性家族史[13]。而这一次,小说人物的生命书写不是由人物自己来完成,而是通过一位第一人称见证者(事实上也承担了采访者的角色)映射传记书写过程,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张力为这部作品增加了新的维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冰岛文坛最引人瞩目的几位女作家全部具有文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五六十年代,斯瓦瓦·雅各布斯多蒂尔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中世纪冰岛文学、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瑞典文学;1970年,奥尔芙伦·贡略格斯多蒂尔(álfrún Gunnlaugsdóttir,1938— )获得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中世纪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冰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维格迪斯·格里姆斯多蒂尔(Vigdís Grímsdóttir,1953— )于1978年获得冰岛大学冰岛语本科学位。弗丽达也是一位冰岛文学专家,她也多次在采访中提到,自己热爱阅读冰岛与世界文学[14]。这些女作家的作品或如斯瓦瓦,以女性角度重审冰岛文学遗产;或如奥尔芙伦,将冰岛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之下;或如弗丽达与维格迪斯,冥思虚构、艺术及写作的本质,进行元小说(metafiction)创作。而弗丽达的艺术追求并非“自揭虚构”这样简单,她寻觅的是揭开虚构后的那份现实感;她以(后)现代笔法书写的,或许仍是某种社会现实——指涉虚构,是为了破除幻象,直抵现代性暴力在人们身体与精神上遗留下的创伤。而弗丽达作品中那些丰盈而沉重的具身痛苦、那些幽邃而澎湃的生命叙事,也正是她为冰岛文学做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
二
《夜逝之时》获1990年首届冰岛文学奖,1992年又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成为冰岛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作家。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会这样评价《夜逝之时》:
这是一部大胆、创新而富于诗意之美的小说。作品回望过去,追寻其中对我们当下仍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故事发生于冰岛西峡湾的壮丽风光中,自然描写亦构成了文本魔力的一部分。作品并未营造我们能够完全理解祖辈现实的幻觉。它唤起重重疑问,却也在寻觅答案。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以其诗意之笔,勾勒着我们对于历史与叙事的需要,也昭示了求索生命与艺术的唯一真理是何等艰难。[15]
过去与现实的对撞是弗丽达的胸中块垒所在,在她的作品中,过去是幽灵般的存在,无处不在,一再侵袭,令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现代人措手不及,勾起他们不能承受的创伤记忆[16],《夜逝之时》是弗丽达对这一主题最为深沉的演绎。我们可以无限简短地复述这部小说的情节:当夜晚逝去之时,尼娜坐在母亲的临终床畔守夜,关于家族女性的古老故事与记忆却萧萧来袭。我们也可以去无限细致地整理,尼娜在床畔回忆起的六代女性故事。而《夜逝之时》不是一部传统的家族历史小说,尼娜是回忆者,亦是记录者——为了“消磨时间”,尼娜将六代女人的生命经历付诸纸上。记忆转为文字,尼娜成为作者。或许我们所阅读的这部作品,便是尼娜写作出的一部小说。她在时空之间穿梭不停,企图记录、企图寻觅,而“寻觅,狂悖的寻觅——寻觅些什么?”
女性的历史/历史的女性
苏艾娃—索尔维格—卡特琳—马利亚/索尔蒂斯—马大/尼娜—萨拉。
《夜逝之时》是一部生动鲜活的女性历史,而她们也都是历史中的女性。第一夜,尼娜坐于床畔,回忆/写作出第一辈(苏艾娃、斯蒂凡、雅各布)、第二辈(索尔维格)与第三辈(卡特琳、奥德尼、埃琳)的故事。
粗略算来,第一辈的故事约发生于19世纪初,第二辈、第三辈的故事则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如前所述,豪斯川迪尔人依凭悬崖与海洋为生,春日,人们会下悬崖捕鸟蛋。春日生机盎然,这一段叙事也诗意飞扬:“那是鸟的时节。悬崖的时节。北极之隅的宁静海湾中,忙碌与历险的时节。”如果将这段话分为数行,我们便得到一首隽永的小诗。而自然的诗意中藏匿着危险,“那只苍灰的爪,在此等着捕捉每一个胆敢挑战悬崖的人”。悬崖飞石随时都有可能夺去人们的性命。据冰岛民间传说记载,主教古德蒙德·阿拉松(Guemundur Arason)为冰岛北部德朗盖岛(Drangey)上的悬崖祝圣,以期减少伤亡。主教悬在绳上,降下悬崖,为其洒上圣水,而一只苍灰的毛爪猛然持刀出现,欲剪断主教身上的绳子,同时道:“恶灵总要有块栖身之地”;主教重又回到崖边,一部分悬崖遂未被祝圣[17]。“苍灰之爪”这一意象在《夜逝之时》中反复出现,代表着巍巍自然的原始危险。
原始自然之间亦有情欲流动。尼娜记录下苏艾娃、斯蒂凡、雅各布、弗丽德梅等人的罗曼故事。在冰岛,苏艾娃(Sunneva)是个罕见的名字,她的身世亦颇神秘;苏艾娃意为“太阳的馈赠”,她也为这座农场带来了光明与快乐——又抑或灾难与痛苦?农场主人斯蒂凡是苏艾娃的丈夫,侄子雅各布却也对她生出爱慕[18]。一位黑眼黑发的海员到达这偏僻的海湾,为苏艾娃留下一条披巾——或许还有更多:雅各布葬身悬崖时,一条崭新的生命却降临到苏艾娃体内。
而这只是尼娜从姨姨马利亚那里听来的一段故事,在母亲索尔蒂斯看来,这是一段荒谬的丹麦罗曼——情节夸张空洞的虚构故事。尼娜笔下,索尔维格与卡特琳的故事亦复如是。索尔维格是苏艾娃的女儿,生下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后,便于悬崖下自杀。卡特琳嫁给了索尔维格的儿子奥德尼;面对丈夫的不忠,她选择原谅,并将丈夫的前情妇埃琳接到农场一起生活。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尼娜充满不解、充满愤怒。她直接进入自己创造的文本世界:“我摇摇头,不要咖啡,正在奔跑,同弗丽德梅一起,我已卷入了一个故事之中”;成为故事中的人物,质问卡特琳:“还想把她接到家里!你疯了吧!被一封叽叽歪歪的信骗得团团转,谈什么原谅,谈什么赦罪。”作为现代女性的她不愿理解、也不愿原谅祖辈女性做出的各种“卑微”选择。
进入第二夜,尼娜开始写作母亲索尔蒂斯与姨姨马利亚的故事。索尔蒂斯(Tórdís)意为“索尔的女神”,索尔是北欧神话中力量的化身,与大地、与农耕紧密相关,索尔蒂斯亦是如此。马利亚则是《圣经》中的名字,可这里指涉的是哪个马利亚呢?是圣母马利亚么?抑或是抹大拉的马利亚?20世纪上半期的一年冬天,索尔蒂斯与马利亚曾一同在雷克雅未克生活。姐姐马利亚不希望索尔蒂斯重回那片偏僻海湾,鼓励她与自己一同在领事公馆内侍候宴会,再与自己一同出国探寻更广阔的天地。此时冰岛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已缓慢开始,女性的生存空间更加广阔。索尔蒂斯却选择重返水湾,尼娜责备道:“却在阡陌交汇处背过身去——通往其他方向的阡陌。拒斥其他选择与可能,重返家乡那片海湾。不相信选择。”二战期间,随着英美驻军的先后到来,冰岛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全面现代化,一整代冰岛人被生生“抛入现代”[19]。尼娜出生于现代化完成之后,而索尔蒂斯属于上一代,母女之间的个体冲突也因此附着上历史性与社会性。
姐姐马大与妹妹尼娜之间的冲突却似乎带有某些意识形态色彩:尼娜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化身,而马大笃信革命、笃信社会主义与“自由、平等、友爱”。马大之名同样取自《圣经》,有“家庭主妇”之意。姊妹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却也与情欲、爱欲两相纠缠,她们激烈地“争夺”母亲与男人的关注与爱——最后一夜,在母亲床边,这场斗争或许终将落下帷幕。
尼娜的自我叙述散落于各处。城市之子、时代骄女尼娜,曾与哥哥海尔吉、恋人阿德纳尔重返故乡那片海湾,于农场废墟旁、没腰高草间蜷卧酒醉,西峡湾的恐怖自然令她不知所措,令她一再想到死亡。尼娜与许多冰岛人一样,也曾梦想成为作家,期待亲身体验冰岛的自然与历史。她的初恋男友阿德纳尔是一位画家,二人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如果不能写作,我会死掉的。”尼娜说。“你怎么会不能写作呢?我画画,你写作,一切都恰到好处啊。”阿德纳尔说。而乌托邦式的艺术幻想在生活的重压下破灭,尼娜与阿德纳尔分手,带着一部无人问津的小说手稿回到家中,而后同律师古德永结了婚,成了家庭主妇。与古德永离婚后,尼娜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广告工作室,转向“那唯一恒久的诗艺——广告的诗艺、现代的诗艺”。
抛却虚构,抛却文学,尼娜自诩为真正的时代之子,她所使用的词语与句式属于这个崭新的时代:“属于那炸弹的世界,尼娜,那由巨人主宰的世界,那里无处安放一件过时的破烂,一件过去的遗物。”她常将主语省略,句子多以动词开头,句式简短破碎,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并置手法(parataxis)不无贯通之处。这是速度的文字,是效率的文字,也是迷惘与痛苦的文字。尼娜在讲述祖辈故事之时(尤其是第一辈苏艾娃、斯蒂凡与雅各布等人的故事),也曾试用过连贯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但她明白,自己的讲述皆为虚构:“突然间我明白了,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永远也无法理解他们之间的种种。”有论者指出,回忆得愈多,尼娜愈能感知过去与现代的贯通,她的叙事也愈渐完整[20],而在我看来,随着所述事件距尼娜愈来愈近,她的叙事却愈趋破碎,其对过去与现在的感知双双瓦解,文本的裂隙不断扩大,这种不确定性在全书结尾达到顶点:“现在,我将怎样呢?”
回溯历史是20世纪80年代北欧女性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女作家们回望历史,追索历史中的女性认知与女性形象,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途径:去问妈妈[21]。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回溯历史这一举动,体现着北欧女作家们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反抗。女性不断要求获得更多权利,而女性自身有何权利要求这些权利?女性是谁?我们是谁?“你是谁人的子孙?”这些问题都萦绕在80、90年代众多女作家的心头。
记忆与后记忆——如何现代?怎样女性?
一条披巾将六代女人联结在一起。苏艾娃的披巾是外域海员的礼物,后来依次传给索尔维格、卡特琳、索尔蒂斯、尼娜与尼娜的女儿萨拉。披巾是沉重的符号,承载了太多意义、太多记忆、太多女性气息,读者可以对此作无穷解读。披巾的传承是一种记忆行为,而到达尼娜这里,披巾本身已成为一个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 )如是说:
历史的演变在加速。对于这个说法,除了其隐喻意味,还应评估其含义:对象转向最终死亡的过去的速度越来越大,但人们也已普遍意识到对象已经完全消失——这是平衡态的断裂。人们已经摆脱以前尚存于传统的余温、缄默的习俗和对先人的重复(受某种内在历史意识的驱动)中的经验。在已然变了的环境中,自我意识已经到来,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已经走到终点。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22]
尼娜之所以始终抗拒这条披巾——“想为她戴上镣铐,索尔蒂斯,将她与历史联结,一段早已消亡的历史,逸散出血液、泥土与腐烂的酸涩气息。将披巾递给她,叫她不忘角色,不忘陷阱”——正因为她哀女人之不幸、怒女人之不争,换言之,因为她对女性命运、女性地位持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过去周而复始的事情”在她这里“已经走到终点”。然而披巾在她眼中虽然空洞,却仍沉重,因为作为记忆之场的披巾即是过去与现代断裂的明证,一场记忆危机(memory crisis)已然发生[23]。
身陷记忆危机的现代人同时因过多的记忆与过少的记忆而煎熬[24]。对尼娜来说,属于祖辈女性的过去是那“过多的记忆”,她们的生命经历无比浓烈,却掺杂了太多尼娜不能忍受的价值与色彩。而与此同时,或许尼娜并不了解自己的母亲,也根本无从了解这些祖辈女性。姐姐马大不止一次地诘责尼娜:“你根本就不了解她”“你如何能理解她,你如何能理解他们,你这失却尊敬、失却信仰的一辈!”尼娜对于祖辈女性的“记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记忆,而是一种所谓“后记忆”(postmemory)。罗马尼亚学者玛丽安娜·赫什(Marianne Hirsch,1949—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以探讨后辈与祖辈之间的记忆传承。祖辈历经的记忆通过故事、照片、行为等形式传递给后辈,成为后辈记忆的一部分。赫什主要将这一概念用于大屠杀等创伤事件的幸存者;在这些家庭中,没有经历过创伤的后辈也将其纳入自身记忆。作为一种关于记忆的记忆,后记忆主要产生于想象与创造[25]。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谨慎地挪用后记忆理论,描述、阐释现代人罹受的记忆危机。后记忆与记忆之场一样,都是过去与现代截然断裂的显证。记忆在社会中的一般保存过程为:个人记忆→家庭记忆→档案或文化记忆→社会或国家记忆;大屠杀等创伤事件干扰了这一过程,而后记忆的作用就是要以个人与家庭记忆,去激活、体现那些被干扰的文化与社会记忆[26]。大屠杀等集体创伤事件或许会抹去历史档案的存在,关于冰岛的前现代时代则存在着有限的档案。尽管如此,现代性的临降仍然使尼娜这样的现代人丧失了与历史档案间的具身联系。然而,通过马利亚、索尔蒂斯、马大等人的叙述,通过马利亚展示的老照片,通过与家庭成员间的具身交往,尼娜收获了丰满的后记忆,(不)自觉地激活了关于冰岛前现代的文化与社会记忆。
但这一切并非怀旧式的缅怀,而是痛苦的凝视与清算。尼娜经由后记忆抵达的前现代社会不能为她提供任何慰藉,现代式的割裂一切的虚无主义亦非出路。在隐含作者眼中,尼娜或许是当下现代女性的代表,却绝不能代表现代女性的未来。可何为现代?怎样女性?这些重任或许落在了尼娜之女萨拉的肩上。萨拉是小说中的希望所在:“也许令萨拉觉得正常的正是这个:变化。”
无独有偶,《夜逝之时》与张洁(1937— )的《无字》(2002)之间有着镜像般的惊人相似。《无字》是一部三辈女人的史诗,作品对女性的冀望也同样寄托在主人公吴为的女儿禅月身上:“别看妈妈蹦来蹦去,换了一个男人又一个男人,实质上还是男人的奴隶。姥姥和妈妈都是男人的奴隶,那些男人,剥削着他们的精神、肉体、感情……难道她们看不出来?”;“这样当女人可不行,禅月看够了”;“禅月是一个语法正确、表述清晰、合乎逻辑的句子,吴为却是一个语法混乱的句子,就像她的小说。”[27]尼娜可不就是个禅月般的女性?独立,不依赖男人,语法正确且表述清晰?可在弗丽达看来,尼娜仍然算不得现代女性的榜样。
女性的痛苦是屡见不鲜的话题,丁玲与张洁就曾相继呐喊:“做了女人真倒霉”(《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方舟》,1982)。弗丽达的尼娜已超脱于此,她早已不再为生为女人而痛苦,能够坦荡享受自己的性别,她甚至可以跟碧昂斯(Beyónce,1981— )一起唱:Who run the world Girls(2011)——谁统治这个世界?女孩。可迸发自历史、时代、两性交往、同性交往(母女、姊妹、友人)的痛苦,缘何丰盈如旧?现代女性究竟应当如何?女性的未来在哪里呢?《夜逝之时》向读者抛出这些问题,又或者如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授奖辞所说,这部作品“唤起重重疑问,却也在寻觅答案”。
三
《夜逝之时》是一部能够作无穷阐析的复杂作品。小说甫在冰岛出版,便广受赞誉,而在其他北欧国家却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小说留白太多,场景转换过快,时空变幻过频,主人公尼娜过于扁平,缺乏深度与可信度,等等[28]。如今看来,这些批评恐怕很难站得住脚;期盼一劳永逸地理解《夜逝之时》是不可能的任务——若想真正进入小说的世界,我们或许需要一再“重访”那间狭窄的病房、那片逼仄的海湾。
小说问世已有28年,而今终与中国读者见面。我盼望着,这部作品能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国民意识展开对话: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记忆断裂、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自然还有更多。正如尼娜在小说中的玄思:艺术“不是为了囊括现实,不是为了将其固化,是为了打开这道裂缝——”
这部作品由冰岛语直接译至中文,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欧文学专家石琴娥教授的无私帮扶,感谢冰岛大学ástráeur Eysteinsson、Dagny Kristjánsdóttir、Daisy Neijmann、Gunntórunn Guemundsdóttir、úlfar Bragason等教授与我进行的讨论,感谢Jón Karl Helgason与Bergljót S.Kristjánsdóttir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感谢Margrét Jónsdóttir教授、冰中文协前主席Arntór Helgason及其夫人Elín árnadóttir的关怀。
我将这部译作献给我的父母。
张欣彧
2018年11月于天鹅沼
张欣彧,1994年生于吉林,冰岛大学冰岛文学硕士,从事冰岛文学翻译与研究。曾获冰岛文学译者奖金,在冰岛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主编、主译《世界文学》杂志冰岛文学小辑(2018/6),译有《酷暑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等。
盐柱。
晶体之间,
幅幅画面,
缘盐之窄道、
纵横索道,
委蛇无前,
冲越群山、
冲越岩麓,
古老的故事,
融散盐晶,
昏绿光芒明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