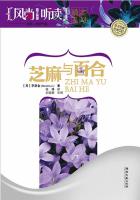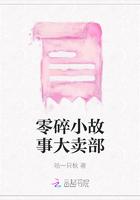其说也,无甚异。但此语要得孟子口气。若论口气,则似于形色稍重。而今说者多详性而略形,更觉无意味也。大要亦自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躯,不以为重。及谭性命,便更索之玄虚,以为奇崛。轲氏惜之,故曰:“吾此形色,岂容轻视也哉?即所以为天性也。”惟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圣人者,于此形色方能实践。实践云者,谓行到底里,毕其能事……只完全一个形躯,便浑然是个圣人;必浑然是个圣人,始可全体此个形色。首先须注意的是“得口气”一说,这是近溪再三强调的解释学方法,意谓不能盲从传统注疏,而要详细领会“圣贤语意”。应当说,近溪的“得口气”与朱子的“添语言”,表面上看似不同,其实却有一致性。因为无论是“得口气”还是“添语言”,其根本用意都在于深入抉发文本的思想意涵,反对就字解字。就此而言,近溪和朱子在经典解释的方法论上都坚持以义理解经的基本态度。问题在于在“得口气”和“添语言”的背后还存在着更为本质的东西,亦即各自的思想立场。
近溪基于他的思想立场,对“形色天性”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孟子口气”重在“形色”,这一解释非常重要,可谓独树一帜。他在“轲氏惜之”的后面所引孟子的几段原话,实际上应当视作近溪对“孟子口气”的一种创造性诠释,尤其是“于此形色方能实践”一说,则完全可以看做近溪自己的观点。对照本节开头所引朱子的解释,便可看出近溪所云“而今说者多详性而略形”,显然是指朱子以来的诠释传统。朱子用“自然之理”来解释孟子“形色天性”,其“口气”重在“天性”。这在近溪看来,未免索然“无意味也”。那么近溪为何强调孟子口气重在“形色”?
其实,这与他的这一观点有关:“天性”不能脱离“形色”而存在,“形色”是展现“天性”的基础和条件,无视“形色”而只讲性命实是“玄虚”之空谈,因此在实践论上,必须将“天性”落实在“形色”之上,于“形色”上加以切身的实践,最终实现“只完全一个形躯”、“全体此个形色”的目标。近溪的这一诠释思路,亦即我们上面提到的“形著体现”的观念,或可称为“形著原则”。在此“形著原则”中,身/心作为一种结构关系,彼此互为关联,而其立足点却在“身”。虽然就近溪的心学立场而言,“心”具有绝对的价值,然而近溪同时也认为心不能孤立于身而独自存在。因此可以这么说,就价值论的角度看,心大身小,故须强调“心以宰身”;就实践论的角度看,身重心轻,故应即“形色”而“践形”,如此才能体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须指出的是,近溪以“完全形躯”、“全体形色”来诠释孟子的“践形”观具有独特的意义,反映出近溪重视“形”及“身”在实践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故近溪强调指出:“便须把孔子之仁者人也,孟子之形色天性,细细体认,我此个人如何却是仁,我此个形色如何却即是天性。”显然,这是将“形色天性”直接解释成形色即天性,揭示了形色问题在孔孟传统中的重要性。
由上可见,近溪通过对“孟子口气”的解读,旨在强调“形色”不仅在存在形式上构成“天性”之基础,而且在实践方法上“形色”是“天性”的“实落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近溪的“身心”观当中,“身”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从历史上看,近溪对于孟子重“形”的重新发现,当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其意义在于:近溪不唯对于宋儒以来未免详性而略形、重天命而轻气质的思想倾向提出了批评,同时,针对阳明心学以来重本体而略工夫之思想现象,近溪也以自己独特的观点主张,提出了具有切实意义的解决方案。
然而也须看到,尽管“身”在实践方法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之本身就构成终极价值之主要内涵,换言之,“身”
主要具有体验意义上的价值。一方面,从身心结构来看,心性离不开身形,无身形则性命便成空谈;另一方面,在以形显性、以身显心的形著模式中,心性仍然是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道德价值之根源所在。在上一节我们曾指出在“心以宰身”抑或“心以从身”的行为抉择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心”。“心”不仅是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具备主宰身体的能力,而且其本身在价值论上处于优先的地位。虽然近溪竭力主张身体在实现心性价值的过程中具有实践论意义,但归根结底,近溪仍然坚持“心以宰身”而反对“心以从身”。
(第六节 天心观
一 问题由来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看到“心”的问题在近溪思想中是一核心问题,这里将要考察的“天心”问题亦不例外,而这一问题又与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有关。通过对天心问题的考察,能使我们对近溪思想的特质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将发现近溪思想中的中国传统宗教意识是相当浓厚的。
首先从何谓“天心”这一问题说起。从词源上说,“天心”一词可上溯到《尚书》,但其中仅出现一次,即《咸有一德》所载:“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若就观念史的角度看,在以《尚书》为代表的商周文化时代,作为神格的“天”是频繁出现的,如“天叙”、“天秩”、“天讨”、“天聪明” (《尚书·皋陶谟》)。甚至还有与“天心”意思大体相当的“帝心”等等。经过春秋以后儒家学说的洗礼,这些具有原始意味的宗教观念在孔孟思想体系中衍生出一套有关天命、天性、天道的思想言说,从孔子“唯天为大”的赞赏,到孟子的天赋良知说,他们相信天既是一种自然之天,又是一种意志之天。在天人感通的存在模式中,天赋予人以某种秩序、属性、本质,给予人以一种道德本性;人之于天则应采取这样的态度:敬天、畏天、知天、事天、奉天。天既是人们敬畏的对象,同时又是与人之心性相通相感的存在,所以“天之明命”也可以在存有形式上表现为人之本性,《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应当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述。事实上,在先秦儒家的理论建构中,“天命”与“人性”在存有论上紧密关联的这套观念非常突出也非常重要,成为后来儒家建构其心性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础。若就近溪而言,他的天心观其实与《周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之观念直接有关。那么,何谓“天地之心”?二程有一个经典解释:“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一解释几乎成了宋明儒者的共识,当然亦为近溪所接受。程伊川更有一句名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
这句话的前半段则是:“《书》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可见,其所谓“天”乃是指“天理”、“天道”。对“天”的这一理性解释可谓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思路,“天”是宇宙秩序乃至是社会秩序、人心秩序的存在依据。
在宋代哲学家当中,比起二程来,邵雍对“天”更是情有独钟,其言“天”者,充满了一种介乎哲人与诗人之间的丰富想象,例如:
“天心”、“天意”、“天人”、“天真”、“天道”、“天和”、“天理”、“天机”、“天时”、“天根”、“天数”、“天性”等等,不一而足。关于“天心”,他有两句名诗:“天心复处是无心,心到无时无处寻;若谓无心便无事,心中何故却生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时,万物未生时。”显然,“天心”是从“天地之心”化约而来,讲的是宇宙生化问题。朱子对邵雍《冬至吟》称赞备至:“康节此诗最好”,“可谓振古豪杰”,同时却以“年年岁岁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来解释“天心无改移”,其意不甚明确,细按朱子之意,“天心”即伊川所说“天地生物之心”的意思。
除邵雍而外,对“天心”有较多论述的,要数张载。其云:
复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壮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时,则有形见;情则见与事也,故可得而名状。……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自有天地以来以迄于今,盖为静而动。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张载结合《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来解释“天地之心”,突出了“生”及“生物”的涵义,将“天地之心”理解为“以生物为本”之“心”,这一解释与上述二程“天地以生物为心”以及邵雍“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的思路基本一致。不过相比之下,张载的论述更为明确。他用“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来具体解释“生物之心”,这是说天地造化是一个自然过程,其中本无人为意志参与其间,故可说天地本无心。然而天地又确有“其心”,亦即“以生物为心”,因为天地若无“其心”,则天地“生生”造化之意便无由显现。在此意义上,“天地之心”就是生物之“心”。
张载又说:“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 “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这里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张载在天地之心———生物之心这一解释框架中,加进了“仁”的概念,二程及至朱子、张南轩在围绕“仁”的问题展开论说之际,“天地以生物为心”或“天地生物之心”的命题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分析视角,并由此产生了诸多观点不尽一致的“仁说”。另外一点是,张载强调由人心以观天心,故他主张:天本“无心”,由人心而得以见矣。这一点又与张载“大其心”说发生关联。他认为,通过“大其心”,即扩充人心的作用,最后就能达到“熟后无心如天”,亦即“无心”境地。这一“无心”境地是克服“有心”之囿限,能与“天之虚”同在的境地。故云:“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所谓“无心”,就天而言,盖指“天无意”,所谓“天不能皆生善人,正以天无意也”,亦即此意;就人而言,则是指虚其心,消除心中“意、必、固、我”的人为意识、主观成见。要之,张载强调“无心”、“无意”既是“天地之心”的根本特征,同时也是人心所必须努力达到的一种境界。
关于张载的“大其心”与“合天心”的问题,朱子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评述:
“大其心,则能遍体天下之物。”体,“犹仁体事而无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络贯通,无有不到。苟一物有未体,则便有不到处,包括不尽,是心为有外。盖私意间隔而物我对立,则虽至亲且未必能无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这段评述非常平稳,从中看不到朱子自己对“天心”的解释态度,这也反映出“天心”一说对朱子而言,并不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不过,朱子对“大其心”说也有批评:“若便要说天大无外,则此心便瞥入虚空里去了。”这是因为对于任何企图夸大心的作用,朱子总是抱有非常敏感且强烈的反对态度。
至于阳明之言天言心,屡屡见之,不足为奇。他也曾说“天意”,但是否使用过“天心”一词,目前尚无确切答案,或许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到记录,但即便如此,“天心”一词不足以构成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这一点大概是可以确定的。我们知道,阳明有“心即天”、“人心是天渊”等著名命题。其所谓“天”是作为心体存在的本原性意义而被强调的,这显然与人性得之于天这一儒学观念有关。
要之,就宋明思想史来看,有关“天心”的解释基本趋于理性,原初的宗教意味已很淡薄。然而到了近溪那里,不仅“天心”成了非常关键的核心概念,而且“天”的意义在近溪的诠释中,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它既有“天地之心”的宇宙论涵义,又有天的意志这层宗教涵义。在后一层意义上,“天心”成了“天地神祇”的另一种表述,甚至是神灵意志的代名词。
二 天心人心
首先来看一段有关“天心”的简短论述:“夫子之为教,与颜子之为学,要皆不出仁礼两端。而仁礼两端,要皆本诸天心一脉。”显然,值得关注的是“天心一脉”这个提法。何谓“天心一脉”?近溪指出“仁,人心也。心之在人,体与天通,而用与物杂”,重要的是,善观仁者之心,如此便是“心即天也”,反之,则“心即物也”。要之,人心之所以能化为天心,其依据就在于人心中有一颗“仁心”,而此“仁心”在本质上与“天心”是相通相感的,原因在于人心具有“生生不已”的特征。这里又涉及“心”与“生”的关系问题。近溪指出:
殊不知天地之心以生物为心。今若独言心字,则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万异!善言心者,不如把个“生”字来替了他。则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视听言动,浑然是此生生之机,则同然是此天心为复。诚然,所谓“天地之心,以生物为心”,是宋儒以来的一个普遍共识,在这一点上,近溪所见殊无新意。不过,近溪主张以“生”字来代替“心”字,意谓从“生”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心”的涵义,则是近溪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单言“心”字,人有人之心,物有物之心,千差万别、面目殊异,难以卒言,因此不若就其“心”之本质而言,“生”便是“心”之本质,也是天地之心的本质,把握了生生之机,也就意味着实现了天心之复。故云:
宇宙之间,总是乾阳统运,吾之此事无异于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亦无异于吾之此身。其为心也,只一个心,而其为复也,亦只一个复。《经》云:“复,见天地之心。”则此个心即天心也。这是对“天心”的一个明确界定,亦即“天地之心”。具体而言,“天心”是指“乾阳”(复卦中一阳之爻)。故“天心”之“复”,实即复卦的“一阳来复”。这是就“复”卦的阳爻来解释“天心”,应当是“天心”概念的原初意义。故云复卦的“天地之心”也就是“天心”。然而近溪对天心还有两层意思的理解,一是突出了“心”的主体性意义;一是认为天心亦有“知”。先来看第一层意思:
此“心”(指“天地之心”)字与寻常心字不同。大众在此,须用个譬喻,他才明白。盖人叫做天地的心,则天地当叫做人的身,如天地没人为主,却像人睡着了时,身子完全现在,却一些无用,天地间一得个尧舜孔孟主张,便像个人睡醒了一般,耳目却何等伶俐,身体却何等快活,而家庭内外却何等齐整也耶!这里用比喻性的说法,把天地之心喻作“人心”,天地喻作“人身”,指出如果天地没有“心”为之作主,则天地之身犹如昏睡一般,不能呈现任何意义,一旦有“心”为之作主,如同天地间有个“尧舜孔孟”出来主张一番,则人人便如梦得醒一般,个个无不耳目伶俐、身体快活、家庭整齐。因此,天心须为天地作主,如同圣人之心须为人心作主一样;天地之心和圣人之心“与寻常‘心’字不同”,却有唤醒天地、赋予人身以价值意义的能力。总之,天有天心,人有人心,此“心”是决定天地之有价值、人身之有意义的依据。若无此“心”,则天地人身将永远处于昏睡状态,宇宙和人文的价值意义也将无由呈现。在此意义上,天心和人心都是一种“本心”。
问题是,人心能为人身作主,是因为人心有知,而天心要为天地作主,是否也有“知”的存在?这就引出了天心的第二层意思。
近溪的结论是:“虽乾坤亦是此个知字”,其依据是《周易·系辞上》“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