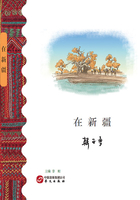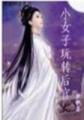不抬水的时候,我也去井沿上玩。最常去的是村东井沿上,去铁匠铺看打铁。开春农忙前铁匠铺打锄头、打犁铧;夏收农忙前打镰刀;冬天农闲时便给牲口钉掌。
铁匠任三爷,肤色黝黑;年轻的助手张海身体很结实。他们都系着厚厚的老布围裙。当任三爷左手拿一把长柄铁钳,夹着一条铁块塞进炉火时,张海便拉动了风箱,随着呼呼的风箱声,炉子里的炭火蹿起了火焰,越烧越旺。铁块被翻来转去地烧成红白透亮时,任三爷便将它抽出来停在旁边的铁姑上夹稳放实。这时候助手早已停了风箱,双手握起长柄大铁锤。铁匠先用右手握着的小铁锤在铁块上敲打几下,张海便高高抡起大铁锤,砸向那红红的铁块,于是铁匠铺里便响起“叮当、叮当”一大一小的打铁声。那条原本长方形的红色铁块,在锤打中开始变形。随着任三爷左手铁钳的翻动调整,铁块便逐渐变成一把铁铲或一把锄头的形状。这中间颜色一旦变黑,便又一次放进炉里烧红,接着再敲打,直到打造完毕。
当器物将打成时,铁匠便很开心,往往在大锤中间敲两次小锤,锤声便“叮当、叮当当,叮当、叮当当”地有了节奏变化,听起来更为經锵悦耳。铁器打造好,任三爷便夹着它放入墙旁的一个水盆里,那水吱啦啦地响起来,被炼得直泛泡。铁匠说:这叫淬火。打铁的整个过程伴着“呼呼”的风箱声,“叮当、叮当当”的敲击声,还有“吱啦”的淬火声,对于童年的我和伙伴们就如同戏法、音乐般的美妙。如果给牲口钉掌,又更是一番景况了。
正是有了铁匠铺,村东井沿回忆起来才十分有趣。当然,井沿上李家园子里,有一棵一枝结酥木梨,一枝结长把梨,还有一枝坠满了吊蛋子的大梨树,也给我留下了记忆。
南村口的井沿上二表姐夫叫金仲彦,是糜滩小学的美术老师。他是我们滩上很有名气的乡村画家。二表姐是二舅的女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兰州学裁缝时曾在我们家住过。
我们抬水时,二表姐看见了便叫我们到家里耍,表姐的两个女儿比我小几岁,苋了我叫表叔爸。有时也跟着我们玩。
上井沿把我叫表叔爸的还有一个高个子大人,瘦瘦的。是一家远亲,辈分低,乡村人慈实,见了我总要问一声:碎表叔爸。看着他高高的个头,我便觉着有些不好意思。
我和大侄子常常经过上井沿去村外玩耍。有一次在快到大堡子的路边拾了一只花猫娃一黄色,虎斑。那只猫娃子还小,捉它时很乖。在路上耍了好一会儿,并没有人来寻找,我们便把猫娃抱回了家,一直养着。
第二年夏天,我随母亲返回城里时,大哥一家留在了糜子滩。我把花猫留给了大侄子,它已经会捉老鼠了。
现在,黄河水小了,泥沙也没那时多了,但却有了工业污染,更不好饮用了。糜子滩家家都有了手压式抽水装置,同样是地下水,一压一起,水便很快顺着铁管流出来了,跟自来水一样方便。
时过境迁,金家庄子那两口老井早已不存在,井沿也没有了。周围的人家和房屋也都变了样子。惟其如此,留在我记忆中的井沿和井沿上的一切便更感亲切了。
2004年8月5日
坝滩庙小学
一九四九年秋季开学,我转到糜滩小学,上了二年级。糜滩小学是父亲最早回县创办的一所乡村小学。初建于一九三三年,到四九年已颇具规模了。是当时糜子滩唯一的一所六年制完全小学。因学校建在位于糜子滩中段的坝滩庙址上,所以糜滩人习惯于叫坝滩庙小学。
坝滩庙小学跟我家所在的金家庄子一东一西’相距不到二里路。
秋天开学时,地里的高粱、包谷已经长髙了。栽在水渠两旁高高的白杨树和学校周边葱郁的槐树柳树连成了一片,屋舍都被遮掩住了。出了村庄,跨过一条南北方向的大路和旁边的水渠,沿地埂弯来拐去地走一段,穿过一片高粱地,再过一道水渠,才能看见隐蔽在树木后面的学校西院墙。
到了冬天,地里的庄稼早已剃割干净,树叶也落光了,眼界一下子变宽了。出了金家庄子,站在村东井沿旁边的大路上朝东南望去,透过树木光秃秃的枝丫,便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学校西院墙,以及校院西侧面的整体轮廓。这才突然发现:学校离我们村庄原来是很近的。
坝滩庙小学西院墙外边有两个大鱼塘,是我们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地。听说是父亲办学初就开挖的,还在塘里试种过荷花,可惜没能成功。我上学时池塘边只有些芦苇之类的水草,也不是很多。塘水清幽幽地泛着绿色,有很多树的倒影。
每天吃过晌午饭去学校,快到鱼塘边我们便放轻脚步,尽量避免弄出响声来,就能看见有不少鱼露出脊背在水面上游。鱼的身体清晰可见,大多是青色,也有红色的,最大的有一尺多长。池塘里到处有哗啦啦的轻微的水声,水面上漾着鱼儿游动时带起的涟漪。突然间还会有一尾两尾鱼儿跃出水面,能有半尺多高,很是好看。这中间若谁不小心弄出点响声来,鱼儿们便一下子没了踪影,塘面上又恢复了平静。
冬天快放寒假前,鱼塘结了厚厚的冰。记得有一天晚自习后,结伴回家的我们看见几位住校的高年级大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冰上凿了一个大窟窿,并给旁边点起了灯,一会儿窟窿处便聚了许多鱼。他们用脸盆从窟窿里往上泼水,便有鱼被泼了上来。差不多每一盆子都有鱼泼到冰上。泼上来的鱼先是翻腾挣扎,不一会儿便冻在了冰面上,变成了冰鱼。是那样的有趣和神奇,这种捕鱼方法也是我几十年唯一见过的一次。
冬天教室里很冷。土坯砌的炉子没有烟筒,每天早晨生火时,门窗便要大开着,烟冒完才能关门窗。上课以后便不再添炭,那一笼火只是熏熏教室里的寒气而已。同学们大都身穿厚厚的棉祆棉裤,头戴有双耳扇的棉帽子;也有戴皮帽子或戴耳套的,但不多。脚上穿着有皮“鼻梁”的棉窝窝(棉鞋穷苦人家的同学也有穿不上棉裤和窝窝,只穿一件破棉祆的。上课时最冻的是脚,冻疼了便忍不住在地上跺。那时我们家乡还不知戴口罩,许多同学都伤风流涕。上课时,用鼻子吸鼻涕和打喷嚏声此起彼伏。当踩脚的声音连成一片时,老师便会厉声制止;对于吸鼻涕和打喷嚏即便很厉害,老师也只能听之任之。
课间,我们几乎全都涌出教室,开始各自的取暖运动。男生主要是在墙角挤暖暖,或抱起一条腿单脚跳着打斗。女生主要是踢毽子。当然也有踢毽子的男生,甚至有个别踢技远高于女生的,一旦踢到好看处,旁边的同学便会喝彩助阵。
太阳红时,背靠向阳的北墙,踩着脚晒太阳,也是很惬意的。谁要在前边挡住了太阳,便会挨一句唱歌一样的骂语:“谁堵我阳婆影影,我掐了他妈的奶头顶顶!”被骂的同学一般并不生气,一边躲开一边对骂起来:“谁挡我脚尖,我掐了他妈的屄尖!”粗俗野蛮的语句,歌一样的童声。小小年纪的我们’丝毫也意识不到这骂语里的邪狎之意,却自小便在无意里透露出乡村汉子的一种粗野豪蛮之气。
坝滩庙小学的树很多。教室前边的院里有很多杏树,快放暑假时,杏子便陆续黄了。上课时,能听见熟透了的杏子在微风里掉到地上的响声,那声音对于我们是很有吸引力的。下课铃响了,老师一走,我们便冲出教室,直奔树下抢拾杏子,杏子又黄又大,好吃极了。如果遇到刮风,掉下来的杏子就多了,课间捡杏子的场面也更热闹。只要不从树上摘和打,抢拾地上的杏子,校长和老师们一般是不管的。
学校大门是向南开的。校门外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对面有一个大戏楼,跟学校旁边的坝滩庙门正好相对,是庙会时唱戏的。平时学校集会,校长和主任便站在上边讲话。期末大考时要停课,可在校园里自由复习,那戏楼便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戏楼斜对面距庙门不远处,有一棵很大的空心柳树,据说是遭雷击烧坏了树心。树还活着,枝叶也还茂盛,但树的样子既神秘又有些恐怖,胆子大的同学对它也是敬而远之的,很少有人钻树洞玩。
在坝滩庙小学的一年中,留下的片断记忆都是好玩的事。关于学习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只记得我的功课都能及格,但已远不是成绩优秀的学生了。
2004年7月12日
父亲的书架
我们家糜子滩的三间上房虽然是北向却有点偏西,过去我曾误以为是西房,其实是北房。上房两边各有两间耳房:进大门的两间一门一窗,是一独立房间;靠里边的耳房没有门,却开了两个大窗户,属于上房的一个套间。套间里摆满了书架,是父亲的书房。
父亲书房里的书架大约有六七个,挨着三面墙摆着,靠后墙的三四个特别宽大好看。所有的书架上全摆满了书,一大部分都是布面硬皮精装的。父亲的书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各个方面,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不少革命或进步书籍。父亲的书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英文本。
书架下边是带门扇的橱柜,里边全是父亲收藏的名人字画。字画中不少是范振绪、陈国钧等省内名家的,也有省外一些书画家的作品。
父亲的书房,在我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父亲在家的那一段日子,他的书我是从不敢动的,进了书房也只是抬头瞻仰那些立在书架上厚厚的书,对父亲的学问充满了崇敬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时间不长,父亲便离开了家。父亲不在的时候,他的书房对我们来说显得自由多了。哥哥们找一些文学作品去看,而小学二年级的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种英文画报,那上面的彩色图片印刷非常精美,是我经常翻看的“花书”。
父亲的书里有一本《丰子惜漫画》,也是精装的,从扉页题字知道是朋友赠送的。厚厚的并不太白的书页的中间贴着彩色的子惶漫画,这种装帧在当时算是精致的了。我上小学高年级时,因为对绘画有了兴趣,这本画册便归我所有了。后来上高中时,市场上纸张紧张,加上我的无知,居然将只贴了一面边的子惜先生的画页从画册上小心地撕下包起来保存,而将空白厚书页做了速写本。虽说那些漫画至今还在,那本子也为我学画派了用场,可那种版本的子惜漫画集却在我的手里不复存在。每想起来,总不免感到遗憾。
父亲的书里,还有一套线装布套封的《芥子园画传》和一套《醉墨轩画传》。南兄小时候画得出色,得力于这两套画谱。他参军去部队后,这两套画谱便留在城内的家里。我也曾临摹过上边的花卉翎毛。
在兰州二中上初中时,我给家里捎话让将《芥子园画传》带给我。
好像是初三第一学期刚刚开学,我们初三年级的教室在学校东北角的一个院子里,是平房,我们班是坐东向西的一间教室。下午的自习课,外边下着雷阵雨,闪电不断划破天空,雷声很响,像在院子里炸开一样。教室门窗全都关着,仍然震得坐在窗户边的同学心惊胆战。
雷雨稍稍小了些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教室外边用手指敲响了窗玻璃,向窗户看去,只见有两个人向里边招手,那面孔我好像认识。再仔细一看,他们的确在向我这边招手示意,手里举着几本书。我突然想起来了:是西兄的同学谢靖荣和张宏勇。原来他们是去西安上大学的,西兄托他俩给我带来了《芥子园画传》。因为那天的雷雨特别大,所以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后来我在靖远一中教书时,曾跟谢靖荣同事六年,他始终像兄长一样关照我。前些年在白银见到他的女婿,才知道靖荣兄巳因病去世;英年早逝,闻之令人悲切。宏勇兄跟宰南兄做了儿女亲家,我们两家成了亲戚,来往自然比较多了。他也不幸于去年病逝,患病期间和去世后我曾去探望和吊唁。他担任过教育局副局长和中学校长,同事、部下和学生吊唁者数千人,站满了院内院外。我想逝者若有知,亦可慰藉了。
他们二位早年带给我的那套《芥子园画传》,多年前也在我的手里丢失了。现在我手头的一套《芥子园画传》跟原先的一样,这仍然是父亲的书,是他后来在古旧书店里买的。父亲曾经临画过上边的菊花。我回到家乡当小学代课教师时,决心把绘画作为毕生的爱好和追求,父亲便把这套画谱送给了我。
父亲留在糜子滩的那些书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三哥大学毕业,分配到靖远师范教语文,他选了部分教学用得上的文学类的书,其余绝大部分卖给了兰州古旧书店。我记得装在麻袋里拉了高高一三轮汽车。
父亲收藏的名人字画,大部分在土改时流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篆刻家陈少亭先生家里见过不少字画,上款落有父亲的名字。我问因何在他手上?少亭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县城的地摊上买回来的。
一九六二年,我去糜子滩看望母亲。大哥在上房的正面墙上挂着一个大中堂和一副对联,中堂是陈国钧的字,对联是于右任的五言草书。那时我是书法盲,根本没有看到它的价值,只是想到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对联挂在家里,担心给大哥招来祸。因为喜欢绘画,把挂在左边檩子下边的一幅山水小中堂,跟大哥要上带进了城,是范振绪画给父亲的,至今还保存在我身边。至于于右任、陈国钧的书法,以及大哥保存的其他字画,经过“文革”,早就不复存在了。是大哥自己烧掉的,还是别人拿走的,便不得而知了。
我到兰州上中学时,父亲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书橱,是单位上配发的,里边放满了老人陆续购买的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书。一九五七年后,父亲屋里的书橱被收回了。我们家也搬出了省民革,租了共和路(后改名金塔巷)西头女主人姓许的靖远老乡院里的几间小房子。那时候,父亲的工资减了一半,但他仍旧在小沟头一家旧货店看上了一个不大的六成新有玻璃门扇的小书橱,星期天带我们去买了回来。里面自然又装满了他的书。“文革”中父亲被疏散到武都县城,住在西门里边的县工商联院中。病重时我去武都探望时,发现伴随父亲的除了两个破旧的箱子外,便是这个依然装满了书的已经显得陈旧的小书橱。
父亲去世后,我和西兄遵照老人遗嘱,各自选了几本文学名著外,其余的书连同书橱都捐给了县上。听侄女彦玲夫妇讲,父亲离兰时,屋里有许多书,让他们选了些,带到武都的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都捐给了政协图书室。后来我在靖远一中图书馆见到不少盖父亲名章的藏书,那是父亲初创靖中时捐给学校的。
父亲爱读书,也爱买书。他那一屋子摆满书籍的书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激起对于知识的崇拜和向往。长大了,我爱读书,也爱买书。即使是很清苦的时候,只要读起自己喜欢的书来,便快乐自信,便去憧憬和追求那美好的艺术世界。
父亲没有遗产留给我们,但我始终以为,对于知识的追求是父亲传给我们的无价可计的精神遗产。为此,我感激父亲,便也常常想起有关父亲书架和书的故事。
2004年8月1日增改旧稿于野趣斋
院子和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