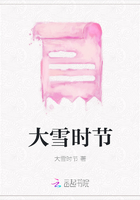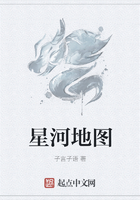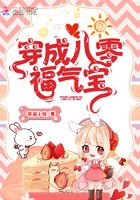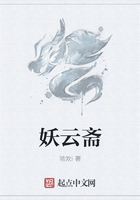上文的言说是力图把赵树理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关系给一个梳理,虽然从中看到赵树理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意识,是对以前所谓赵树理是“党”的政策的阐释者的观点的反驳,可得出赵树理对自身的存在价值是非常坚定地建立在“为农民实利”的立场上的。但这种研究仍是在意识形态的圈内言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而没有把赵树理知识分子意义的研究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剥离出来。事实上造成赵树理晚期自身困惑的是来自他自己对自己价值的消解与怀疑,这种消解与怀疑对他自认的知识分子价值具有真正致命的作用。在这种自身价值的独立思考中,更显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个案的意义。真正走进晚期赵树理的心态,来自于他对个人写作生涯的反思。
赵树理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时,立志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农民)写作,宣称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并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此后的创作,赵树理站在大众现实关涉的价值立场,创作出了大量的杰出的“问题小说”。但在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后,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显示出对紧贴现实的、为大众的“问题小说”价值的怀疑与消解。赵树理不仅对自己小说的读者对象产生了怀疑,而且对自己小说的价值意义产生了怀疑。
从1955年1月《三里湾》发表一直到1957年11月重写《金字》,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竟是一片空白。《金字》原是作者1933年于太原写的,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我”,作为一个乡村教师被夹在统治者与被压迫乡民之间的尴尬处境中,尽管“我”的立场是站在群众的一边,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受命为鱼肉百姓的统治者书写歌功颂德的“金字”。在1957年11月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赵树理以回忆的方式重新发表《金字》,又一反赵树理“问题小说”风格,小说具有某些暧昧的象征意义,实是大有人生况味。在这“新时代”,对于知识分子、上层统治者、下层民众三者的关系,赵树理感到了犹豫、困惑、惆怅、无奈。虽然30年代的时代背景远离新时代的意识形态,但仍可以曲折艰涩地流露出赵树理内心深处自己说不清楚的这种疑惑,他又明确警觉到这种个人情绪在当时体制中的危险性,申明自己只是“偶一为之”。1962年8月《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赵树理说:“抗风是多种形式的,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脱离群众……这种人物并不是不可以写的。抗风也有调皮捣蛋很巧妙的方式。有的还跟县委调皮。但有好多是不好写,不能写”,“主流层有好多文章可做”,“文艺好反映就反映,不好反映就算了。很微妙的来写它,找不到微妙的办法不写也可以。束为同志谈的集体和个人的矛盾很得几年写。”
这全是在言文艺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究竟哪些东西“不好写,不能写”,“要微妙的来写”呢?在此,我们可以理解赵树理作《金字》时的那种犹豫和困惑,在1957年那种复杂多变的政治与文艺语境中,赵树理是欲言又止,极尽委婉曲折。而这一开头,赵树理的小说开始脱离了“问题小说”的路子。
经过1959年中国作协内部的批评,赵树理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个人风格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主导面由明朗隽永转向含蓄沉郁”。此后到1960年的三年间他平均每年只有一个短篇,《老定额》(1959.10),《套不住的手》(1960.11),《实干家潘永福》(1961.4),1962年三个短篇,《杨老太爷》(1962.2),《张来兴》(1962.5),《互相鉴定》(1962.10),1964年1月发表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卖烟叶》。
作者虽言《老定额》是意在批评公社制下大队干部“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积极性”的指导思想,但小说中主旋律的东西已经相当冲淡,而作者对乡村乡民(不分村民和干部)在暴风雨前抢收庄稼的火热劳动场面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这是对劳动本身的赞美,对不务虚名的劳动者及生产劳动过程本身的赞美。这种脉络延伸到《套不住的手》中,这是一首关于一位76岁乡村劳动者的赞美诗,由人而赞美劳动,赞美朴实勤劳、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老舍言“文字极为朴素严整,不像赵树理同志以往的文章那么风趣”。《实干家潘永福》直陈潘永福的实干之德、经营之材,“实利主义”。《张来兴》的重心落在了人物耿直的个性上,对不畏权势的“人格”的赞赏,是对在张来兴身上所体现的人的尊严的尊敬,张维在把张来兴借给何老大时,破坏了厨师的行规,损害了张来兴的人格尊严,同时也损害了劳动的神圣性。在以上这些篇章中,赵树理的中心并不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而是回到了对人类劳动、创造力、求实精神的礼赞,回到了对人类的若干基本价值的发掘和探索之中。而这种人类基本价值,又是在老一代人的身上所保存,如“快五十岁”的林忠、“已经是76岁的老人”的陈秉正、“56岁的”潘永福、“75岁”的张来兴等。在这老一代人身上有一种无可动摇的自我认知,一种对尊严和价值坚守的立场。
赵树理的这种倾向脱离了他原先的“问题小说”、为农民看的“文摊文学”的路子,小说不再是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再是通过“小”字辈式的新人物来昭示未来,以“老”字辈式的守旧落后来显示历史,最终以新代旧;而是转向“文坛文学”,以老一代人来体现某种“人”的精神价值,基本价值。赵树理自己也说:“后来写的这几篇,我知道对象不是农民了,艺术形式究竟走哪边,我还打不定主意。我要写的《户》,恐怕还并不是给群众看的。”
从小说的发表刊物看也许也有此意:《金字》1957年发表于《收获》第三期,《老定额》195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套不住的手》1960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一月号,《实干家潘永福》1961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四月号,《张来兴》1962年发表于《人民日报》十九日,《互相鉴定》1962年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号,《卖烟叶》196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一至三月号。曾经为了能让老百姓买得起自己的书,赵树理把自己的作品不给稿酬高的《人民文学》,而给通俗文学,如今如此集中地在这中国可称最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其预设的读者对象也发生变化了。而且在这七篇小说中除《套不住的手》、《张来兴》没明言外,赵树理都在强调小说的自动写作,所说的自动写作该是指这些作品不是“赶任务”赶出来的创作,是自己自愿所为,自是远离了主流话语的体系。
这种转向明显显示出赵树理对自己原先的、紧贴现实的、为大众的“问题小说”价值的怀疑。首先是赵树理对自己小说的读者对象产生了怀疑,自己的小说果真是农民所需要的吗?《邪不压正》发表后,“我所期望的主要读者对象,除了有人给我来过一份信之外,我还没有机会了解到更多一些人的读后感,因此还断不定一般效果如何”。《三里湾》印数虽不少,但“不久以前,我才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农民买书的机会很少”,“工人、干部、学生都需要一部分,下到农村的就没几本了”。
“过去我写的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尽量写得通俗易懂,本意是让农民看的,可是我做了个调查,全国真正喜欢看我的小说的,主要是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真正的农民并不多。这使我大失所望。”
打青年时代就立志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到头却发现农民尚不具备基本的阅读条件。晚年赵树理认为自己打算写的长篇小说《户》“恐怕还并不是给农民群众看的”,这在赵树理是怎样的酸楚与痛心啊!他所认同与期待的乡村农民不具备文学作品的接受能力,而能够阅读其作品的乡村读者(主体为乡村中学生)则多半与他的价值方向背道而驰——赵树理希望他们能够安心于农村生产,而他们则想方设法要离开农村。在临终前的拘押中,面对一位冒险前来探望的家乡大学生,赵树理更是发出了如此充满困惑又令人惊心动魄的询问:“农家子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人还是教育了人?”
由此可见,赵树理不仅对他小说的读者对象产生了怀疑,而且对自己小说的价值意义产生了怀疑。
而在小说《互相鉴定》与《卖烟叶》中,赵树理流露出的甚至是对自己“写作”本身价值的怀疑。《互相鉴定》中主体对自己语言的把握产生了动摇,小说中刘正希望通过自己给县委李书记的信中所陈述的“事实”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事实是,他所言说的“事实”本身就不是什么事实。这封信传递出去之后,由于不同人的流传,信件“所指”的“事实”被不同的叙述者所言说而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刘正对自己的信件的“所指”失去了控制,被卷入了一场无法确切弄清的语言游戏之中,最终被以王书记为代表的权力话语所控制。
刘正的理想的破灭是对写作幻想的讽刺,这是否也暗示出赵树理本人对写作的一种怀疑?由此而下,《卖烟叶》更是进一步地反思“写作”行为。贾鸿年的写作动机是要通过写作来改变他务农的人生命运,他视写作如商业性的活动,当他认识到写作不可实现其理想时便从事更为直接的商业活动——卖烟叶。写作在贾鸿年这儿成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在王兰那儿写作成了有多义性、不可靠性的“能指”。王兰正是欣赏贾鸿年的写作才能而喜欢上了贾鸿年,她把贾鸿年的信当作宝贝似的保存着,时常拿给好友周天霞欣赏,但在后来王兰又从这些信件中找到了贾鸿年的坏思想,信件在不同的时期有了不同的意义。李老师因自己“业余作家”的身份而欣赏贾鸿年的写作才华,结果自己被贾鸿年蒙骗。李老师的写作并没能有效地教育帮助贾鸿年,而真正有效的却是国家机器的直接干预。写作在贾鸿年这儿变成了一种使青年导向危险境地的东西,使青年产生不切实际的种种幻想,而且是一种危险的力量,是一种陷阱。在这种情绪里是否含有一种赵树理对自己写作经历的自嘲?当解放区“发现”赵树理后,他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意识形态的言说秩序,《小二黑结婚》被政治意识形态误读,赵树理“为农民实利”的文学价值追求就被打了折扣,他的真正的创作意图被逐渐地部分地消解掉了。当他以“方向”的代言人出现时,主流意识对赵树理文本的评论已远离了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同时他又为此而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批判。20世纪60年代的“大批判”更是远离了文艺的批判,他被贫农代表陈永贵斥为“贫下中农的死敌”,这种荒诞性使赵树理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小说本文的“所指”意义,真正是陷入了如同“刘正”的困境中,最终被驾驭控制语言和符号的权力机构的秩序所捕获,失去了言说的自由,而曾是他安身立命的为农民的、大众化的“地摊文学”的追求只不过是个虚幻出的美梦罢了。
总观赵树理后期的这七篇小说的创作,唯一正面的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价值是实际的“生产劳动”,无论是老一辈人身上所体现的,还是与写作青年相对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从事生产劳动的青年身上所体现的。在赵树理这里,生产劳动体现了真实价值的存在,生产劳动也使人获得了自我存在的确认。这种价值定位再一次展示赵树理深层意识中三晋文化求“实”的底蕴。但这种求“实”的劳动定位引起了赵树理更深层的自身矛盾,他自己的一生就是跳出生产劳动后在写作中存在的,如此地确认生产劳动的价值意义也即对写作的放逐,这样他本人的存在意义也恰恰被放弃掉了,他一生的写作意义也将受到怀疑。由此可见,赵树理在此进入了“文学是什么”、“写作是什么”的孤独而矛盾的思考中。这种思考不再是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纯现实层面的,而含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从赵树理当年立意“文摊”要作“为农民实利”的大众化文艺到晚年对其理想的深刻怀疑可以看出,他的理想追求与农民的实际利益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背靠背”的状态,仍是知识分子式的对农民单向度的关注,而非彼此双向的交流。农民不识字的现状使其根本不可能与那些为他们写作的知识分子进行沟通与交流,因此横亘在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民之间的这道障碍不是大众化启蒙的知识分子在现实可跨越的。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剥夺了下层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力,都市出生的知识分子又不可能真正理解农村的实际现状,就算是熟悉农村实际状况的赵树理这样的知识分子出现,为生存而奔波的底层农民仍不可能受到现代教育而与赵树理进行交流。赵树理所坚持的文艺大众化在当时的现实农村中只能是一种善良而又美好的个人愿望,可望而不可即。纵观现当代文学对农村世界的关注,依赖于五四以来都市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价值观念———对农村民众的启蒙只能是一种远距离的观望,而依赖于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现状的熟知,对农民“实”利的关注而作大众化的努力,结果仍是赵树理式的“背靠背”的结果。鲁迅认识到自己无法启蒙闰土、祥林嫂等人后“逃异地,走异路”,逃往知识分子聚集的都市,这是现代意识知识分子的“大逃亡”,他不再做启蒙大众的梦,而去做启蒙与自己一样的启蒙者的梦了。赵树理痛苦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位为民鼓呼的知识分子在“体制”面前的无力、软弱与渺小,这种痛苦必然导致他转向自我考问——我究竟能为农民做些什么,我究竟拿什么确认我的存在价值。但赵树理没有鲁迅那样高的历史意识及自觉,三晋文化求“实”的精神孕育出他对“实”的坚守时也染上了固执与倔强,他仍想通过戏剧的改造来达到他的理想。1964年创作的《十里店》是他倾注全部心血的临终绝唱,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现象。虽然他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一再修改,但仍难逃厄运,在太原仅上演一场即遇停演。正如鲁迅表现的,在那样的现实环境中,不去“逃亡”的赵树理,坚守在农村,降临的便是魏连殳和范爱农式的命运。曾经被定为“方向性”的代表作家在晚年一次次地挨批挨斗,终在“堆着三张桌子的高台上被红卫兵猛推到地,腰被打断了,肋骨也被打碎了,打断的骨头扎到了肺叶”,永远地闭上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