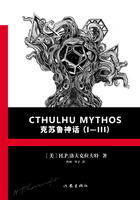“好罢,”索密斯说,转身要走,又说:“看他这样子使我很伤心,很痛苦。”
“唉!先生,”斯密沙儿焦急地说,“您不能这样看。他现在不要烦神,就可以过得非常快活,的确快活。就像我跟厨娘说的,倜摩西先生比从前更像个男人了。您知道,他不散步或洗澡时,就是吃饭;不吃饭时,就睡觉;就是这样。身上没有一个地方痛,心里没有一点记挂,什么都没有。”
“嗯,”索密斯说,“这话有点道理。我要下去了。噢,对了,我要看看他的遗嘱。”“我要等到一个时候才能取出来,先生,他把它放在枕头下面,当他在活动的时候会看见我的。”“我只想知道是不是我替他立的那一张,”索密斯说,“你哪一大瞥一下上面的日期,再让我知道。”
“好的,先生,不过我敢说就是那一张,因为您记得,我和厨娘都作了见证,上面还有我们的签名呢,我们就做了这一次。”
“对,”索密斯说。他也记得。斯密沙儿和厨娘珍妮都是正式见证,但是遗嘱上并没有给她们留下什么,为了使她们对倜摩西的死无所希企。他完全承认这件事情做得简直小心过头,但是佣摩西要这样做,而且说到底话,海丝特姑太已经给了她们不少啦。
“好吧,”他说,“再见,斯密沙儿。好好地照料他,哪个时候他留下什么话,你把它记下来,告诉我。”
“好的,索密斯先生,我一定照做。今天碰见您来,真是新鲜事。厨娘听到准会高兴得跳起来。”
索密斯跟她握完手走下楼。在那只帽架跟前足足站了有两分钟之久,过去把帽子挂在上面不知有多少次呢。“就这样子整个成为过去,”他想着,“过去了又重新开头。可怜的老头儿!”他侧耳细听,盼望倜摩西拖竹马的声音说不定会从楼梯问传下来;或者说不定会有什么一张鬼魂的衰老的脸从楼梯栏杆上面露出来,同时一个苍老的声:说:“怎么,亲爱的索密斯吗!我们刚才还说有一个星期没有看见他呢!”没有-一点没有!只有一股樟脑味和穿过门上面扇形窗格的口光照出的灰尘。这所古老的小房子!真是一座古墓!他转过身来,走出大门,赶火车去了。
回乡。
他的脚踏着家乡的原野,
他的名字是-瓦尔·达耳提。
就在这同一个星期四的清晨,瓦尔·达耳提(他今年是40岁了)从自己在南撒州高原北部租下的人宅子里走出来,他的心情正有点像上面两句诗所反映的那种心情。他的目的地是新市。自从1899年秋天,他从牛津溜了出来去看剑桥州的障碍赛之后,这地方他到今天还没来到过。他在门口停下来,跟妻子亲一个吻,同时把一小瓶波得酒塞进口袋。
“不要过分走累了,你的腿,瓦尔,而且不要赌得太多。”
有她的胸口抵着自己胸口,眼睛望着自己的眼睛,瓦尔对自己残废的腿和钱袋都感觉放心了。他应当有点节制,好丽的话永远是对的-她有一种天生的才干。她的脑子转得很快,总是那样机灵地及早看出他的心情。自从波尔战争时在南非那边成令了他们的浪漫婚姻之后,这二十年来他竟而对自己这位年轻的表妹极端忠实,不但忠实,而且丝毫没有感觉到是一种牺牲或者厌倦的感觉,这在他自己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可是在别人眼中那简直是奇事-他究竟有一半达耳提的血液啊!她是那样的敏捷,总是比他机灵,善解人意。由于两人是第一代表亲结婚,他决定,或者毋宁说好丽决定,不生孩子,虽然她的脸色黄了一点,却保持了美观和苗条身材,以及头发的浓郁颜色。瓦尔特别佩服她在照顾自己的生活外,骑术还能够一年比一年娴熟,并且拥有她自己的生活情趣。她始终不放弃练琴,而且书看得很多-小说、诗歌,什么都看。他们在哥罗尼角那边办农场时,她把农场上所有的黑人妇孺照顾得都非常之好。说实在话,她真是聪明,然而一点不小题大做,一点儿不自命不凡。瓦尔为人虽不怎样谦虚,却逐渐承认她比自己强,而且并不妒忌-这是对好丽最大的尊重。人们说不定会注意到,他看好丽时,好丽从没不觉察,而好丽看他时,他却有时候不知道。
他在门廊里吻了她,因为在车站月台上不打算这样做,尽管她要陪他上车站并把车子开回来。非洲的天气和养马的辛勤使他的脸色黑了一点,而且皱纹多了,那只在波尔战争受伤的腿又使他行动不大方便-不过可能在刚结束的这次大战中却牧了他的命-除此以外,他看上去还和当年向好丽求爱时差不多,笑起来仍旧是嘴咧得多大的,仍旧那样迷人,他的睫毛变得更浓、更深了,睫毛下面的眼睛眯起来仍旧是那种鲜明的淡灰色,雀斑深了些,两鬓微微花白。他给人家的印象是一个在阳光充足的气候下和马在一起勤奋生活过的人。
他在大门口把车子猛然转一个弯,问道:
“小佐恩几时来?”
“今天。”
“你要给他买什么东西吗?我可以星期六带下来。”
“没有,不过你可以搭芙蕾的那班车一同回来-1点40。”
瓦尔把福特汽车开得飞快,他开车子仍旧像男人在一个新国家的坏路上开车子一样,决不放慢,而且准备碰上凹坑时就送老命。
“她是个头脑清楚的女孩子,”瓦尔说,“你觉得不觉得?”
“是啊,”好丽说。
“索密斯舅舅跟你爸爸-关系不是不大好吗?”
“不能让芙蕾知道,也不能让佐恩知道,当然,什么都不能提。只有五天,瓦尔。”
“场内秘密!行!”只要好丽说不碍事,那就不碍事了。好丽狡黠地打量他一下,说道:
“你可看出她要我们请她时说得多漂亮啊?”
“没来看出!”
“就是这样。你认为她怎么样,瓦尔?”
“漂亮,聪明,可是我敢说,她一发起脾气时,什么时候都会跟你闹别扭的。”
“我弄不懂,”好丽咕哝说,“她是不是就是那种时髦的年轻女子。回国碰上这一大堆情形,真让人有如堕五里雾中。”
“你?你很快就摸熟行情了。”
好丽一只手插进他的大衣口袋。
“你使人能熟悉内幕消息,”瓦尔说,鼓舞起来。“那个比国佬普罗芳德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有点像个‘好魔鬼’。”
瓦尔笑了。
“他在我们家的客人里真是个怪人。老实说,我们族里已经闹得很不体面了,索密斯舅舅娶了个法国老婆,你爹又娶了索密斯的第一个妻子。我们的祖父击看到这种情形,准要晕倒。”
“哪一家的老一辈子都会这样,亲爱的。”
“这个车子,”瓦尔忽然说,“要踢两脚才行,它的后腿上坡时简直不得劲。下坡时我得放一下手才能赶上火车呢。”
山于爱马的缘故,他对汽车总是没办法同样具有好感,所以这部福特,他开起来总和好丽开起来看去有点两样。火车总算赶上了。“回去当心些,不然它就会把你摔下来。再见,亲爱的。”
“再见,”好丽喊,向他飞一个吻。
在火车里,他有一刻钟徘徊在好丽、早报、晴朗的天色和新市的模糊回忆之间,后来就埋首在一本方方的小书里去,书里全是马名、血统记录表、主支以及关于马的外表形状的注释。他的福尔赛世家血统使他一心要弄到一匹名种,可是他现在仍旧坚决压制达耳提家性格里那个发一笔大财的念头。他自从把南非那边的农场和马匹卖掉,赚了一笔钱回到英国来,就看出这儿很少出太阳,他跟自己说:“我非得有点消遣不可,不然这个国家就会使我消沉下去。打猎还不够,我得养马和训练跑马。”由于在一个新国家里居住了多年,比别人特别精明一点、决断一点,瓦尔看出近代养马术有它的弱点。那些人全着迷在时尚和高价钱上面。他要买筋骨好的马,种名滚他妈的!然而这时候他已经对某一血统着了迷了!他半意识地想着:“这个浑蛋气候真有点鬼,弄得人团团转。没有关系,我一定要买一匹有梅弗菜血液的。”
他怀着这样心情到达了自己梦想的地点。这是一次比较清静的赛马,那些喜欢看马而不喜欢看以赌赛马为生者的面孔的人,最感兴趣了,瓦尔始终都盯着溜马的场子转。二十年的殖民地生活,使他摆脱掉从小养成的纨祷习气,只剩下爱马者的那种十足整洁的派头,某些英国男子的“嘻嘻哈哈”派头,和某些英国女子的“浓妆艳抹”打扮,他全看不入眼,觉得又特别又可惜-好丽一点不是这个样子,而好丽就是他的理想中的典型。他眼明手快,人又机智,一上来就考虑着怎样作一笔交易,挑一匹马,再喝它一杯酒。当他眼望着一匹梅弗莱牝驹走去时,靠近他身边有人慢吞吞地说:
“瓦尔·达耳提先生吗?达耳提太太怎样?很好吧,我希望如此。”他看出原来就是他在自己妹子伊莫全家里碰见的那个比利时家伙。
“普罗斯伯·普罗芳德-我们曾经一起吃过午饭,”那声音说。
“你好?”瓦尔咕哝一声。
“我很好,”普罗芳德先生回答,他笑得那样慢吞吞的,简直没有人学得了。好丽称他是个“好魔鬼”。哼!这两撇浓浓的、剪得很尖的上须,倒有点魔鬼派头,别人会认为他懒洋洋的,很懂得幽默,眼睛长得很秀气,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聪明才智。
“这儿有一位先生想认识你-你的一位舅父-乔治·富西特先牛。”
瓦尔看见一个大块头,胡子剃得光光的,就像一头公牛,双眉微皱,一双深灰色的眼睛里蕴含着讽刺的幽默。他隐隐记得旧时跟他父亲在伊希姆俱乐部吃饭时曾经见过这个人。
“我过去常跟你父亲一起看赛马,”乔治说,“你的马养得怎么样?要不要买一匹我的马?”
瓦尔笑起来,借此掩饰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养马已经不时髦了。他们这儿什么都不当做一回事,甚至连养马也不当一回事。乔治·福尔赛,普罗斯伯·普罗芳德!连魔鬼本人都不见得比这两个人更加看透一切呢。
“我还不知道你是个赛马者,”他对普罗芳德先生说。
“我不是。我不喜欢跑马。我是个游艇手,却不喜欢驾游艇,不过我喜欢看看我的朋友。瓦尔·达耳提先生,我备了少量的午餐,就是一点点,你可愿意吃一点,不多-就是少量的午餐-在我的车子里。”
“谢谢,”瓦尔说,“承情之至。我大约一刻钟后就来。”
“就在那边。富西特先生也来的,”普罗芳德先生用一只戴了黄手套的指头指了一下,“小小汽车里吃顿小小的午餐,”他向前走去,穿得一身笔挺,却是懒洋洋的,神情淡漠。乔治·福尔赛跟在后面,又整洁,又魁梧,一脸的滑稽样子。
瓦尔仍旧站在那里望那头梅弗莱牝驹。乔治·福尔赛当然是个老家伙了,不过这个普罗芳德说不定和自己一样大,瓦尔觉得自己年纪特别小,好像这匹梅弗菜牝驹是这两个人嘲笑的玩具似的,那马已经变得不真实了。
“这匹‘小’雌儿”他好像听见普罗芳德的声音说,“你看中它什么地方?我们全得死啊!”然而乔治·福尔赛,他父亲的好朋友,却还在赛马,梅弗莱血统-这比别的血统究竟好多少呢?还不如把他的钱赌一下的好。
“不行,傻瓜!”他忽然喃喃自语起来,“要是养马都没有意思,那么做什么事情也没有意思!我来这里做什么的?我要买下它。”
他退后两步,看那些到草场上来的客人退向看台去。服饰讲究的老头子,精明而壮硕的汉子,犹太人,天真得就像是一生从来没来见过马的教练员,轻佻而懒散的高个子女人,或者步履轻快、大声说话的女人,神情装得很严肃的年轻人-有两三个人都只有一条胳臂!
“人生在世界上就是赌博!”瓦尔心里想,“摇铃一响,马跑起来,钞票就换手;铃声再起,马又跑起来,钞票又回来了。”
他对自己竟而有这种哲学见解颇为骇然,就走到草场门口去看梅弗莱牝驹慢跑。它的动作不坏,所以他就向那部“小小”的车子走去。那顿“小小”午餐是许多男子梦想到而很少吃得到的。吃完午餐,普罗芳德陪他回到草场那边去。
“你妻子是个漂亮女子。”他出其不意说了一句。
“我知道她是最漂亮的。”瓦尔冷冷地回答。
“是啊,”普罗芳德先生说,“她的脸蛋儿很漂亮。我就喜欢漂亮的女子。”
瓦尔有点怀疑地望望他,可是这个同伴的浓厚的魔鬼性格中夹有一种好意和直率气味,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哪个时候你们高兴来坐游艇,我愿意带她到海上游弋。”
“谢谢,”瓦尔说,重又不放心起来,“她不喜欢航海。”
“我也不喜欢,”普罗芳德先生说。
“那么你为什么要驾游艇呢?”
比利时人的眼睛露出微笑。“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事情都做过了;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一定他妈的很花钱呢。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够。”
普罗斯伯·普罗芳德先生的眉毛抬了起来,撅出厚厚的下唇。
“我是个很随遇而安的人,”他说。
“你参加了大战吗?”瓦尔问。
“对-啊,这个我也做了。我中了氯气,有点小小不好受。”他带着一种深厚而懒洋洋的富贵神气微笑着。他不说“稍微”,而说“小小”,是真正弄错还是装腔作势,瓦尔可拿不准,这个家伙显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时那匹梅弗莱牝驹已经跑赢了,一群买主正围成一个圈子,普罗芳德先生站在人群当中问道:“你打算叫价吗?”
瓦尔点点头。有这样一个懒洋洋的撒旦站在身边,他觉得必须有个坚定的信念才行。虽然他外祖父事先料到,遗留给他每年一千镑的定息收入,再加上好丽的祖父遗留给好丽的每年一千镑定息收入,使他能免于破产的威胁,他能动用的资本并不是很充裕,卖掉南非农场的那笔钱大部分已经用在南撒州的产业上了。所以叫买叫了没有多久,他就盘算:“他妈的!这已经超出我的价钱了!”他的极限-六百基尼-已经超出,只好不再叫价。那匹梅弗来牝驹在七百五十基尼的叫价下拍了板。他正在着恼地转身要走,耳朵里却听见普罗芳德先生慢吞吞的声音说:
“哦,那匹小牝驹是我买下了,不过我不要,你拿去送给你的妻子。”
瓦尔看看这个家伙,重又疑虑起来,可是他眼睛里的善意却使他实在没法生气。
“我在大战时发了一笔小小的财,”普罗芳德先生看出瓦尔脸上的狐疑,说道。“我买了军火股票。我要把钱花掉。我一直都在赚钱。自己的需要很小。我愿意我的朋友拿去用。”
“我照你的价钱向你买,”瓦尔突然拿下主意。
“不,”普罗芳德先生说。“你拿去。我不要它。”
“他妈的。一个人不能-”
“为什么不能?”普罗芳德先生微笑说。“我是你们家的朋友。”
“七百五十基尼又不是一盒雪茄,”瓦尔忍不住说。
“好吧,你就替我养着,等我要的时候再说,你爱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
“只要仍旧是你的,”瓦尔说,“我倒也无所谓。”
“那就这样吧,”普罗芳德先生咕哝了一声,走开了。
瓦尔在后面望着,心想他也许是个“好魔鬼”,可是也说不定不是。他望见他和乔治·福尔赛世家又走在一起,这以后就不再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