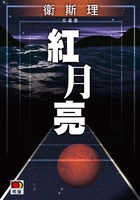郑楠拉着白冰雪就往外走,苏警己也只好跟在他们身后。在医院门前的饭馆里,郑楠先给在救护车里守着老娘的白冰雪的哥哥和司机老梁安排了饭菜,然后领着白冰雪和苏警己往医院的家属区走去。到了二号楼进了一个门洞,走到二楼郑楠伸手按了左边的门铃,就有一个白胖的中年妇女开了门。郑楠说,妈,这是我的同事。郑楠的母亲热情地让他们进屋,屋里的壁灯亮着,柔和的光线照在猩红色的地毯上,乳白色的组合家具舒软的组合沙发二十四寸日立彩电,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看得苏警己眼花缭乱。苏警己仿佛一下子跌进深渊里去,他锁住自己的嘴巴坐在沙发里微微地闭上眼睛,他不想让眼前的东西刺激他。桌上的饭菜索然寡味,他讨厌郑楠那种得意的样子,他讨厌白冰雪和郑楠的对话。他们说话的声音像针一样刺着他的耳孔。郑楠喝醉了酒一样在夸夸其谈,他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他在那副高度近视镜后面闪烁的神采。在苏警己的印象里,郑楠是个有着和他同样爱好孤僻的人。在月光幽幽的夜晚,他常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到河道里溜达,即使到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往往还能在他黑色的皮鞋上看到残留着黄色泥巴。在那所乡村医院里,似乎没有一个人能看透这位医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当今天郑楠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时候,苏警己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人。这位面目白净的同事的确不寻常。在下午他们回到锦城医院的门诊大楼里之后,郑楠没用十分钟就办齐了去做CT的手续。苏警己坐在CT室旁边的椅子上只有一个念头,他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在锦城医院里,他同一个没有出过门的乡巴佬没什么两样。
老人终于出来了,白冰雪和她哥哥守护在她身旁。可是郑楠没出现,他在等待着诊断结果。尽管苏警己开始有些讨厌他,但现在他渴望着他能快点回到这里,来了结这一切。没有他,他的心被一种东西压抑着,这个平时他不太注意的郑楠在他生活里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他仿佛是一盏替换红光的绿灯,当郑楠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有一些恐慌正悄悄地云集在苏警己的眉宇之间。他从他的眼镜后面感受到了一丝在温雪的天气里才有的神情,他没有说话,他只是朝白冰雪和她哥哥使了个眼色,白冰雪和她哥哥跟着他走到一边去,没有谁看苏警己一眼,他就像不存在似的。在那一瞬间,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最大程度的伤害。在这里他是无关紧要的,就像走廊里随便一件什么摆设,椅子,或者痰盂什么的,可有可无。一种愤怒侵占了他的心。他想,走,离开这里,一刻也不能停留!他站起来,也跟着走过去。
郑喃说,片子明天才能出来。不过,基本可以确诊,是脑瘤。
脑瘤?从白冰雪嘴里吐出来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别紧张。郑楠看一眼走过来的苏警己说,可能是胶质的,在中脑,已经有鸡蛋那么大了。
白冰雪的哥哥眼里立刻涌动着明灿灿的泪珠,他说,那怎么办?
郑楠说,现在有两个办法,一是手术,二是保守治疗。
白冰雪说,保守治疗?那不是等死吗?动手术。
苏警己说,不能手术。
白冰雪说,为什么不能?
年纪太大了,七十六了,不能做。苏警己说,你知道,这种手术又不能打开脑盖骨,只有在一边打孔。
郑楠说,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些,先住下,做与不做,等明天片子出来,有了结论再说。
苏警己说,不做,肯定不能做,不做又干吗住下?走,现在就走。
白冰雪说,住下吧。
苏警己说,你为什么不明白?老人这么大年纪,就是住下也不能做。
你怎么老说这话?不能做,不能做,难道你看着让俺妈死吗?
苏警己慌忙解释说,看你看你,你知道做这手术有多么大的难度吗?脑神经那么复杂,目前只有北京、上海能做,我们锦城,只是一个地区医院,能有这水平……
白冰雪生气了,她说,你拿个喇叭吆喝去吧,就你有这样的水平?
苏警己说,我是没这水平,但我是医生,我清楚做下来的后果,如果落个瘫痪……
白冰雪说,那是俺妈,又不用你侍候。
好好好。苏警己说,算我没说,你说走不走吧?
白冰雪白了他一眼说,不走!
你们不走我走。他再也不能忍受,说完,他转身沿着走廊往楼梯口走去。
十
夜色打了一个趔趄,一下子跌倒在苏警己的眼睛里。在这之前,在那辆救护车从锦城路过陈城驶回颍河镇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察觉到夜的临近。在他大脑的屏幕上涌动着波浪,那波浪撞击着海岸边的岩石,发出了类似人类在临近死亡时所发出的喊叫声,那声音使人感到恐惧。起初,苏警己想从那些绝望的喊叫声里找出一些他熟悉的声音,结果他很失望。在汽车的颠簸里,他一次又一次做着努力,想从中找到母亲和奶奶的喊叫声,可是这种努力最终还是没有一点结果。尽管如此,幻觉中的绝望的呐喊已经深深地感染了他,以至影响了他在往后几天里的心情。苏警己走下车来,就在这个时候,夜猛地一下子在他的眼前展开,一处又一处在黑暗里闪亮的灯光让他感到陌生。他看着司机说,这是哪儿?
老梁说,到家了。
在夜色里,苏警己走过花坛,然后穿过一个又一个圆形的拱门,但这些对他来说好象不存在似的,他在海浪撞击岩石的声音里回到了住室里。在灰红的灯光下,屋子里的一切似乎改变了旧日的模样。一天的奔波让他感到劳累,他在床上躺下来。睡吧。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无法入睡,一件又一件陈旧的往事从眼前闪过,可奇怪的是那些从眼前闪过的往事他一件也没有记住。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想,拉灯睡吧。可是灯光一消失,他就在黑暗里看到一扇明亮的门洞,门洞里嵌着一个黑色的影子。那是他的母亲。母亲就那样在他的眼前吊着,一双脚把厚厚的积雪划出两道深沟。妈,你就这样走了吗?你就没想想你这可怜的孤独的儿子吗?他这样想着突然泪流满面。他说,妈。他折身坐起来,那个黑影就不见了。他听到有个脚步声由远及近,来到他的身边停住了,他看到有个女人在他身边躺下来,那是秋霞。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说,秋霞。秋霞坐起来,苏警己看到有光从洞开的房门里照在她的背后上使他无法看清她的面孔,他只能通过她的剪影看到秋霞脸上茸茸的细毛,只能看到她的眉骨她的鼻梁她的嘴唇她的下巴和她的脖颈组成的优美的曲线。那曲线使他热血沸腾,他忍不住伸手去摸他的脸。秋霞说,你想叫我死吗?他说,我不想叫你死。她说,你干吗让我吃那么多药?苏警己说,那不是我。秋霞说,是你,就是你!秋霞伸手卡住了他的脖子,她说,我也叫你死!苏警己感到难受,他想推掉那双手,可他没有一点力量。我就要死了。他的胳膊无力地垂落下去,落下去的手却意外地触到了电灯开关,叭--灯亮了。苏警己醒了。他翻身坐起来,伸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思想仍然沉溺在梦中的恐惧里。四周的夜很静,他转身看了看墙壁上的钟表,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三点。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外边的甬道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最后在他的门边停住了。他屏住气看着他的房门被推开了。姜仲季意外地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姜仲季劈头朝他问道,你跟谁说话?
苏警己感到莫明其妙,他说,没跟谁说话呀。
姜仲季走进来,他一边走一边说,肯定有,你们说话像吵大架一样,刚才我站在门口时你们还在说呢,她人呢?
胡说八道,哪有人?根本没有。
姜仲季肯定地说,不但有,而且是个女人,是秋霞!你把她藏在哪儿?
一说到秋霞,苏警己突然就清醒了。
她说她在你的被子底下,让我看看。姜仲季说着掀开了被子,床上只有苏警己。姜仲季说,秋霞,你在哪?在门后头?姜仲季说着,转身就奔到门边去寻找。苏警己抬腿下了床,来到桌前拉开抽屉打开一个瓷盒,从瓷盒里取出一个针管,插上一个针头,然后拿起一管药液。他把那管药液举在空中,在灯光里查看着,他看清药管上印着“三氟拉嗪”的字样就抬手用针管把药液敲开了,接着把药液吸进针管里。
姜仲季说,你把她藏哪儿啦?
苏警己拿着注射器走过来,他说,脱裤子,脱了裤子我告诉你。
姜仲季说,她在我裤子里?
苏警己说,对,她在你的裤子里。
姜仲季就把裤子脱下来,他一边脱一边找,在哪儿?她在哪儿?
苏警己说,你看不见,来,我给你拿出来。他说着,就把针刺进了姜仲季的屁股里。
姜仲季叫了一声,就平静下来。他说,走吧。平静下来的姜仲季站在那里,苏警己推了他一下,他就往前走。苏警己跟着他一直把他送到病房里。等他往回走的时候,在夜风的吹拂下他突然感到有些头痛。他想,无论如何我也得好好地睡一觉。
可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苏警己仍然感到有些头痛。他呆呆地坐在床边,隐隐地感到有些饥饿。他这才恍惚记得,从昨天上午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好好地吃过饭。他想,他的头痛可能和饥饿有关。他想了想,就拿起碗筷朝食堂里去。阳光从院子东边照过来,撒在路边冬青的叶子上,叶子上的露珠在苏警己的感觉里仿佛变成了一些绿莹莹的眼睛,从那些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光使他感到寒冷。行走的脚步震动着他的肚子一沉一沉的,这使他想到了排泄。苏警己把饭碗放在甬道边水池的池壁上,然后走进了厕所。他蹲在池子上放了两个虚屁,可怎样努力也不觉得有内容排出来,这使他烦恼。他听到隔壁有纷乱的脚步在走动,接着响起了滋滋的排尿声。有个女孩在隔壁说,你听说了吗?
另一个女孩也在隔壁说,说什么?
一个女孩说,苏警己。
一个女孩说,听说了。
一个女孩说,真想不到,看着整天斯斯文文,没想他竟能下那样的毒手。
一个女孩说,就是,他竟然把他老同学害死了。
苏警己的头轰一下炸了,怎么成了我害的?我一定要问个清楚!他提起裤子走出厕所,在女厕所的门前站定了。等那两个护士从厕所出来,他劈头就问,你们给我说清楚,是谁害的。两个小护士吓得脸色发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愣在了那里。苏警己愤怒地说,说呀,是谁害的。两个小护士忙对他摇手说,不知道,不知道。说着,她们就匆匆地逃走了。无风不起浪呀,今天我倒要问个清楚。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朝院长家走去,他把他的饭碗忘在了水池的池壁上。那对碗筷一直在那儿放了许久,后来有人认出了那是苏警己的碗,就用一把铁锨端着,扔到院子外边的垃圾堆里去了。
那天早晨苏警己来到院长家的时候,院长正和女局长一起用早餐。他们停住手中的筷子把苏警己让到沙发上。苏警己刚一坐下就对院长说,那个女人不是我害的。
院长说,看你,谁说是你害的?
苏警己说,可人们都在说。
院长说,谁?谁在说?
苏警己一时没有想起那两个小护士的名字,他愣愣地看着院长,他找不出说这话的人,他知道他就是找到那两个小护士她们也不会承认。是的,没有谁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害死了那个女人。可在他的感觉,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背后这样议论他,他说,人们都在说。
苏医生,要相信组织嘛。局长放下手中的筷子说,这起医疗事故正在调查中,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苏警己没有再说什么,他只好起身告退。他走在院子里,在感觉里始终有一个声音在跟着他说,是你,是你……他停下来,可是四周却没有一个人,他想找到一个人大声对他吼叫两声,不是我!不是我!可是,那是谁呢?姜仲季?是姜仲季!可是谁信他说的呢?又有谁来证明这是真的呢?白冰雪,只有白冰雪才能证明,只有她能证明。
在冗长的时光里,他焦急地等待着白冰雪的归来,然而等待的时光变得那样灰暗,如同一个无边无际的梦境。在这冗长的梦境里他回忆着一件又一件往事,无边的往事使他感到疲劳,他想躺下来好好地睡一会儿。可是,病人不断地来到他的门诊里就诊,他不知道他是怎样处理完那些病号的,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他只感到脑袋在轰轰作响。他讨厌这嘈杂的世界,可是那嘈杂的声音却无处不在。他站在走廊里,人们的说话声像锥子一样刺着他的耳朵。他走在通往住院区的甬道上,水管里流水的声音使他难以忍受。他看到那个穿红褂子的乡下姑娘蹲在水池边刷铝锅,她手里的钢丝球滑过锅体的声音险些把他的脑袋撕裂。他匆匆地穿过一道圆形的拱门,沿着一条两旁长满了冬青的甬道向前走,等他穿过最后一道圆形的拱门,那座白色的房子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在白房子的前面,那棵桃树上的花朵开得正艳,粉红色的花朵散发出着淡淡的清香。突然间外界所有的声音一下子消除了,这里显得是那样的宁静。苏警己站在桃树边,透过树枝上粉红色的花朵去看那座白色的房子。那座白房子的门敞开着,秀过敞开的房门,他隐隐约约地看到那辆停尸车孤独地待在空荡荡的房屋中间。
十一
白冰雪的母亲死在了手术台上。这消息并没有让苏警己吃惊,反而使他长出了一口气。这在他的意料之中,这证明了他主张的正确性。在安葬老人和老人安葬之后的这些日子里苏警己对这事只字不提。他认为这没什么必要,这样反而使白冰雪难堪。白冰雪臂戴黑纱在护士值班室里进进出出,在他面前过来过去没有一次正视过他,这正说明白冰雪的内疚。这些天来苏警己在她面前保持着沉默状态,他没有让她去证实氯丙嗪的事,但他内心安稳多了。他想这事总会慢慢平息的,只要有她在他身旁,其它一切都显得次要,显得无所谓,他想一切总归会正常起来的。可是他却缺少等待漫长时光的思想准备,冗长的时光使他几乎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这使他焦躁不安。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就像满天的乌云覆盖了他目所能及的空间,无边的压抑终于把他的精神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在全院职工大会上,女局长宣布了医院里的副院长的任命通知,但出乎苏警己意料,出任新副院长的不是他,而是郑楠。这突然的变化像一块巨大的石块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坐在会场上勾着头,直到熙熙攘攘的脚步从他的身边消失。最后,有一只手落在他的肩膀上。苏警己抬头看到了院长,他强忍着内心的愤怒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可是群众投票选出来的呀?
院长说,冷静些,冷静些。
苏警己说,当不当院长无所谓,可是这说明什么?难道真是我害死了那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