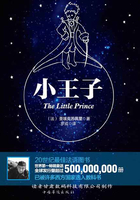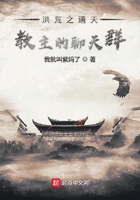“不过我缺少最重要的东西,”他回答,“我缺少权力欲。我曾经有过,但巳经过去了。”
“对不起,这可不是真话。”赛普克霍夫斯基微笑着说。
“是的,这是真的……目前是……我说的是实话。”渥伦斯基又说。
“是的,目前这是实话,这就是另一回事了,但‘目前’是不会持续到永远的。”
“也许吧。”渥伦斯基说。
“你说‘也许吧’,冶赛普克霍夫斯基仿佛猜到了渥伦斯基的心思,继续说道,“但我要说的是‘肯定’。这就是我要见你的原因。你的行为很正确,我完全能够理解。但你不能过于执迷。我只请你给我行动上的自由。我不是要庇护你……其实我为什么不可以庇护你呢?你庇护过我多少次了?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超越这些东西!是的,”他露出女人般温柔的微笑,说,“给我行动上的自由,你离开军团,我会悄悄提拔你的。”
“可你要知道,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求保持原状。”渥伦斯基说。
赛普克霍夫斯基站起身,站在渥伦斯基面前说:“你说‘我只求保持原状’!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你听我说!我们是同龄人,也许你认识的女人比我多。”赛普克霍夫斯基脸上的笑容和他的手势说明渥伦斯基无须害怕,他会小心谨慎地触碰渥伦斯基的痛处,“但我结过婚了,相信我,有人曾说过:‘只需了解一个你爱的妻子,就会比认识几千个女人更了解女人。’”
“我们马上就来。”渥伦斯基冲着那个被团长派来叫他们、正向房间里张望的军官说。渥伦斯基此刻急于听到赛普克霍夫斯基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就是我的立场。女人是男人事业最主要的绊脚石。爱上一个女人,又要有所作为,这是很难的。又要成功,又要无牵无绊地爱一个女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才能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呢?”喜欢打比方的赛普克霍夫斯基接着说下去,“等一等!等一等!是的,如果你又要拿包袱,又要用两手干活,就只能把包袱绑到背上,这就是婚姻。我结婚以后就明白了这一点。我的双手突然获得了自由。可要是你不结婚,拖着这个包袱,你的双手就腾不出来,就什么也干不了。瞧瞧马赞科夫,瞧瞧克鲁坡夫!他们全都因为女人毁了自己的前程。”
“可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女人!”渥伦斯基想起了同这些人厮混的法国女人和女演员,说。
“那就更糟糕了!女人的社会地位越稳固,情况就越糟糕!这还不只是像用手拖着包袱,简直就是从别人手上抢包袱。”
“你从没真正爱过。”渥伦斯基轻声说,双眼直盯着前方,脑子里想着安娜。
“也许是的!可还有一点:女人总比男人更讲求实际。男人觉得爱情很伟大,而女人总是很实际。”
“来了,来了!”他对走进来的仆人说。但仆人并不像赛普克霍夫斯基所想的那样来叫他们,他交给渥伦斯基一封信。
“您的仆人从贝特茜公爵夫人那儿带来的。”
渥伦斯基拆开信,顿时涨红了脸。“我觉得头疼,”他说,“我要回家了。”
“那好吧,再见!你给我行动上的自由吗?”
“再说吧。我到彼得堡会去找你的。”
巳经五点多了,为了不迟到,而且不使用人人都认识的自己的马,渥伦斯基坐上了亚希文租来的马车,嘱咐车夫尽量跑得快些。这辆老式的四座马车很宽敞,他坐在角落里,腿搁在对面座位上,陷人了沉思。他模糊地意识到巳经清理好了自己的账务,模糊地回想起赛普克霍夫斯基对他的友谊,还夸赞他是个有用的人才,尤其是对眼前的幽会满腔期待这一切融合成了生命无限欢乐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把腿放下来,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用手抱住,摸了摸自己昨天坠马时摔伤的结实的小腿,然后身子往后一仰,深深舒了好几口气。
“真高兴!太高兴了!”他想。以前他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有愉快的感觉,但从没像现在这样热爱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强健小腿上的轻微疼痛以及呼吸时胸肌的一起一伏,都使他感到很愉快。晴朗、微凉的八月天使安娜感到绝望无助,却使他觉得精神振奋、精力充沛,使他刚才擦洗得发热的脸和脖子感到十分清爽。他胡须上抹的润发油的香气在清新的空气中分外好闻。他从车窗向外望去,在薄暮的微光中,透过澄澈微凉的空气,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同他本人一样清新明朗、生气勃勃。落日余辉中闪亮的屋顶,栅栏和屋角的清晰轮廓,路上偶遇的行人与车马,静止不动的碧绿的青草与树木,垄沟齐整的马铃薯地,房屋、树木、灌木和马铃薯垄沟投下的斜影一切都令人愉快,好似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彩的风景画。
“快点,快点!”他从车窗探出身子,冲车夫喊道,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塞到回过头来的车夫手里。车夫摸索着什么东西,然后鞭子啪地一响,马车在碎石铺成的平坦大道上飞奔起来。
“除了这种幸福,我什么也不要。”他凝视着马车前窗间用象牙制成的圆形按铃,心想,满脑子都是上次见到安娜时她的模样。
“时间越长,我越爱她!这是弗雷德家乡村别墅的花园。她在哪儿?在哪儿?为什么?她为什么在贝特茜的信里约我到这儿见面?”他想,不过他巳经来不及思考了。马车还没驶进林荫道,他就吩咐车夫停车。车还没停稳,他就打开车门,跳了下来,向通往房子的林荫道走去。林荫道上一个人也没有,但一拐到右边,他就看见了她。她戴着面纱,但他喜悦的目光立刻捕捉到了她特有的步态、微倾的肩膀和头部的姿势,刹那间,仿佛有股电流传遍他的身体,从强健双腿富有弹性的动作到肺部的呼吸,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撩拨他的嘴唇。她走到他身边,紧紧抓住他的手。
“我让你上这儿来,你没生气吧?我非见到你不可。”她说。他一看到她面纱下嘴唇庄重、严肃的表情,心情立刻就变了。
“我怎么会生气?可你怎么来的?”
“这没关系!”她说,把手放在他胳膊上,“来吧,我得跟你谈谈。”
他感觉到出了什么事情,因此这次见面不可能太愉快。在她面前,他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他还不知道她为什么焦躁,就巳经受到感染。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他问,用胳膊肘紧紧夹着她的手,竭力读懂她的表情。
她默默走了几步来鼓足勇气,然后突然站住了。
“我昨天晚上没告诉你,”她说开了,呼吸急促而沉重,“我和阿列克斯·阿列克山德罗维其回家的路上,我把什么都告诉他了……我说我不能再做他的妻子……我什么都告诉他了。”
他听着,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仿佛竭力想减轻她的负担。但她一说完,他就直起了身子,脸上露出傲慢和严厉的神情。
“是的,是的,这样更好!好上一千倍!我理解这对你来说有多痛苦。”他说。但她没有听他说话,而是竭力从他脸上读懂他的思想。她猜不出他的表情说明他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一场决斗不可避免了。因此她从别的方面理解他那一瞬间的严厉表情。她读完丈夫的信件后,内心深处就十分清楚,一切都会保持原状,她不会有勇气不顾自己的处境,为了同情人结合而抛弃儿子。在贝特茜公爵夫人家度过的这个下午也证实了这种想法。不过这次见面对她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她希望这次见面能够改变她的处境,能够拯救她。如果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坚定而热烈地对她说:“放弃一切,跟我远走高飞!”那么她就会抛下儿子跟他离开。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对他产生她预期的影响,他看起来不过是受到什么冒犯一样。“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她恼火地说,“看看这个……”她从手套里抽出丈夫的信。
“我明白,我明白!”他打断她的话,接过信来,却没有读,竭力安慰她,“我只有一个愿望,此外别无所求,那就是打破这种局面,为你的幸福奉献我的一生。”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她说,“难道我会怀疑吗?要是我怀疑……”
“谁来了?”渥伦斯基指着两位朝他们走来的夫人说,“她们也许认得我们!”他赶紧拉着她走到旁边的一条小径上。
“哼,我才不在乎呢!”她说。她颤抖着嘴唇,眼睛带着异样的愤恨从面纱下望着他。“我说过了,问题不在这儿!这一点我不会怀疑,可你看看他给我写的信吧,看一看……”她又停下脚步。
像最初一刹那听到她向丈夫坦白的消息一样,渥伦斯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同受侮辱的丈夫的关系。此刻他手里拿着信,不由得想象今天晚上或明天他将收到的挑战书,想象着决斗的场面,那时他将面带此刻同样的冷漠傲慢神情站在那里,向空中开过一枪之后,等待受侮辱的丈夫的枪弹。此刻他脑海里闪过了赛普克霍夫斯基刚才对他说的话,以及自己今天早晨的念头(就是最好不要束缚自己冤,但他知道他不能把这些想法告诉她。
他读完信后,抬眼看她,但他的神情并不坚定。她立刻就知道,他自己巳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知道无论他说什么,他都不会把内心全部的想法告诉她,知道她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这可不是她所期待的局面。
“你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颤声说,“他……”
“原谅我,我倒觉得很高兴!”渥伦斯基打断她的话。“看在上帝分上,听我把话说完,”他又说,露出恳求她允许他解释一番的神情,“我高兴是因为我知道事情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像他所想的那样维持原状。”
“为什么不可能?”安娜强忍着泪水说,显然不再重视他要说的话。她觉得她的命运巳经决定了。
渥伦斯基本想说,经过一场他认为不可避免的决斗之后,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但他却说了别的话。
“不可能继续下去了。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他。我希望……”他窘迫起来,涨红了脸,“你能允许我来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才说了个开头,她却不让他说完。
“我儿子呢?”她喊道,“你看到他信上写什么吗?他要我离开儿子,可我做不到,也不想那么做。”
“可看在上帝分上,哪种情况好些?是离开你的儿子,还是继续过这种屈辱的生活?”
“对谁来说是屈辱的?”
“对所有人,尤其是对你。”
“你说这是屈辱的!不要这样说,这种话对我没什么意义。”她颤声说。她不希望他现在说假话。她只剩下他的爱了,而且她也想去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一切就都变了。对我来说,天底下就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你的爱!如果我拥有它,我就觉得很高尚,很坚定,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是屈辱的。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很自豪,因为……我自豪的是……自豪的是……”她说不出她自豪的是什么。羞耻和绝望的泪水哽住了她。她停下脚步,失声痛哭。他也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生平第一次觉得想哭。他无法解释是什么打动了他,他替她感到难过,却又觉得无法帮助她,因为他知道是他给她造成了麻烦,是他做了错事。
“为什么不可能离婚?”他有气无力地问。她默默地摇了摇头。“难道不能带上你的儿子离开吗?”
“可以,但这全都取决于他。现在我要回到他身边去了。”她冷冷地说。她认为一切都将维持原状的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星期二我要回彼得堡,然后一切都会解决的。好了,”她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事了。”先前被安娜打发走,现在又回到弗雷德家花园来接她的马车驶过来了。安娜辞别渥伦斯基,回家了。
星期一,“六月二日委员会”召开例会。卡列宁走进会议室,像往常一样问候过了主席和委员们,就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一只手按住他面前的文件。这些文件里有他需要的统计资料和一份他打算发表的声明的提纲。但他并不是真的需要这些资料。这些内容他全都烂熟于心,觉得根本没必要一遍遍在脑子里背诵。他知道,只要时间一到,只要一看见政敌在他面前徒然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他自然就会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比他预先准备的还要好。他觉得他的演讲内容那么重要,字字句句都举足轻重。不过,在听例行报告时,他还是露出一副天真质朴的神情。看见他那双青筋毕露的白净的手,修长纤细的手指抚弄着面前白纸的两边,脑袋疲惫地侧向一边,谁也不会想到从他嘴里滔滔不绝吐出的话将会引起轩然大波,使得委员们相互呵斥叫嚣,迫使主席不得不要求大家遵守秩序。听完报告后,卡列宁用他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向大会宣布,在异族人定居的问题上,他要发表几点意见。于是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他身上。卡列宁做演讲时有个习惯,就是不看他的政敌,而是盯着坐在他对面的第一个人,这会儿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在特别委员会里从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小老头儿,于是卡列宁盯住他,清了清嗓子,开始阐述他的意见。当他谈到基本组织法时,他的对手跳起来表示反对。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斯特里莫夫也被触怒了,开始同他辩论,大会上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辩。但卡列宁胜利了,他的提议通过了,成立了三个新的特别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的社交圈里人们就只谈论这次会议。卡列宁的成功超出了他的预期。
卡列宁星期二早上醒来时,回想起他头一天的胜利,感到很得意。他的秘书显然想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会议的传闻报告给他。卡列宁虽然想装出一副淡然处之的样子,却还是忍不住微笑了起来。
卡列宁同秘书忙个不停,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规定安娜回来的日子,当仆人进来通报她回来时,他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快。
安娜一大早回到了彼得堡。由于她事前打过电报让他派马车来接她,她想他应该等着她回来的。但她到家时,他并没有出来迎接她。仆人告诉她,他还没离开书房,正在同秘书办理公务。她吩咐仆人告诉丈夫她巳经回来了,就去了自己房间,开始整理东西,等着丈夫来见她。可一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来。她借口吩咐什么事情走进餐厅,故意大声说话,希望他会出来,但他还是没有过来找她,虽然她听见他把秘书送到了书房门口。她知道,依照他的习惯,他很快就要去上班,她想在他离开之前见到他。
她经过大厅,毅然向他书房走去。她进去时,他正坐在一张小桌子边上,胳膊肘支在桌上,疲惫地望着前方。他巳经穿好了官服,显然准备出门了。他还没看见她,她就先看见了他,知道他正在想她的事。
他看见她,想站起来,却又改变了主意,脸随即刷地一下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没见过的。
不过,他还是迅速地站起来,向她走来,不去看她的眼睛,而是盯着她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拉着她的手,请她坐下。
“我很高兴您回来了。”他说着,在她身边坐下。他显然想说点什么,却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好几次他想开口,却还是没出声。虽然她准备同他会面时,一再告诫自己要鄙视他,责备他,但现在她却不知说什么是好,不禁可怜起他来。两人好一阵都不吭声。
“谢里沙还好吗?”他问,没等她回答,他自己又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马上就要走了。”
“我本打算去莫斯科的。”
“哦,不,您回来做得很对。”他回答,然后就又不说话了。她看出他没有勇气开口,就替他先说了:
“阿列克斯·阿列克山德罗维其!”她没有在他紧盯她头发的目光中垂下眼帘,而是打量着他的脸说,“我是个有罪的女人,是个坏女人,但我和从前没两样,那天我就告诉过您的。我来是为了告诉您,我不会做任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