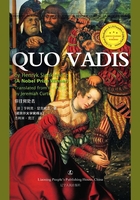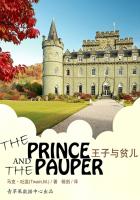“在俄国,永远都不可能!我们没有权力!”那地主回答。
“还能发现什么新条件呢?”斯维亚兹斯基喝完酸奶,点燃一支香烟,回到辩论者当中。“同劳动力的任何一种可能的关系都巳经研究过,并且确定下来了,”他说,“农奴制一瓦解,那些野蛮时代的残余互惠互利的原始公社就分崩离析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自由劳动的形式巳经确定了,我们必须采纳。雇工、短工、长工,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欧洲其他国家对这种体制并不满意。”
“是不满意,它们正在探求新形式。或许会发现的。”
“我只想说,”列文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探求呢?”
“因为这就好比发明建造铁路的新方法。方法巳经发明出来了,都是现成的。”
“可要是那些方法不适合我们呢?要是那些方法很拙劣呢?”
列文又从斯维亚兹斯基眼睛里看到那种惊慌的神色。
“是啊,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院我们巳经发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东西!这种话我听多了。对不起,您知道在劳动力方面欧洲有哪些建树吗?”
“不太清楚。”
“这个问题目前欧洲最优秀的人物正在研究。舒尔茨·德里奇派……思想最自由的拉萨尔派,论劳工问题的大量着作……穆尔豪森制度……这都是事实,我想您应该知道吧。”
“我有所了解,但不太清楚。”
“哦,您只是这么说罢了,我相信您知道的不会比我少!当然了,我不是什么社会学教授,不过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要是您也有兴趣,您可以研究一番。”
“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地主站起来了,斯维亚兹斯基又一次制止了列文窥探他内心秘密的讨厌习惯,走出去送客人。
当天晚上,列文同女士们待在一起感到百无聊赖。他一想到最近对农业活动感到不满并非他个人的想法,而是俄国农业的普遍状况,一想到使劳动者像途中遇到的老农家的雇工一样对待劳动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就觉得分外激动。他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应该尝试去解决。
列文同女士们道过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一天,陪她们骑马去国有森林看一个有趣的大坑。就寝前,他走到主人书房,去借几本斯维亚兹斯基推荐给他的关于劳动力问题的书。斯维亚兹斯基的书房非常大,四壁都是书橱。书房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巨大的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中间有一盏台灯,各种语言的报纸和杂志像垫子一样摊在四周。写字台旁边还有一个装满各种商业报纸的柜子,柜子的抽屉上都贴着金字标签。
斯维亚兹斯基把书取下来,在摇椅上坐下。
“您在找什么?”他问站在圆桌边翻阅杂志的列文。
“哦,那里面有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又说。他指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杂志。“原来瓜分波兰的主要人物不是弗雷德里克,”他兴致勃勃地说,“原来……”
他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简要叙述了这个重大而有趣的新发现。虽然目前列文对农业问题最感兴趣,但他听主人说话时,不禁问自己:“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他对瓜分波兰这么感兴趣?到底为什么?”斯维亚兹斯基说完之后,列文忍不住问道:“那又怎么样?”但斯维亚兹斯基并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原来……”,至于他为什么会感兴趣,他觉得不必解释。
“是的,我对那个爱动怒的老地主很感兴趣,”列文叹了口气,说,“他很聪明,他说的很多话都是事实。”
“啐!他背地里是个冥顽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他们全都是!”斯维亚兹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往相反的方向领。”斯维亚兹斯基哈哈大笑,说。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他说我们用合理方法经营农业没有收益,唯一能赚钱的办法,就是像那位文静的地主那样放高利贷,或者用最基本的方法来经营……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错!但说它没有收益是不对的。瓦西尔契科夫就赚到钱了。”
“工厂……”
“我还是不理解您有什么好奇怪的。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水平太低了,他们肯定会反对原本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在欧洲,合理经营农业会有收益,那是因为农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怎样教育他们呢?”
“教育农民需要三件东西:学校,学校,还是学校!”
“可您自己说过了,农民物质水平很低,学校又有什么用?”
“您知道吧,您使我想起了一个劝告病人的故事:‘您应该用点泻药。’‘我用过了,更糟糕。’‘试试水蛭。’‘试过了,更差劲。’‘那你只好向上帝祷告了。’‘祷告过了,更要命。’我们也是如此。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糟糕;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差劲;我说教育,您说更要叩。
“可学校有什么用呢?”
“能满足农民的其他需要。”
“我实在是不明白,”列文激动地说,“学校怎么能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呢?您说学校和教育能满足他们的新需要。这样反倒更糟,因为他们这些需要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我真的想不通,他们学会加减乘除和掌握教义问答怎么能帮助他们提高物质条件!前天晚上,我遇到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我问她上哪儿去,她说,她要去见巫婆,因为她儿子爱哭闹,她带他去治一治。我问她巫婆怎么治这种病,她说‘她把孩子放在鸡棚上,然后念咒语’。冶“哈,这就是您的答案!教育就会让他们不再把孩子放到鸡棚上去治病。”斯维亚兹斯基快活地笑着说。
“哦,根本不是!”列文不高兴地说,“我是用这种治疗办法来比喻用学校治疗农民。农民贫困无知,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就像那个妇女看到孩子老是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学校怎样治疗贫穷无知,就像鸡棚治疗孩子的哭闹病一样,叫人实在难以理解。他们需要治疗的是贫穷。”
“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同您很不喜欢的斯宾塞观点一致。他也说,教育或许是生活幸福舒适的结果,按他的说法,就是经常沐浴的结果,而不是会读书会算数的结果……”
“啊,我很高兴,或者说很遗憾同斯宾塞不谋而合。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那时自然就有学校了。”
“现在全欧洲的学校都实行义务教育。”
“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会同斯宾塞如此一致呢?”
斯维亚兹斯基眼睛里又闪过一丝惊慌的神色,然后他微笑着说:
“治疗哭闹病的故事太妙了!真的是您自己听说的吗?”
列文看出来,他不可能找到这个人的生活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显然,无论他的论证导向什么结论,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他需要的只是这个过程。要是他的论证把他引进了一条死胡同,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这样,避免出现这种情形,竭力把话题转向愉快有趣的事情上去。
这一天的所有印象,从途经的那个农家开始(这是他一天中所有印象和思想的基础)都使列文激动不巳。这位亲切和蔼的斯维亚兹斯基之所以对事物持有观点,仅仅是出于社会需求,他显然还有一些不为列文所知的生活原则,他同老百姓在一起的时候,会运用那些与自己格格不人的思想来指导舆论;那位一肚子怨气的地主对自己的苦恼生活发表的议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对整个阶级、全俄国最优秀的阶级表示怨愤却不太应该;列文对自己的活动感到不满,他模模糊糊地希望能找到所有问题的解决方式。所有这一切,都融汇成了一种躁动不安、渴望迅速解决问题的心情。
列文独自待在给他安排的房间里,躺在一抬腿或一伸胳膊就会忽然弹起来的弹簧床垫上,好久都没睡着。他对自己同斯维亚兹斯基的谈话没有一点兴趣,虽然后者说了很多聪明话;但那地主的意见却值得考虑。列文不由自主回忆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在脑海里纠正着自己的回答。
“我应该对他说院‘您说我们的农业不兴旺是因为农民痛恨一切改良,因此要改良就必须强制实施。要是不改良农业就毫无收益,那么您的话就是对的。可只要我们让劳动者按照自己的习惯劳动,就像我路上遇到的那个农民一样,还是能搞好农业的。您和我们一样,都对农业现状感到不满,这说明错在我们,而不在农民。我们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欧洲的方式)经营,没有考虑劳动力的特性。我们不要把劳动力看成抽象的劳动力,而要看成有独特天性的俄国农民,然后根据他们的天性来安排农事。”我还应当对他说:“您想想看吧!要是您像那位老农那样经营农场,想办法使雇工们关心收成,并且找到他们认可的改良方法,那么,土地就不会变得贫瘠,收成也可以增加一到两倍。您把收成平分,一半分给劳动者,这样,你得到的那一半多起来了,劳动者得到的也更多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降低耕作水平,使农民关心收成。怎样做到这一点,还是个需要详细考虑的问题,不过肯定是能办到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十分兴奋。他直到半夜都没睡着,仔细思考如何把想法付诸实施。他本来不打算第二天走,但现在却决定一大早就离开。何况,这位穿敞胸连衣裙的小姨子使他产生了一种近乎做了坏事而感到羞耻和悔恨的心情。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赶在越冬作物播种之前提出新方案,这样就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他决心彻底改变他以前的农业经营方式。
列文实施计划遇到很多困难。他竭心尽力实现目标,虽然结果并不如意,但他至少相信这件事值得努力。最主要的困难是农事正在进行,不可能让它停下来重新开始,只能在运转中调整这架机器。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把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显然很高兴地赞同他的一部分意见,也就是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的、无利可图的。管家说自己向来都是这么说的,可列文却不听他的。至于列文提议他以股东身份同农民一起参与农场经营,管家却只摆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没有发表任何明确意见,然后就立刻说起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运走和派人去耕第二遍地的事。因此列文认为现在还不到考虑这一计划的时候。
列文同农民谈到按新的条件把土地租给他们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们白天忙于农活,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项新计划的利弊。
牧牛人伊万是个天真的农民,似乎完全理解列文让他全家分享饲养场利润的提议,完全赞同这项计划。然而,当列文向他说明他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时,伊万脸上却露出了焦急和歉疚的表情,表示不能再听下去了。他似乎突然想到几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又是抓起干草叉把干草从牲口棚里叉出来,又是去提水,又是去清除厩肥。
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们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尽可能掠夺他们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他们坚信,不论他说什么,他的真实目的总是隐藏起来,不会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呢,发表意见时会说很多话,却从来不会说出真正的想法。此外,列文觉得那位爱发脾气的地主说得对,农民在签定任何契约时,不可变更的首要条件就是,不能强迫他们使用任何新的耕作方法或新式农具。他们承认英式犁耕地耕得更好,松土器耕得更快,但他们会找出上千条理由来说明他们为什么不使用这两种工具。虽然列文确信必须降低农业水平,但他还是不愿放弃那些显然有益的改良方式。不过,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他的计划开始实施了,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起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按新的合作条款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他很快看出这是行不通的,于是决定把农场分成几部分。饲养场、果园、菜园、草场和分成几块的庄稼地,应当分别进行管理。在列文看来,单纯的伊万最理解这项计划,由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家人组成的合作社,参与饲养场的经营。远处有片荒了八年的耕地,在聪明的木匠西尔多·雷祖诺夫帮助下,由六户人家按照新的合作条款负责耕种。农民舒拉耶夫按照类似条款租下了菜园。其他产业还是照常经营,但这三个部分是新秩序的开端,列文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这上面。
事实上,饲养场的经营状况并没有一点好转,伊万强烈反对给牛棚保暖和用新鲜乳酪做黄油,坚持认为奶牛养在冷的地方可以少吃饲料,用酸乳酪制成的黄油存放时间更长。而且,他还希望像从前一样给他发工资,对于他领到的并不是工资,而是预付的一部分利润,他丝毫不感兴趣。
事实上,西尔多·雷祖诺夫的合作社借口没有时间,没有按契约规定用英式犁耕两遍地。这个社的农民虽然答应按照新的条件耕种,却并不认为土地是集体共有的,依旧把它当成收益对半分成的租地。合作社成员和西尔多·雷祖诺夫本人都对列文说:“要是您只收收地租,您就会省心得多,我们也自由得多。”此外,这些农民找了种种借口,把契约上规定的修建牲口棚和谷仓的事一味拖延下去,一直拖到了冬天。
事实上,舒拉耶夫把租来的菜园分成小块转租给了其他农民。他显然曲解了、而且是有意曲解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
事实上,列文同农民谈话,向他们解释这项计划的好处时,感觉到他们不过听听他说话的声音,心里却打定主意,不管他说什么,都绝不上当受骗。这一点,他同他们当中最聪明的雷祖诺夫交谈时感触最深,他的眼神明显流露出对列文的嘲笑,表现出一种坚定的信心:即使有人上当受骗,那也绝不是他雷祖诺夫。
尽管如此,列文还是认为事情有进展,只要进行严格的核算,坚持自己的方向,他总能向农民证明这些新计划的好处,然后一切就会自然而然推行下去了。
这些事情,加上手头上的其他农务,还有他的室内写作,足足使列文忙活了一个夏天,忙得他连打猎都没有时间。八月底,他听那个把女式马鞍取回来的仆人说,奥伯朗斯基一家回莫斯科去了。他觉得由于自己没有回复多莉的来信(他一想起这个无礼行为就会脸红冤,他巳经破釜沉舟,再也不能去拜访他们了。他在斯维亚兹斯基家不辞而别,行为也同样恶劣。不过他也不会再去拜访他们了。现在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对农场的新安排比任何事情都更吸引他,从来没有哪件事情这样吸引过他。他通读了斯维亚兹斯基借给他的书,又订购了所需要的其他各种书籍。他还阅读了有关这一方面的政治经济学着作和社会主义着作,但正如他所料,没有找到任何与他事业有关的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着作中(譬如说他最早热衷于研究穆勒),时刻希望能找到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发现了从欧洲农业管理中推导出来的种种规律冤,但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在俄国行不通的规律会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专着的情况也是如此:不是他大学时代一度非常着迷的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就是与俄国农业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欧洲现存秩序的改良或补充。政治经济学断言,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规律毋庸置疑具有普遍意义。社会主义学说则宣称按照这种规律发展只有死路一条。但无论哪种学说都没有稍加暗示,列文和拥有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亩土地的俄国农民和地主应当做些什么来提高生产力,促进公共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