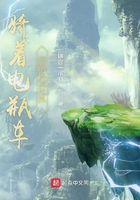“任命玛丽·波丽索夫娜伯爵夫人为陆军部部长,瓦特·科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为陆军参谋长如何?”一位穿着绣着金边的制服、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这样回答一位又高又漂亮的宫廷女官关于晋级事宜的提问。
“那我就当副官好了。”宫廷女官笑嘻嘻地回答。
“您的职位巳经安排好了,去掌管教会部门,卡列宁做您的助手。”
“您好,公爵!”老头儿同一个走过来的人握了握手,说。
“你们在说卡列宁什么呢?”公爵问。
“说他和普提亚托夫获得了亚历山大·那夫斯基勋章。”
“我还以为他原来就得过了呢。”
“不,您看看他。”老头儿用他的金边帽指了指穿着宫廷制服,胸前挂着一条崭新的红绶带,正同一位议会要员站在门口的卡列宁说。“正志得意满呢。”他又说,停下来同一位体格健硕、仪表堂堂的宫廷侍从握手。
“不,他老了。”宫廷侍从说。
“操劳过度。他现在老是起草计划。他不把所有细节问题说清楚,是不会放那个倒霉的家伙走的。”
“他老?真是的!人家还在谈恋爱呢!我想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正嫉妒他的妻子呢。”
“得了吧!别说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坏话了。”
“她爱上卡列宁有什么不好·”
“他妻子在这里,是真的吗?”
“当然不在宫廷了,可她在彼得堡。我看到她和渥伦斯基在莫斯卡亚大街上手挽手散步呢。”
“这种人没有……”宫廷侍卫话没说完就打住了,给一位皇室成员鞠躬、让路。
他们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议论卡列宁,贬斥他,取笑他,而他正拦住那位议会要员的路,硬要人家听他一点一点详细阐述他的财经计划,一秒钟都不歇气地说着,生怕人家溜走。
几乎就在妻子离开卡列宁的同时,官场中人最感痛苦的事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的升迁之路断了。这巳是既成事实,人人都看得分明,但卡列宁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仕途巳经走到了头。不知道是因为他同斯特里莫夫的冲突,还是因为他同妻子之间的不幸,抑或只是由于他在官场巳经到了命定的极限不管怎么样,今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的仕途完结了。尽管他还身居要职,担任许多委员会的委员,但他巳经没有前途,不能再对他抱什么希望了。不管他说什么,提什么建议,大家都觉得是老生常谈,没人愿听。但卡列宁对此浑然不觉,相反,正因为他现在不直接参与政府工作,他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别人的过错和谬误,并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如何修正这些谬误。同妻子分居不久,他就着手写一本关于新的法律程序的小册子他注定要写的无数本关于行政部门工作的、谁也不需要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但卡列宁根本没察觉到他在官场中的绝境,他非但没受到一点困扰,反而对工作比以前更满意了。
“娶了妻子的,挂虑的是世俗的事,想怎样取悦妻子;没有娶妻的,挂虑的是主的事,想怎样叫主喜悦。”使徒保罗如是说。如今卡列宁事事遵循叶圣经》教导,常常会想起这段话。他觉得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通过这些计划草案来更好地侍奉上帝。
议员明摆着的不耐烦神气并没使卡列宁感到不安,直到议员利用一位皇族经过的机会溜走,他才停止他对计划的冗长说明。
就剩卡列宁一个人了,他垂下头,定了定神,然后漫不经心朝门口望了一眼,希望在那里见到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他们个个身体多么强健啊。”他打量着那个胡子梳得整整齐齐、散发着香气、身材壮硕的宫廷侍从,还有那位穿着紧身制服的公爵红红的脖子,心想。他必须从他们身边经过。“世上一切皆是罪恶,这话真没说错。”他用眼角的余光又瞥了一眼那位宫廷侍卫的小腿,心想。
卡列宁带着一贯的疲惫和威严神情,从容不迫地走过去,向这群议论他的先生鞠了一躬,然后望着门口,寻找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
“啊,阿列克斯·阿列克山德罗维其!”当卡列宁从老头儿身边经过,冷冷对他点了点头时,老头儿目露凶光,大声说道。“我还没向您道贺呢。”他指了指卡列宁的新绶带说。
“谢谢。”卡列宁说。“今天天气可真好啊。”他又说,照例特别强调这个“好”字。
他知道他们在嘲笑他,但除了敌意他并不指望在他们身上还能得到什么。他巳经习以为常了。
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走进门来。卡列宁一看见她从紧身衣里裸露出来的黄色肩膀和她那双召唤着他的梦幻般的美丽眼睛,就露出洁白无瑕的牙齿微笑起来,向她走过去。
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今天的着装煞费了一番苦心,最近她总是精心打扮自己。她现在打扮的目的同她三十年前截然相反。那时她希望自己打扮得越漂亮越好,现在恰恰相反,要是她过分修饰的话,就会与她的年龄和身材不相称,所以她关心的只是不让她的修饰和外表反差太大。对卡列宁而言,她达到了这个目的,他觉得她很有魅力。在他眼中,她是包围着他的敌意与嘲笑的汪洋大海中唯一的孤岛,一座不仅对他友好而且满怀爱意的孤岛。
此刻他穿过那些芒剌般的嘲讽目光,像植物向着太阳一样,自然而然地被她含情脉脉的目光吸引过去。
“祝贺您。”她用眼睛示意他的绶带,说。
他忍住满意的微笑,耸耸肩膀,闭上了眼睛,仿佛在说他并不觉得有什么高兴。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非常了解这是他人生一大乐事,虽然他自己从来不肯承认。
“我们的小天使还好吗?”她问,指的是谢里沙。
“我不能说对他十分满意,”卡列宁睁开眼睛,扬了扬眉毛,说,“西特尼可夫对他也不太满意。”西特尼可夫是谢里沙的家庭教师,负责对他进行普通教育。“我告诉过您,他对那些本该使每个大人和小孩激动不巳的最重要的问题无动于衷。”他接着谈起了他公务之外唯一感兴趣的话题对儿子的教育。
他在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帮助下恢复正常的生活和活动之后,觉得有责任担负起儿子的教育重任。他以前从未关心过教育问题,现在花了一些时间研究教育理论。他读了几本人类学、教育学和教育法的书,制订了一个教育计划,还请来彼得堡最优秀的教育家进行指导,然后着手工作。他最近就总在忙这事儿。
“是啊,可他的心呢!我看出他有他父亲一样的心肠,有这样心肠的孩子是不可能坏的。”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热情地说。
“也许吧。不过对我来说,我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责任了。”
“您能上我家来吗?”伯爵夫人沉默片刻,说,“我们得谈一件会使您觉得痛苦的事。我愿想尽一切办法使您摆脱那些不愉快的回忆,但别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收到她一封信。她就在彼得堡。”
卡列宁一听她提起妻子就打了个寒噤,脸上立刻露出死人般僵硬的神色,表示他对这类事情完全束手无策。
“我早料到了。”他说。
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心醉神迷地望着他,对他高尚的灵魂钦佩得热泪盈眶。
卡列宁走进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间摆满古代瓷器、挂满画像的舒适的小会客室时,女主人还没到。
她在换衣服。
铺着桌布的圆桌上,摆放着一套中国茶具和一只架在酒精灯上的银壶。卡列宁心不在焉地打量着装饰会客室的无数幅熟悉的画像,坐到桌边,翻开桌上的叶圣经》。伯爵夫人丝绸裙子的声惊动了他。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了,”她带着兴奋的笑容,挤到桌子和沙发中间说,“一边喝茶一边聊吧。”
伯爵夫人说了几句开场白,然后就喘着粗气,满面通红地把她收到的信递给他。
卡列宁读着信,好半天沉默不语。
“我认为我无权拒绝。”他抬起眼睛,怯生生地说。
“我亲爱的朋友,您在任何人身上都看不到罪恶!”
“恰恰相反,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罪恶。但这样做对吗?”
他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希望在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上得到建议、支持和指引。
“不。”她打断他的话。“凡事都要有个限度!我懂得什么叫伤风败俗,”她这话说得并不实在,因为她从来都不理解女人为什么会伤风败俗,“但我不懂得冷酷无情……而且是对谁呢?对您!她怎么能待在您所在的城市?‘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真没说错!我正在学习了解您的崇高和她的卑鄙。”
“可谁愿意投掷石块呢?”他说,显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满意,“我彻底原谅了她,因此无法拒绝她出于对儿子的爱提出的要求。”
“但我亲爱的朋友,这算得上爱吗?这是出于真心吗?假使您过去宽恕她,现在依然宽恕她,可我们有权这样对待小天使的灵魂吗?他认为她巳经死了。他为她祈祷,求上帝宽恕她的罪过,这样还好一些。可……他会怎么想啊?”
“我没想到这一点。”卡列宁显然同意她的看法。
伯爵夫人用手捂着脸,不说一句话。她在祈祷。
“如果您征求我的意见,”她祈祷完,把手从脸上放下来,说,“我求您不要这么做!难道我看不出来您多么痛苦,看不出这件事又揭开了您的全部伤疤吗?当然了,您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考虑自己。可这会有什么后果呢?您又会觉得痛苦,孩子也跟着痛苦!要是她身上还有一点人性,她就不该想这种事。不,我劝您不要犹豫,拒绝她的要求。要是您允许的话,我这就给她写信冶口。
卡列宁答应了,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就写了下面这封法文信:
亲爱的夫人:
如果让您的儿子想起您,他势必会提出种种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向他的心灵灌输一种精神,使他谴责他原本视为神圣的东西。因此,我请求您本着基督爱的精神体谅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全能的上帝宽恕您。
丽迪亚伯爵夫人这封信达到了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隐秘目的。它伤透了安娜的心。
卡列宁呢,从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回来之后,就没办法处理他的日常事务,也找不到他以前所体会到的灵魂得救的信徒应有的内心平静。
妻子这样对不起他,可他正如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那句公道话所说的,对妻子就像圣人一样,因此他想到妻子不应当有什么难过。但他就是烦躁不安,看书看不进去,一想起他同她的关系,想起他现在才感觉到的他对她做过的错事,便无法摆脱那些痛苦记忆。他想起从赛马场回来时,他怎样听她承认自己不忠(尤其是他只要求她对外保持体面,并不要求同渥伦斯基决斗冤,就好像懊悔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感到非常痛苦。他想起他写给她的信,也感到十分痛苦。尤其是想起他那谁也不需要的宽恕和对别人孩子的关爱,他就觉得羞辱难当,悔恨交集,似火焚心。
现在,当他回想起他同她的整个过去,回想起他百般鋳躇之后向她求婚时说出的那些难为情的话,他同样感到羞愧和懊悔。
“可我哪一点做错了呢?”他自言自语。这个问题照例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其他人,比如说渥伦斯基、奥伯朗斯基和那个小腿发达的宫廷侍卫,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会有什么不同吗?他脑海中浮现出一整排精力旺盛、身体强健、信心十足的人的形象,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吸引他的注意力与好奇心。他把这些念头驱逐出去,竭力使自己相信他活着不是为了短暂的现世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但他在这短暂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中犯下的无足轻重的错误,却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仿佛他所信仰的永恒救赎都不复存在了。不过,这样的诱惑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就恢复了平静和崇高的心境,并且藉此忘却了他不愿记起的事情。
“怎么样,卡皮托尼奇?”谢里沙在生日前一天散步回来,兴高采烈,脸色红扑扑的,他把外套递给那个俯身笑眯眯看着他的高个头老门房,说,“对了,今天那个扎着绷带的官员来过了吗?爸爸接见过他了吗?”
“接见过了。秘书一走,我就去禀报了,”门房眨着眼睛回答,“我来帮你脱吧。”
“谢里沙!”斯拉夫家庭教师站在通往里屋的门口,说,“自己脱!”谢里沙听到了家庭教师微弱的声音,却不理不睐。他拉住门房的肩带站着,仰望着他的脸。
“那么,爸爸答应了他的要求吗?”
门房肯定地点了点头。
扎着绷带的官员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来求见过卡列宁七次,引起了谢里沙和门房的兴趣。谢里沙在大厅里见过他,听到他可怜巴巴地求门房替他通报一声,说他和他的孩子都快饿死了。从那时起,谢里沙在大厅里又遇见那人一次,对他产生了兴趣。
“他很高兴吧?”他问。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走的时候高兴得都要跳起来了。”
“有人送过什么东西来吗?”谢里沙沉默片刻,问。
“哦,少爷,”门房摇摇头,轻声说,“伯爵夫人送了东西来。”
谢里沙立刻明白,门房说的是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给他送来了生日礼物。
“真的吗?在哪儿?”
“科尔尼拿进去给你父亲了。想必是样好东西。”
“多大?有这么大吗?”
“没那么大,不过是样好东西。”
“一本书?”
“不,是样东西。去吧,去吧!瓦西里·鲁卡奇在叫你了。”门房听到家庭教师走进的脚步声,说道。他对家庭教师点点头,使个眼色,轻轻拉开了那只抓着他肩带、手套脱了一半的小手。
“瓦西里·鲁卡奇,我马上就来!”谢里沙说,他快乐而温柔的笑容总能征服严谨勤勉的瓦西里·鲁卡奇。
谢里沙太高兴、太幸福了,不能不让他的朋友门房同他一起分享家里的另一件喜事,那是在夏花园里散步时听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侄女说的。这件喜事对他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它正好同那位扎绷带官员的喜事和他收到礼物这件乐事同时发生。谢里沙觉得,今天是个人人都应当快乐幸福的大好日子。
“你知道吗?爸爸得了亚历山大·那夫斯基勋章。”
“当然知道!大家都来道贺了。”
“怎么样,他高兴吗?”
“皇上的恩典,他怎么会不高兴呢?说明他有功劳。”门房一本正经地回答。
谢里沙沉思起来,凝视着他仔细研究过的门房的脸,尤其是那花白胡子下的下巴,别人看不见,只有总是仰视着他的谢里沙才能看到。
“你女儿最近来过吗?”
门房的女儿是一名芭蕾舞演员。
“她不到周末怎么可能过来呢?她们也要读书啊。你也得上课了,少爷!去吧!”
谢里沙走进用做教室的房间,没有坐下来听课,而是告诉家庭教师,他猜想送来的礼物是一辆火车。
“您觉得呢?”他问。
但瓦西里·鲁卡奇只想到谢里沙该预习语法了,他的语法教师两点钟就要过来。
“哦,您跟我说说吧,瓦西里·鲁卡奇!”谢里沙手里拿着一本书坐在桌子旁边,突然问,“什么勋章比亚历山大·那夫斯基勋章更高?爸爸得了亚历山大·那夫斯基勋章,您知道吗?”
瓦西里·鲁卡奇回答说,更高一级的是弗拉得米尔勋章。
“再高的呢?”
“最高的是圣·安德鲁勋章。”
“还有更高的吗?”
“我不知道。”
“连您也不知道呀!”谢里沙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沉思起来。
他的思绪五花八门、错综复杂。他想象父亲突然获得了弗拉得米尔勋章和圣·安德鲁勋章,这样的话,他今天来上课就会和气得多;想象自己长大以后也将获得所有勋章,而且那时人们还将设立比圣·安德鲁勋章级别更高的勋章,只要一设立出来,他就会得到;人们还会继续发明更高级的勋章,他也会立马就弄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