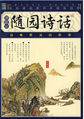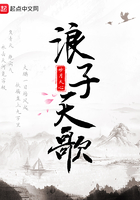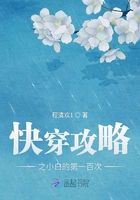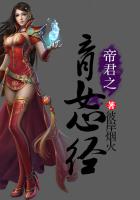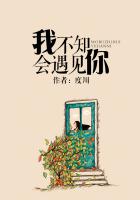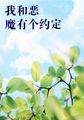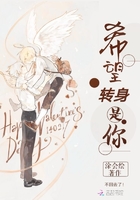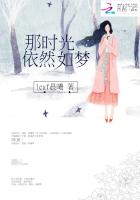洪子诚教授在著作《问题与方法》的中有曰:“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2011年7月,我到北京大学学习,亲沐洪子诚教授、李杨教授、陈晓明教授、黄子平教授,贺桂梅、邵燕君副教授以及人民大学孙民乐教授,中国社科院白晔研究员等名家教泽。学习期间与众位教授多方交流,结合我对所讲内容的理解及他们著作中有关对于人文学者困惑的观点,做一综述。
一、关于学人的自我认知问题与思考
对于学人的自我认知思考,我一直以来就存在困惑。同样是在搞学术研究,只因研究的领域不同,研究者的处境会千差万别。尽管一个院所有一个院所的个性特色,但无论怎么强调公平公正,我还是认为文学研究是无法与经济、能源研究相提并论的。原因有三:其一,我们所处在当下这样一个拜金时代,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几乎是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研究能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属有意义和有价值。而经济研究或能源开发是创造经济效益最直接手段,因而会成为评判研究者意义与价值存在的标杆。其二,重视经济信息资源和能源开发是时代的最强音,因此搞经济或能源研究有话语权,有经费,有前途,干劲大。其三,经济效益最直观,不仅使人民立刻得到实惠,就是政府官员也可功德在谱,升迁有望,自然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和特别关照,研究的环境与空间拓展,成为研究者不必为此担忧费思的前提,一门心思把好研究课题的质量水平关便是。介于这样一种现状,搞文学研究的学者就没有那么幸运,尽管精神文明建设是强国发展中的“另一条腿”(******语),但实际上却是一条隐形腿,研究的实效性弱,即使是紧贴时代脉搏,紧随时代律动,也收效的是基础理论性效应。因此,少有关注的目光和投资,研究费用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研究者会对自己的研究价值产生怀疑,对自身认知产生困惑。特别是文学研究的边缘化,让从业者无论怎样努力也走不上话语权的前台,从我们每年的科研经费的分配比例就可以看出,********的不仅仅只是基础理论学科,最明显的还是审批过程的艰难。
洪子诚:人文学科是渗透着权力和价值在里边的,研究时一定要抑制这种冲动,否则无法评介出作品与作家的好坏优劣,也无法对研究成果作出正确判断。就拿我这次给你们上课的内容: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定位问题来说,面对当代文学史的批评责难和创作,文学研究困境和现状,我认为“研究者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反省自己的认识能力”。比如搞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严格划分当然不可能,不过也要承认有所区别。文学批评或者说现状研究,要注重文本的分析、评价、阐释,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多的“静态”分析的特点。而文学史自然也离不开文本批评,但它是回顾性的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关于这点就有研究者说:文学史研究是研究者关于文学回忆的整理。这个“回忆”自然不仅是个人性的,也不是经验性的。它还要关注作品产生的一系列条件,比如作者的情况,社会环境,社会机制的制约,文学传统如文类、写作方法、题材等的演变以及国别文学之间的关系等。你要是对这样的说法没有一个很好的自我认知能力,怕是无法担当文学史的著述。还有,对目前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有人指出:几乎都不能读,大多是“垃圾”。这当然也包括我过去参与编写的文学史。这话听起来很受刺激,让我们这些长期做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人伤心,有的甚至还感到愤怒,是重大打击。这种说法虽然过于偏激,但当代文学史写作在这二十多年中,确实问题不少,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大概也不为过。尽管我们很努力,有更新观念和方法、改革编写体例上的努力,使90年代出版的多部文学史各具特色,比如:刘锡庆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除文学思潮外,以文学体裁区分,注重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於可训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略》评述扼要简洁,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赵俊贤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综史》以作家的“文学观”,作品的“文学形态”,文学运动的“思潮模式”的发展,作为描述角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集体编著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篇》除大陆外,也包括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等等,各有千秋。但并不说明就没有问题,比如对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普遍存在怀疑,一是即使通过主编统稿,各部分在观点和评述方法上也还是显得不平衡。二是可能会出现一种强烈的“国史馆”的权威意识。集体写作有点像过去的“翰林院”,因此入选的作家作品会很注意方方面面的“关系”、“官职”,比如不说周扬担任作协副主席、******副部长,能认识周扬在当代的活动吗?不谈袁水拍是如何一步步上升到“****”期间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能看清楚一个诗人的“命运”吗?这些身份的处理方法,会让人觉得它是作家成就的重要标志。这里边存在的问题,作为文学史“编委”的我,当然是有责任的。
“自省”自然是学人的可贵品质,但光有自省没有“自主性”自然是徒劳。我想洪先生这种自省是建立在具有极高权威意义上的。像我们这些普通研究者,人微言轻,再具有自省意识也很难改变一种处境。
洪子诚:“当代文学”在现在的学科体制中,有普遍被看作是“没有学问”的。可是严家炎、谢冕这些名家大家不都是从事这个行业吗?我大学一毕业就留校教书,而且教的就是“写作课”。当时和同是北大毕业高我一级(1955级)的黄修已先生同住一个房间,记得我去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从19楼到一教的路上,全身发抖,紧张得要命。但黄修已却一开始就胸有成竹,神情自若。他备课用的是红格竖行的稿纸,这种纸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用毛笔写,每两堂课写六千多字的讲稿。我当时很纳闷,六千多字我一堂课都不够讲。这就是水平的高低。再说,在北大教书,我也是从见习助教,到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一步一步“爬”上去的。在生活上,从住筒子楼,在楼道里烟熏火燎做饭,到按工龄、年龄、学历的计分方法排队住进二居室,再排队住进三居室。等搬进了三居室,也终于熬成了教授,这个时候也就两鬓斑白,同时也就到了该办退休手续的时候了。当然,我们也用相似的模式“规范”不如我们资格老的人。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想试图超越这些限定,但成功总是很少,失败的居多。即使是成功的“超越”,也可能是进入另一种限定罢了。就像乐黛云老师曾经说过的那样,所谓个体的“自主性”其实是脆弱的,我们是生活在“他人引导”的世界中。有时看起来很“自主”的决定、路向,都要受到社会环境、学术体制的严格制约。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所走的路子,有多大程度是“自主选择”的呢?其实“自主性是一个被映照出来的面具”。
二、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意义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兴起,是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反思联系在一起的。90年代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接受,在国家社会科学的学术管理体系中,也获得了它具有独立学科的身份和地位。没有人怀疑它的兴起,是在为我们中国文学展现又一个特殊的汉语文学空间,并直接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华人作家从地域转移到生命移植,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他们身处异域文化的特殊身份,让他们笔下的思考多了几分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审视,因此在考察他们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时,文化因素自然成为研究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对扩大文学理论、方法及版图与疆界都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读了贺桂梅教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一书,从一种更具有想像力的整体历史视野揭示出80年代中文化时间的不同层面,及其与90年代以来“全球化”现实之间的联系,我想贺老师对学术界台、港、澳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热研,是否也和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有关,从文化角度考察文学有哪些意义?
贺桂梅:如果从90年代已经规范化的学科体制角度看去,固然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打通”是某种跨越学科领域(或学科方向)的实践。不过就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处境来看,这种越界行为却更是某种学科、知识重组的表征。也就是伴随着历史转型,而对学科建制和知识体系所进行的重组。这里或许包涵着两个方向和两个层面的作用力。一是具体学科方向内部的压力,即一种强烈的渴望打破学科界限的诉求。(这种说法我表示赞同。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在发现社会主义文学之外还存在一个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学空间,强烈渴望这种与大陆文学不同的文学书写,能够在为人们打开一扇了解海外的窗口的同时,让它的审美范式也能为广大读者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与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而另一方面的作用力,则来自于知识界某种正在成型中的广泛的新共识。王晓明曾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20世纪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强烈共鸣:“各种各样的新的学术思想,就好像是早春时候江中的暖流,在冰层下面到处冲撞,只要有谁率先融塌一个缺口,四近的暖流就都会集聚过来,迅速地分割和吞没周围的冰层。”
这两方面的作用力似乎是任何一种文化变革必然会有的,但具体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来说,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质疑当时支撑着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主流知识体系,那种强烈的“破关”意识本身已经宣告了这一知识体系的失效,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以怎样的语言来表达新的共识。也正是在后一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不是“用材料的丰富”“补就理论的困乏”,而是“换剧本”的问题(黄子平语)。也不是讨论一个文学史分期的问题……而是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问题(陈平原语),是从“旧概念”到“新概念”的“飞跃”(钱理群语)。这也就是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不在“破旧”而在“立新”。这种讲述方式在当时人文知识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只能理解为整个学术界、文化界都在调整,我们因应了这种变化时代需要”即所谓“踩上点儿了”。如果我们采用某种后结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突破,就需要意识到,所谓“新”从来就不是说出早已存在的事实,而是“创造”出那些已经存在的事实的意义的过程。因此,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值得分析的首先是他们以怎样的叙述逻辑、知识结构和文化想象来讲述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也许就是文化调整之后对于文学研究带来的新意义。
三、关于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早些年在研究香港文学批评的时候就读过黄子平老师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文中一些观点,比如:“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等,不仅打开了大文学史观的思路,而且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崭新的风气,这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也是一剂不可多得的良药。事实上,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和其他学者一样都有一种特别感受,就是在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黄子平和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谈笑间的那种自信、自如甚至自豪的浪漫主义色彩。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黄先生又给我们讲文学史是“重铸灵魂史的灵魂”,是“把时间意识形态中的故事进行剪接”;文学史应该有边界“没有边界何来学科”、“文学史应该是一个博物馆,这样就可以出现一个入口,一个出口,没有排他性”等,依然激情未减,谈笑之中自有一般学者难能的达观与趣味。黄老师,这是否和您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有关?在学术界人们常常说:有独立思想的人都难逃痛苦的宿命,也许只有在终极信仰中找到心灵栖息地的少数人,才能达到内心的祥和。
黄子平:每一个人都有对于自己局限性的自觉,因为当代社会的发展会不时地摧毁自己的基础,搞不好社会都会处于失语状态,何况我们个人。严格意义上说我对当代文学产生兴趣,是从第四次文代会对作家的死亡名单的默哀开始的。它有震撼作用,灵魂的震撼,给了我生命的改变,生命意义的改变。但是对于写作我仍然心存顾忌。前段时间我发表过一篇《害怕写作》的书,讲的并不是纯粹技术上的问题,是关系到一种学者良心的建立和坚守。其实从杜甫甚至更早的文人开始就面对这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了。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涉及到一个文人安身立命和道德理想的永恒话题,作为学者我们希望“著作等身”,又希望名垂后世,然而名利双收毕竟有时只是一种幻象,当我们屈从于时代,热衷于作学术明星时,肯定会放弃很多与时尚相悖离的原则,而一旦远离这些,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就成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读了黄子平教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我发现作为一名普通学者,通常情况下并不能完全游离于学术体制之外,如何以研究或写作的方式表征自己,也不是一个可轻易解决的问题,关键要有对待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学术有为人生的学术,为人心的学术,即便是为“社会的”讲究“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反身性”原则。这是周宁教授的观点,也就是说即通过剖析自身而认识他人。如果一味地强调“实证”和“可操作性”,思想和精神就失去了自由驰骋的空间。我想既然无法游离于学术体制之外,要保持学术终极目标自然就很难,我们该如何去做?
黄子平:依我有限的观察,学术体制现状已然如此,很难改变。即使改变,也很少朝着好的方向。事实上,受现状损害最甚的还不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而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腐败,造假,资源浪费,对社会道德基础的侵蚀,新一轮******带来的失魂落魄……这些都多谈无益,徒增焦虑和忧苦。于是问题就回到我们自身,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如何在这“盛世”的边缘,持守人文学者的生命信念?答案么,也还是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最真诚地分析你之所见,写出你想写的文字,从而经由所谓“学术”,参与到这个活的世界中去。蔡元培当年从后门赶出去的两大玩意儿(“做官”、“发财”),如今大摇大摆,从前门回来了,而且冠冕堂皇,要超英、赶美、创一流。这些年都忙什么呢?争博士点,建基地,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长江学者,核心刊物论文数量排行榜,层出不穷。用李零的话说,四海无闲田,农夫皆忙死。可是地里不长庄稼,光长数字。有多少人会思考这些用来满足大势的追求,是否具有终极意义和永恒价值。尽管时间会给有生命力的艺术品以应有的报偿,时间不会原谅买椟还珠、错失良机的人,但用时间来交换某种利益和事物目标,就得有“牺牲”。高尚的牺牲与世俗的交换不同,它“高”就高在,为看不见的对象牺牲看得见的利益。何况“牺牲”通常有两种不同方式:壮丽的瞬间或漫长的痛苦,人们往往不能忍受后者,因为它需要有超人的执着态度和承受能力。
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大多在大陆出版的海外华文作品(如:新移民作品)的叙述模式、知识表述甚至是意识形态都没有脱离中国式,(也许我在改变纯文学研究的思路)这其中不排除有出版社选题的因素,但无疑阻碍了学术界对于台、港、澳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热研的质的升华。再者,不可能每个研究者都有海外实践的机会,那么如何打通某种跨学科领域的实践,也是摆在我们人文学者面前的实际问题。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对于华文文学的研究该如何寻找价值入口?
黄子平:我很少从“学科”的角度去读“世界华文文学”,更不清楚纳入国家学术管理体系后带来了怎样的新视野。你接触到的作品,正如你敏锐的观察,“叙述模式、知识表述甚至是意识形态都很难发现有质的飞跃”,“新移民”仍然活在“共和国话语”里,而且海外赤子的心总比海内更为拳拳。这倒未必是“出版社选题”过滤的结果,根本的还是与这些作者移民前后的人生遭逢相关。台港、马华文学的异质性就很明显了,他们基本上使用另一套语汇。当然,“母语”是另一片有“疆界”的“国土”,另一个“大唐人街”。“双语写作”的作家更有可能带来“新质”。探讨文学写作中母语的变异、混杂、移位,或许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可能“入口”之一。
聆听了北大几位老师的讲解和拜读了他们的著作,发现他们的共性特征都有圣贤般征服自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他们各自的睿智、学识、毅力、执着、谦和以及承受外界干扰的豁达和幽默。正如南怀瑾先生说的那样:“英雄征服天下,圣贤征服自己。”洪子诚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一种沉静的心态来从事文学史的研究,没有超常的思维定力是难以持久的。他的言行举止告诉我们,人文学者严于自省的品质,在这个盛行以金钱考衡、以狂傲为荣的时代风气里,尤为可贵。贺桂梅博士给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在跨越学科边界而能够整体性地回应当代社会与思想问题的能力。对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将其视为上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文本进行解构解剖,同时,借助对其知识表述及播散方式的追索,可以彰显支配文学审美表述的知识更新和权力机制的人性化力量。而黄子平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从1994年定居香港至今,也参与了香港的很多重要的文学活动,编选过香港的年度小说选刊,不管在北京还是在香港,黄先生都有许多“文学在场”的经验。希望有机会再续学缘,再次与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以提高自己文学研究的水平。
(注: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参考洪子诚著《问题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参考贺桂梅著《“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参考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