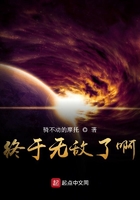终于忍不住又开了腔——也不知算不算又一个“无聊”问题:“那么,这些年,你就是靠这个——维生,生活的吗?”这字眼,太笨拙,太难选择。
“谈不上维生,消磨时间吧。”
“消磨时间?”我狐疑地望着他,
“真话?假话?”
“不真,却也不假。”他笑笑,徐徐说道,
“不真,在于平日说的消磨时间,是说时间在消磨你、我,消磨所有的人;可我这里说的是,我想去消磨那个——时间。”
“有点费解。这话——怎么说?”
他嘎嘎嘎的,有点恶作剧地大笑起来。
笑罢,重重喷出一口烟气,才缓缓说道:
“你记得温玛长老说过,那个中土古国,对时间有一套自己的认识尺度么?我深信,即便能展开深入的考古挖掘,恐怕也很难找到凶巴人对时间观念的实证性的记载了。这些年在荒沙野地里行走,这感觉是我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他吐着烟圈,看着烟气且浓且淡地在大气中消散,仿佛注视着他说的“时间”的消逝,慢悠悠说道,“依我现在看,时间的最大意义,就是它的无意义。不必要硬为这个被赋予了岁月年华呀、花开花落呀之类的意义而犯苦发愁、患得患失,以至于争斗倾轧,流血掉脑袋。我敢斗胆说:时间是万恶之源——或者更说得板上钉钉:对时间狭隘功利的理解,是万恶之源。你想想,人类犯的许多错误,根源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纳粹,比如‘文革’,比如冷战,比如我的‘203’或者‘302’之类,或者今天的现代化、市场化、唯流行消费为大之类,打打杀杀,追追赶赶,东闯西撞,为了什么?为了改变时间的轴线。——不,或者说,是驯服于一种古老而单向的时间轴线。要‘优生统治’呀,要‘只争朝夕’呀,要“成功成名”呀,要‘最大效率,最低消耗’呀,还要变着法子延长生命逃避衰老恐惧死亡呀!不就是想在那根有限的时间轴线上,尽可能变出更多的利益花样来吗?所以,想‘优’、想‘快’、想‘争’的一类人,就要打击被认为是‘劣’的、‘慢’的和‘不争’的一类人;而且认定该被打击的,就一定是坏的,处于道德劣势的,必须不择手段、千刀万剐的。为了以‘最低消耗’创造‘最高效率’,就要寻求‘最高能量’;可‘最高能量’所依仗的,反而必然就是造成地球老爷子的‘最大消耗’而不是‘最低消耗’!更不必说,寻来的那个‘最高能量’的极端——核弹氢弹之类,正是将造成人类自我毁灭的‘终极消耗’!如此这般,都可以怪罪于那个——‘时间’,那个老得出了筋、掉了毛的时间尺度!”
——好一套玄奥伟岸的高论!未免过于惊世骇俗,甚至不无矫情造作了吧?可是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有从米调那样一种角度,去想象过这个“时间尺度”的话题。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算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意义,还是新的无意义?这算是一种彻底的进取呢,还是彻底的颓废?是蔑视一切的规矩尺度,还是在遵循一种最严格、最苛刻、最清苦的规矩尺度?只有一点是我敢肯定的:这样一种出格的时间理念,恐怕真的是要置放在黄沙大漠的荒绝背景上,才会冒生出来的。每日每时,大漠就这样空落落、平展展摊在你眼前,没有起点,也没有尽头。傍在沉默的骆驼身边连日行走,我确曾这样想过,在这里,“有限”和“无限”都是没有意义的;而米调他们,确是在用自己的筋骨肉身,在消磨着这“有限”和“无限”。我忽然想起自己那晚野宿在沙漠上,仰看星空时所引发的遐想;还有这一路上,米调一再嘲笑过我的——“大汉人的世故”……
“你等等”。我打哳他,
“照你的意思,你究竟是要把生命的有限性看淡呢?还是要充分认识生命自身的有限性呢?”
他回答得毫不迟疑:“就别在有限、无限里犯酸了吧,那还不是在‘时间’的老套套里兜圈子?就这么简单地说吧,也不光是时间了,这年头,日子越过越复杂,人身上披挂的家伙越来越多,人的许多根源性的东西就越是乱了套了,迷失流走了。我想,只有把以往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那些东西统统看轻了、看淡了,人哪,才能活出一点他妈的新意思来。——我说清楚了么?”
“不,越说我越糊涂。”
我笑了,他也笑了。
“所以我叫——消磨时间。”他指着背后广袤的沙漠,“温玛长老给我的名字叫索罗卡拉,我想,就咱这么一架血肉凡躯,也不妨做一个面对另一种时间尺度的——索罗卡拉吧!”
落日,又耀起了那片虚幻的玫瑰色。
我心底的那个挑衅的欲望,又一次被隐隐点燃了。
我盯着他:“你是说,你是想把自己的一生,跟命运,或者跟上帝、跟一个什么万能的神明下一个赌注,把自己投入一场你想象的另一种时间尺度的实验里去,以求得一个什么答案,对么?”
“赌注?实验?你说得太伟大了。——没打算求什么答案,就这么活着吧。”
可是,没待我发难,冷不丁地,潘朵已经插进话来:“索罗,我能加入你们的谈话吗?”
原来潘朵一直侧耳旁听着我们的交谈。这一路来,她其实始终是最专注的聆听者。她用带口音的汉文说:“索罗,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总说,你再不会相信世间会有什么真神。可是,你不是把你说的温玛长老,当作你的真神了吗?你总是相信他告诉你的每一句话,难道你现在这样不顾一切去找那个北京女人,也是温玛长老要求你做的吗?”
我看着潘朵因为认真、也因为极力发音准确而显得吃力扭动的面容,笑着说:“潘朵,你问的,也正是我想问他的问题!”
米调笑笑,对我说:“这一向,潘朵对我没有像她一样的信从喇嘛教,意见大得很哩。”他转向潘朵,“我说潘朵,温玛长老并不是我的真神,但他是一个真人,一个有高智慧的人。我确实再也不相信人世间会有真神,可是我相信汉话里说的,一样米养百样人。人世间既有我这样的盲驴瞎马,就会有大智大慧的真人。温玛长老对于我,就是这样的真人。至于那个——北京女人,我相信,如果温玛长老在这里,他一定会要求我,无论如何找到她的。”
潘朵指着身边连绵起伏的沙岭,捻了捻她胸前的佛珠,提高声调说:“在这样连老鹰都不肯下蛋做窝的地方,索罗,你不信喇嘛菩萨,信什么呢?”
米调望望我,他显然觉察到,这大概也是我对他的疑问。“有时我自己也感到很迷糊。”他低下头,像是在自说白话,“我敬重温玛长老的地方,正是他身在佛门,却劝我不必遁入佛界空门,他认定神性的根源,首先要从人的根性里来。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具体宗教的信徒,可是又觉得,自己有信仰,至少是需要信仰。不过你要问我,这个信仰究竟是什么?我又说不明白。”
潘朵把头一扭,回身向后面跟来的黑皮和骆驼走了开去。
米调向我摊摊手,苦笑。
“不对吧?”我看着潘朵委屈的背影,终于被激怒起来,“米调,你不觉得这一切显得很虚妄么?什么‘消磨时间’,什么‘无宗教而有信仰’,”我把几天来积压在心头的悬疑一股脑儿全倾倒出来,“你不觉得你一直在欺骗自己,在故意回避,回避自己必须要真实面对的许多东西吗?”
“好好好,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大反攻又开始了。”
“——你别打岔。说白了吧,我甚至觉得,你的那个什么‘凶巴古国’,也许完全是你自己想象虚拟出来的!你的‘温玛长老’,你的‘索罗卡拉’,以至你要寻找的‘廖冰虹’,都是你给自己找的一种心理慰藉,都是你其实不敢真正面对的东西!我甚至难以想象,如果那位潘朵说的北京女人——廖冰虹,现在就果真出现在你面前,你,你会怎么样?!”
我知道这番话有点豁出去的味道,这也确实是我“蓄谋已久”的。可话说出口,却听不见回音。这时候,我们正歇息在一道沙梁上。回过身,见米调把头垂在两个膝盖之间,一口口抽着闷烟。旱烟杆却在指掌下晃荡。看得出来,米调显然像是被我的话“击中”了,收住刚才谈论“凶巴古国”的飞扬神彩,沉下目光,嘴角微微抖索了一阵,像是要找一个什么最合适的字眼,却终于只变成一口长叹的大气:“……也许你对。我明白,这些年来自己确实在回避着一些什么。特别是你提到的廖冰虹,我是真想见她,可是我也真有点害怕见到她,你说得不错……”
望着这张人过中年变得日渐苍老疲惫的黑脸,我心头升起一丝悲凉。
他却忽然变得激动起来,磕磕磕点着烟锅,抬高声调说:“可是,在你看来,在你们这些优哉游哉的丝路游客看来,有什么东西不是虚妄的,不是可以玩玩闹闹、看看耍耍,却不可以当真的呢?!看看你们这些赶鸭子的旅游团吧,我就常常犯嘀咕:这些人有谁真会把心思放在什么丝路、敦煌上?出过门,花过钱,照过相,回去一显派,完事啦!——他妈的,这不虚妄吗?”
我一时语塞。我自己,目下正是这一类“鸭子团”的受害者。
他冷笑:“说得好!什么‘凶巴古国’、‘温玛长老’,‘索罗卡拉’诸如此类,当然都是那位故作玄虚的‘索罗卡拉’臆造出来的!臆造也可以,玩玩嘛,这小子还当真要滚爬到沙漠上去,犯什么背时的痴呆!——你以为,我有必要去说服你们吗?!说服你们给我一个什么首肯或者名份吗?”他抄手就将还闪着红火的烟锅杵到了沙堆里,弓身站起来,“相信你们活见鬼的‘西夏之谜’去吧!让什么‘索罗卡拉’玩儿蛋去吧!——‘廖冰虹’?滚他妈的蛋吧!”
他劈啪劈啪甩着如同西北老农一样的步子,大步走到前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