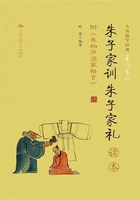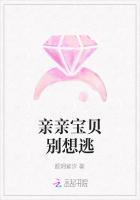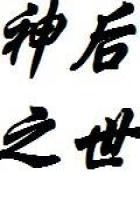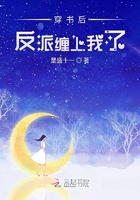我在沙井驿小学一直保持着好学生的地位和影响,而好学生的主要标志就是功课好。虽然小学里只有语文算术两门功课算是主课,我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考试基本上都是5分。那时侯,统治学校的教育思想和基本教育方针依然是苏联的那一套。尽管当时中苏已经交恶,但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却没能改变。受苏联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的影响,学校评定学生学习成绩的打分体制就是5分制。门门功课都是5分,自然就是好学生。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当了班长。二年级上半学期加入少先队,当了中队长,并且被选入少先队大队部当了大队委员,这可算是我“从政”经历的发轫。
终于有一天,我在学校阅览室里拿起了一本“新中国少年儿童丛书”,我仿佛能够读懂这本小册子里那些字的意思了。那本小册子好像是在说一些自然常识一类的知识。虽然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具体的内容,但是那种能够阅读书籍时体验到的愉悦感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二十多年以后,我在大学里学习英语,当我第一次能够读懂一些英文小册子的时候,我忽然就感觉到了一种熟悉的愉悦,童年时期第一次读懂文字的感受,就又一次在我的神经系统发生了反应,而这种愉悦感却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我想,大约所有的读书人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美妙的感受。
识文断字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人,就开始脱离蒙昧状态,向文明迈进了。
在沙井驿小学,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启蒙教育。我掌握了常用的基础汉字,凭着学到的那一点识字能力,半懂不懂地翻看了不少课外读物,到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时,我已经能够读懂当时流行的一些小说了。我那时候读书似乎读得极有兴趣,很可能就此奠定了我几乎坚持了一生的读书习惯。
五
1962年初,我刚上小学不久,父亲由沙井驿砖瓦厂调到市里的妇幼保健院做财务工作。那时,父亲不过三十来岁,为了回家方便一点,他置办了一辆白山牌自行车,星期六晚上就回来了。这辆结实得如同老坦克一样的白山牌自行车,父亲几乎骑了一辈子,在他70岁那年,终于骑不动了,30元钱处理给一个收破烂的。回想起来,那些年的周末,他为了省点车钱,从四十多公里外的保健院一路骑行回到沙井驿的家里。想想也真够惊人的,每个周末,他都要骑一次马拉松长跑的距离。有时,我们也到城里去看他,天不亮就起床,在黑咕隆咚的夜色中出门,步行好几里地,经过钟家河的黄河大桥去颖川堡火车站坐市郊车。所谓市郊车是一列专门在火车东站到西固之间运行的通勤列车,因为乘客大都是铁路职工,极少查票的,因此我们也就从来没有买过车票。
市郊列车在“自由路”有一个车站,而父亲工作的保健院恰好就在自由路车站的跟前,大大方便了我们探亲。随母亲坐了几次市郊车后,我掌握了乘车的路线和方法。有一天上午,我对母亲说了一句要到城里去找爸爸,母亲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也没在意,想不到我真的一个人走到了颖川堡车站,登上了去城里的市郊列车。到保健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骑着自行车回了沙井驿。父亲回到家里,见我不在家,母亲说我到城里去找他了,这才着了急,生怕我出什么意外,又骑着自行车返回市里。此时天已经大黑了,而我却若无其事地用父亲的同事给的钱买了六十个炒大豆,坐在父亲办公室的门前嘎嘣嘎嘣地嚼得正起劲呢。记得父亲的同事给我的两毛钱是那种印着一列火车的墨绿色钞票,我花了一毛,卖炒大豆的还找给我一毛钱。
那一天,父亲骑着自行车跑了将近一百六十里路。而我也知道了我可以一个人从几十公里之外找到父亲的工作单位。走它几里地找到车站登上火车看见自由路的站牌子下来望见那棵大椿树就能见到父亲了,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难度嘛。
我知道,我长大了,我已经从一个儿童变为一个少年了。
不料,这天夜里,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出满了红色的斑点,我在昏沉中感觉到有穿着白大褂的一些人在床头走来走去。父亲问我想吃什么,我想起一种蛋卷很好吃,就向父亲提出了这个要求。可是,当那种乳白色的蛋卷放在床头时,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去,只能勉强喝一点大米稀饭。就这样昏昏沉沉地昏睡了好几天,半睡半醒中我老看见屋顶天花板上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在晃来晃去,我以为那就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鬼怪精灵。当父亲在我床头时,那些精灵就不见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疼爱。而过去,父亲好像不大管我,就是管,也是十分严肃和严厉地教训一顿完事。我从医生护士们的谈话中知道了我得的病叫出水痘,不能见风。那是个夏天,屋里闷热得很,却门窗紧闭,我感到难受极了。好在几天后,我身上的红色斑点逐渐消退了,热度也渐渐降了下来,大约一星期之后,我就痊愈了。这是我第一次懂得了“得病”是怎么回事情。
六
1963年夏天,我母亲也调到保健院工作了,在门诊部挂号室当了一名收费员,从此结束了她做小学教师的生涯。我们家也就从沙井驿迁到了城里,我从一个乡下孩子转换为一个城里人。
我记得搬家那天,来了一辆卡车。那时候全家的家当包括铁锨、水桶、扁担等等杂物也没有多少东西,连半个车厢都没有装满。那根青木的扁担又粗又沉,到了新家后这根扁担一直在用来挑水,夜里便当作顶门的杠子顶在屋门上。
到保健院安家落户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出门去玩,走到医院大门外的那棵老椿树下东张西望,就看见过来一个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两人对视了一眼,那男孩问我:“搭补大?”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却感知到是在问我问题,就顺着他的话茬答到:“大”。却未想到那男孩上前一步就抓住了我的衣领,接着就是一个绊子要摔倒我,我踉跄了一下却未被他摔倒。虽然我猝不及防,似乎处于下风,但我不假思索地立即就投入了反击。在沙井驿的田野里,我成天在山上山下到处疯跑,与那里“公社”的孩子们也没少打架,也打出了一些战斗经验。当我反应过来眼前的这男孩不怀好意,就使出抱腰别腿的绝招,一下就把他给摔趴下了,然后将他压在身下,问他:“搭补大?”他却说:“不大了”。于是我俩就各自分开了。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我终于弄明白那男孩问我“搭补大”的意思原来是“打不打?”我才知道,这孩子名叫赵达,比我小将近两岁,竟敢和我叫阵,只因为他比我早一些日子来到这个大院生活,就可以把比他大的后来者不放在眼里。从此,我明白了什么叫做“欺生”。可谓不打不成交,经过这一摔,赵达就成了我到这个新环境后的第一个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对环境的熟悉,赵达的地位渐渐下降成为马崽。只是他个头比较高也很胖,在骑马打仗的游戏中,经常做我的“战马”。后来,我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了院子里的四个娃娃头之一,也就是小孩子们的“大王”之一。这四个大王分别是:明明,瑞平,小林和我。他们三个都和我同岁,我们带领着院子里的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成天打打闹闹,玩得天昏地暗,几乎把保健院闹翻了天。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到保健院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必须继续读书上学的问题。此时,我正处于小学二年级快结束的时候,就联系了距保健院不远的兰州市职工子弟小学。这是一所五年制的实验小学,而沙井驿小学却是六年制学校。由于学校体制不同,我在沙井驿小学的二年级学历得不到承认,直接进入新学校三年级的资格欠缺了一些,于是就重新读了一遍二年级,等于留了一级,所以就成了1967级的小学毕业生,未能像与我同龄的人们一样,成为后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老三届”。我在小学这慢了半拍的升级进步,几乎制约了我一生的命运。与我同岁却比我高一个年级的明明、瑞平、小林他们都赶上了招工参军升学的好机会,明明和小林后来都参了军,也不知道现在怎样了。瑞平上了师大附中,后来去了美国。我比他们低一个年级,在人生道路上慢了半拍,就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了。
这一转学,真的造成了我一生命运的转折,或者说是注定了我一生发展的基本方向。
假如我一直在沙井驿读完小学,再到安宁堡去读中学,同样会遇到“文革”的年代,命运就不知会怎样了,说不定会在沙井驿砖瓦厂当一名工人也未可知,反正,到市职工子弟小学读书,是有着决定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以为,父亲从沙井驿转往市里工作,无疑造成了我一生中第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个人历史和命运的转折点。假如一直在沙井驿生活下去,我后来的命运和生活道路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命运的转折的确是存在的。
三 祖父的时代
一
命运的转折的确是存在的,这从我的祖父和父亲一生的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人生道路的一些关键时刻,如果你不知道该向左走,还是该向右走,你就逃脱不了被捉弄的命运。然而,又有谁能够逃脱被命运左右的命运呢。其实,人生的一切似乎都是命里注定的。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确是有些道理的。在我已近天命之年之时,我真的有些相信这一说法了。
祖父与父亲一生的经历都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先说说他们。
祖先,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过是这“根上”分出的一些枝蔓和叶子。
提到“祖先”这个概念,往往使我们悠然生出一种遥远的历史感,仿佛祖先就是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伏羲女娲、大禹周公一类的传说人物。这固然不错,只是这种历史感有时不免显得过于遥远而难以捉摸。要周密地描述“祖先”这个概念的内涵,想必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这远不是一篇文章和一个章节所能够承担的。然而假如我们将考察的范畴锁定在某一“姓氏”或者某一“家族”的“祖先”这样一个相对单纯的概念中,事情似乎就简单得多了。
其实,“祖先”指的就是祖父以上与我们血脉相传的先人,如果将“祖父”也包括在“祖先”这个概念的范畴中,“祖先”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而“祖宗”一词,更是近在咫尺。“宗”字的含义即指家族中的父辈,父亲即是我们的“宗”。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独生子,因而,父亲对祖父而言,祖父对曾祖父而言,都只有一“宗”。到了我们这一辈,父亲育有三子一女,按中国传统的观念,从子女的视角来看,我们这一辈则分为了三“宗”。而宗族中的女性未嫁时归本姓之宗族,出嫁后即归入丈夫姓氏的宗族。我的妹妹出洋留学后嫁给了一位美国人,将来或许要归入这位洋妹夫家的宗族祠堂——假如洋人也有祠堂的话——其实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信笔写来,聊作谈资而已。
我的祖父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以九十高龄无疾而终,只是最后有几年进入老年痴呆状态,但身体一直没有大毛病,经常拄着拐棍在大街上溜弯儿,却经常找不着回家的路,出门后经常向路人打听“东关”怎么走。而兰州这个城市却没听说有“东关”这个地名,只有西关十字和南关十字的说法。“东关”是他在山西的老家所在地。那时,他或许只记得年轻时的事情,对眼前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几乎进入忘我的境界。
祖父出生于晚清,虽然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影响微乎其微,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但是,对我的父亲和我们兄妹而言,祖父的历史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大人物影响整部历史,小人物影响一个家族的兴衰,小人物的命运对他的后代的影响,丝毫不比大人物对他的后代的影响小一点。写大人物的文章汗牛充栋,构成历史的主线;写小人物的文章却并不多见,又常常要用曲笔,用小说的笔法进行所谓典型化,历史的真实细节就常常在虚构中丢失了。而文章本无定法,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祖父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国人的人生故事,所以,我就把祖父一生的主要经历当作写小说的素材先记录下来,或许有一日会以此而构思创作一篇小说,而这一篇,就先当作散文和随笔来写吧。
二
说到祖先,汉族人中流传一首歌谣: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假如你用普通话吟诵这首歌谣,你只会有一种文字阅读的感受,而如果你试试用山西方言来吟诵,你立即就会产生一种亲切感,更能体会其中的韵味和蕴涵。中华民族中许多姓氏的家族寻根问祖,有据可查的,大多只能上溯到洪洞大槐树而已,再往上,则往往无稽可考。而我们这支岳姓家族的祖先,据父亲讲,也只能上溯到洪洞大槐树而已。至于与太子少保、武穆岳飞有什么瓜葛,也已无可考究。许多岳姓的人都将岳武穆奉为祖先,以取得一种精神上的鼓励。我们向初次见面的朋友介绍自己时,往往说:“免贵,姓岳,岳飞的岳”。朋友立刻就知道我的姓氏如何写法,而不会再问类似“是立早章还是弓长张”的问题。似乎提起岳飞就能为我们岳姓后代增添一些自豪感和荣誉感。自宋朝以来,岳飞就享有天皇巨星级别的知名度,在中国,不知道岳飞大名的人恐怕极其少见。
我们岳姓的祖先如此辉煌,真令人肃然起敬。
大槐树移民,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和历史知识,是明朝初年开始的事情。元明交替之际,中原地区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而山西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尤其兴旺。山西人口在明初已达四百多万,相当于当时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山西人口稠密的地方,首推晋南汾河流域,而洪洞又是临汾一带人口稠密之县。洪洞地处交通要道,北达幽燕,东接齐鲁,西临河陇,南通秦蜀。明初移民,当然不是只迁洪洞人,但把洪洞作为移民重点,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明朝政府在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设移民局派驻官员,负责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盘资”。所谓“凭照”相当于今日之户口迁移证,而“盘资”则是政府发给移民的补贴经费。广济寺前的大槐树,就成了一个显著的标志,在移民的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移民们在大槐树下集中后,往往以同一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编排队伍的依据,扶老携幼组合成移民单位,一群一群地踏上离乡之路,依依不舍地一步三回首,从而吟诵出我在前边提到的那首民谣,流传至今已六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