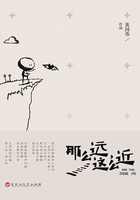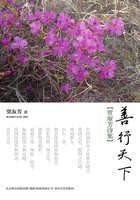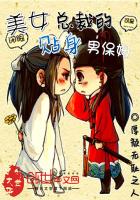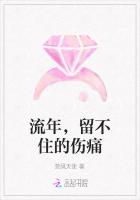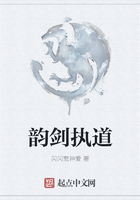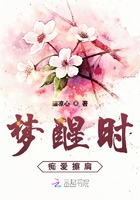本拟以中国作家为例,因我常在作理论探讨时剖析一些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已屡遭“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之讥。但想了想,决定还是举外国作品,因外国作品终究也还是作品。而月亮其实并无国籍(正如儿童文学本不应以国为界),无论从哪国看,都会有圆有缺。更何况,硬要在艺术分析中体现爱国主义并想以此封他人之口,我总觉得不算聪明。
我想举出的,是大家都熟悉的新美南吉,他的代表作《去年的树》,一篇极其短小隽永的童话。
它写一只鸟和一棵树成了好朋友,鸟儿天天唱歌给树听。冬天来了,小鸟要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就和树约好,明年再到这儿来给大树唱歌。可到了第二年春天,树不见了,只剩下了树根。树根告诉小鸟,伐木工人将树锯倒,拉到山谷去了。小鸟追到山谷,工厂的大门告诉它,树被切成细条条,做成火柴,运到村子里卖掉了。鸟儿飞到了村里,在一盏煤油灯前,它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就问她知不知道火柴在哪儿——
小女孩回答说:“火柴已经用光了。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个灯里亮着。”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
接着,它就唱起了去年唱过的歌儿,给灯火听。
唱完了歌儿,鸟儿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儿,就飞走了。
故事完了,就这么简单。要说浅,它已经浅到极点,两岁的幼儿也能听懂;但它又是那样的深,才高八斗的大学问家,也常会赞叹那字里行间深而又深的苍凉。
这里没有外在的道德教训,也没有成人社会的那些思想和理念,它所深入人心的,是人生的无可回避的处境、难题和情感。即使是儿童,也已开始体验这样的人生了,他们日渐长大,将会有更为深广的体验。所以,这个小小的作品,可以让人从小读到大,读到老。它当然可以有多义的发掘,但在我看来,有两个向度,是尤为突出的。其一是小鸟和大树的友情。对儿童来说,这样的友情是十分珍贵的,刻骨铭心的,那些大人们不当一回事的片言只语,在他们可是天一般大,是一诺千金的,他们会为之日思夜想,决不可玩忽。当小鸟好不容易盼到了春天,却没法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它的焦急、惊惶、疑虑,当会引起各个年龄段的受众的无穷的共鸣。其二,就是关于永远的消失。儿童大多还没经历过人生的悲剧,他们总是愿意将世界想得更其光明,已经拥有的美好的东西,他们希望一直有一直有,一旦有什么消失了,他们总希望有一天能再找回来。但坚硬强悍的现实人生,早晚会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小鸟碰到的,就是永远的消失,永不可逆的离去,不仅树没了,树的细条条也没了,用细条条做成的火柴也用光了,只有那一点火还亮着,但它很快也要熄灭的。小鸟再也找不到大树了,它没法实现自己的诺言,只能聊胜于无地,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对着灯火,唱一曲去年说好的歌……这里边,其实有着关于死亡的体验和思考,儿童未必会往这方面想,但这种审美体验会伴随他们未来的人生,也许竟会伴随整整一生。日本民族对于死亡本来就有深邃的思考,从这个作品中,我们也可隐隐看到日本的人生和审美体验的特征。可以说,这个小小的作品,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儿童文学的,也是属于整个文学的。我想,把它放到辉煌的世界文学之林,它既不会输给安徒生,也不会输给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甚至,也不会输给从未写过儿童文学的莎士比亚。——我想,这就是儿童文学的深度。
我说清了上述的三个问题吗?也许还没有。记得有一位作曲家用小提琴演奏了自己的新作,一位记者问:“这个曲子的主题是什么?”作曲家重新演奏了一遍说:“这就是主题。”我不会小提琴,所以,只好再用学理的方式,简述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儿童文学的深度,是文学的审美的深度,是关于人生和人性的深度,这和成人文学是相去不远的。托尔斯泰说过,他不愿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写一篇小说以解决地方自治问题,却愿意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作品,它让人读了更热爱生活(大意)。这也适用于儿童文学,并且,我认为这是对于文学深度的最好的回答。具体例证:《去年的树》。
第二、我们还是要深度,就像我们说,“人间要好诗”。但诗不可能篇篇好,但我们还是想要好诗。至少,在我们的儿童文学界,要有对于好诗的渴求感,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渴慕,如这一点想头也没有了,只想着要畅销,要多赚,要快赚,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在我,是有点如《去年的树》里那个小鸟似的焦急、惊惶和疑虑的。当然,各人可以有各人的追求,但整个儿童文学界,还应该有对于最具审美深度的好作品的追求。好作品示例:《去年的树》。
第三、追求深度应有度,度就是儿童能够接受。但这个度不是绝对的,因为真正优秀的作家应当有所作为,应能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但这个新路仍要让儿童能够接受,而不只是让自己的批评家兄弟能接受,只自己几个人关起门来称大王。这就牵涉到关于深度问题的最难解决的部分了,也就是:你怎么把深的东西写浅?——是要真浅,而不只是表面的牙牙学语,不是“蹲下来和孩子说话”。是要极清浅而极深刻,是要在深和浅的两个方向同时掘进,是真正掘进了而又仍是一个审美整体,是“不以浅害意”。它同时又是你的真正真诚的身心投入,那里要有你的真生命……这个问题越说越复杂,我想,具体的论说只能放诸以后,另设专题了。现在,不妨仍以具体例证说话。范例:《去年的树》。
说来说去,最要紧的,大概还是这句话:它有多深,就该有多浅。
这就是儿童文学的深度。
(写于二〇〇七年初春)
8、“廉价效果”
记得在“文革”后期,上海的一些剧作家常被招集拢来,“集体创作”一两个配合形势需要的戏,有话剧,也有先是话剧然后再改成电影本子的。但因为是从政治需要出发,或曰“从概念出发”的,说教味很重,所以观众很少有真正感兴趣的。组织者也想提高创作质量,有一次,在创作一个名为《盛大的节日》的剧本时,就请老导演谢晋来提提意见,还希望以后由他亲自任导演。听说那次谢晋谈了不少,别的我都忘了,有一点却一直记到现在。那个戏里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给“造反派”栽赃,要自己的秘书把手臂砸断,然后截肢,然后说是造反派打的。这成为戏里的一个高潮,秘书的犹豫和反悔也牵动了不少人的心,大家都看好这个情节。但谢晋说:“这个情节不好,这是制造廉价效果。”
我当时听过传达,心里很震动。我能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不知理在哪。所以我只能佩服他的辨别力,很希望自己今后也能够迅速辨别廉价与否。而因为不解,多少年来,凡有作品过眼,我总在体察和思考这一点。现在,半生已逝,我忽然发现,自己有些明白了。
促成我豁然开朗的是浙江一位研究生的来信,她问,为什么我在那本《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的专着中,写了“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却没有“死亡”的母题呢?此前,也有儿童文学界的朋友提出,我何以没有专门列出“苦难”的母题?关于儿童文学中“死亡母题”的思考,前不久已经有了一些争鸣的文章了,可见,有不少同行已在考虑这一问题。但我对这一问题,却确实不是遗漏,而是有自己的想法。
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其实还是说了这个问题的。我认为,成人文学的三大永恒主题——爱与死与自然,“对于儿童而言,在他们的欣赏范围中,恐怕只有‘自然’这个主题备受青睐;而‘爱’和‘死’,尽管也为他们所关怀和涉猎,但毕竟同他们的生活和心理有很大的距离,难以成为他们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我又说,“随着儿童的成长,随着青春期以及后来更漫长的人生岁月的到来,儿童的心理侧重必然会发生移位和变更。他们对于‘母爱’的关怀渐渐转向了‘情爱’,他们对于未来的遥望则渐渐被越来越沉重的现实感所淹没,以至被‘死’的忧虑所替代。这就规定了在文学审美中,儿童文学的母题向成人文学的永恒主题演变的轨迹。而青春期的文学,表现少男少女‘分裂时期’的作品,就正处于这种母题转变的临界点……”
也就是说,在我所划分的那个粗线条的框架中,“死亡”还不应成为儿童文学的一个“母题”,它还不能与“母爱”“父爱”相并列,我觉得它应当从属于“爱的母题”之中的“父爱型”,是它下面的一个分项。因“父爱型”作品既体现成人对儿童的爱,这种爱又不回避生活的沉重和严峻,此中当然包括了“死亡”和“苦难”。这并不是说儿童文学要一味回避它们,只是,它们在整个儿童文学中的比例,不可能那么大;它们在创作上,也有些特殊的难度,不能不引起创作者的特别注意。
事实上,对于成人文学来说,死亡和苦难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由于死是人生的大限,没有人能够逃脱死的痛苦;苦难又是直接诉诸人的感观的,所以它们的强烈程度往往要超过其他描写。但人不能老是谈论死,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人可以超越死之恐惧而生活,人能暂时避开这个话题,能利用它的积极面(如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而不在此中沉沦。所以,优秀的成人文学善写死亡与苦难,却不一味在此渲染,而最终能给人充实的审美体验,使人更加热爱生活。如古典雕塑《拉奥孔》所体现的“不到顶点”(请参阅莱辛的同名论着和王朝闻先生相关的散论),就正体现了这种人生与艺术的智慧。
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动辄展示死亡与苦难,无异于拿“麻胡子”吓唬孩童,效果虽然会出乎意料地强烈,但离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距离,也会出乎意料地大。儿童的心更为单纯,它们更易被攫取,他们所受的暴力刺激将永远铭刻在稚嫩的心底,他们还没学会淡忘,他们几乎没有解药!所以,真正爱儿童的作家艺术家会在这些方面投注更多的智慧和心力,而古今中外名作中的成功例子也是并不少的。我认为最成功者之一,就是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在这个优美的童话中,暗含了“死”的意象,却使儿童得到了极大的审美享受。
于是我明白了当年谢晋的意思。是的,离开了生活依据与情节的必然性,拿些死亡、苦难、残疾、迫害、虐待(现在则又加上性)来作渲染,以达到一种强力效果,那是并不难的;但这只是一时的刺激,却不能换来审美体验——这不就是“廉价效果”吗?(顺便说一句,现在街上常见的展示骇人残疾以博取同情的乞讨,所利用的也正是同一种人性弱点)
所以,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尤其要避免这样的廉价效果;在一个浮躁的、急于一夜暴富、惟恐不能“吸引眼球”的文学环境中,真正有责任心、愿为儿童着想的人,更不应轻易使出这最易得手的“杀手锏”——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一锏将会打在谁的头上。
我不得不说,最近,我读到一位年轻朋友的一本写校园暴力的书,虽然打出的是阻止暴力的旗号,而我看到的,却只有借展示暴力而获取的“廉价效果”。虽然这效果会直接转换成“注意力”、“印数”、“效益”……我则顽固地认为,作者还是不要写这样的书,出版社也以少出这样的书为好。
中国的图书市场太不缺这样的书了。我们缺的是《去年的树》。
(写于二〇〇六年初冬)
9、走出战争状态
自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直到“文革”以后,在儿童读物的布局上,存在着一种偏颇——战争题材的作品,具体说是写儿童介入战争,亦即写“娃娃兵”的作品,实在太多,写法也实在太单一了。这在一个时期内是看不出来的,但半个世纪下来,我们应该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了。
就我自己儿时的阅读经历来说,印象较深的小说有《小矿工》(那是我最早读完的长篇),有《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那一度成为我最喜欢的书),还有一本《青春似火》(书里的情节我全忘了,但当初阅读时的美好感觉却完整地保留在我心里)。就单本的书来说,这都是相当优秀的作品。它们写的都是战争年代的少年生活,无一没有血淋淋的搏斗场面,其中的“小马倌”则是个真正的兵——一个九死一生的“抗联”战士。那时的少儿读物,除少量写学校生活的小说,和翻译的外国儿童小说外,恐怕十之七八,都是写战争,写“娃娃兵”的。而翻译小说中,尤其是来自苏联的那一部分,写“娃娃兵”的也不在少数。
这当然有原因,除了观念上的原因,还有历史原因。“解放战争”紧接着“抗美援朝”,战争曾是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当作家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写作,他们怎能抹去这强烈乃至惨烈的记忆?人们心中时时提防着或准备着新的战争,“要准备打仗”后来还成为一个长期的口号。所以,在给儿童看的书、电影和其他艺术品中,“娃娃兵”形象的大量出现就在所难免了。对此,我们身在其中,早已熟视无睹,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前几年,我像忽然被重锤击醒了一般,认真思索起这一问题来。使我猛醒的是这样一篇报告文学:《硝烟里的娃娃兵》,作者欧阳墨君,载二〇〇二年五月《少年文艺》(下半月刊)。作品写的是阿富汗原北方联盟十五岁的少年将军胡马云,但作者没有孤立地写这一人物,而是把他放到了很大的国际背景下。文章一开头写道:
二〇〇一年六月,国际儿童权益保护组织在向全世界大众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在看似和平与幸福的当今世界上,还有近千万的少年儿童被笼罩在战争的可怕阴影下,他们遭受着战争的摧残,同时也被卷进了战争的漩涡,充当起战争这个杀人机器的血淋淋的齿轮。据调查统计,在塞拉利昂、科索沃、刚果、阿富汗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三十万十到十五岁的少年娃娃兵在战火里浴血……
这使我反思起儿时所接受的价值观,反思起我们那时的小说、电影、戏剧和歌曲来。我想,哪怕有再多的理由,我们也不能硬说我们作品中的小战士不是“娃娃兵”。战争终究是战争,它总是有共性的。那么,我们怎么把自己早已熟悉的价值观,和现在的世界性问题接轨呢?我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思索。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从小所读作品中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我们的“娃娃兵”是把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献给“正义战争”的,没有他们所献身的“战争暴力”,就不可能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都是对的。所以,对这些小战士在战火中的成长和他们的英雄主义的歌赞,应该是无可否认的。但同时我又想到,不管怎么说,战争环境总是反常的。让儿童进入这种反常的环境,总是违反儿童成长规律的。如果把其中的一面绝对化,把这种“娃娃兵”的生涯理想化、神圣化,仿佛这才是最美妙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也是不正确和不真实的。
我把当时的想法写成了一篇《关于“娃娃兵”》的随笔,发表在二〇〇二年的《少年文艺》上。但我的思索并没有结束,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没完全想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