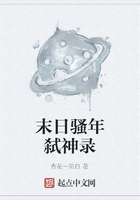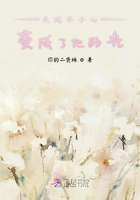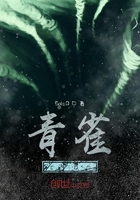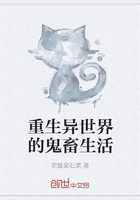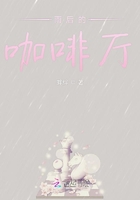1、七十年代的“朝花夕拾”——我读《同学少年都不贱》
我读张爱玲小说轶作《同学少年都不贱》,可说是一则以惊,一则以叹。惊者,“惊艳”之谓也;叹则是惋叹,或曰扼腕之叹。我没料到张爱玲在她文学生涯的后期还会有这样的力作,我不同意现在大报小报上看到的那种差强人意式的艺术评价,我以为它虽不及其早年作品的丰润流丽,但那种枯瘦简淡的文词背后的俗世影像与沧桑感悟,以及对于人心的单刀直入式的尖刻而精准的剖析,比起她创作盛期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她不曾将这篇作品“搁开”,而能连续写出几部这样的小说,那么,一种新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准意识流式的)“晚期张爱玲”风格或许就能确立。这对于中国小说发展史,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风格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极端的含蓄和简洁。粗看平淡无奇,细一推敲,就会发现容量惊人,有时一句寻常的话里竟能挖出无穷无尽的东西。这得之于她自小心仪的《红楼梦》,但更得之于她晚年花过大功夫的《海上花列传》;而与李健吾先生翻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文风上竟也有一种奇异的妙合。
小说以中年女性的眼光回味当初住读贵族女中时期的青涩生涯,而又与后来的变化万端的漫漫人生对照着写。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女中时期那种泛化的同性恋倾向。但小说女主角赵珏后来反思当年的情感,便发现那时其实相当幼稚,更多的只是“那种天真的单恋”,与在美国看到的同性恋真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那是少女们到了青春期,内心有一种情感的萌动,周围又没有异性交往,于是对女伴(或同性的师长)产生了一种虚拟的爱恋,这在女孩的成长中往往是难免的,而在女子中学的特殊环境里就更普遍了。作品坦率而真切地写出了这一“难言的奥秘”,恰如别林斯基所要求的那样,“真实到了令人害羞的地步”。
但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当年的同学——赵珏和恩娟,后来有了很不相同的人生经历。恩娟嫁给了犹太人李外,两人说不上有什么爱情,“当然性的方面是满足的”,在赵珏看来,“至少作为合伙营业,他们是最理想的一对”。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后来李外的境遇越来越好,居然进入美国政界做了高官,恩娟自然得意非凡。赵珏对于爱情则不愿妥协,她宁可为抗婚而退学乃至脱离富裕的家庭,后来跟一个朝鲜商人跑单帮,再后来嫁给了美国大学的一个华人教师,她始终认为:“感情不应当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结果。”赵珏的婚姻并不如意,后来与丈夫也分手了,但她一直保持着自尊自爱,并小心地不受任何人的利用。书中最为警醒的,是她们两人各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后,终于恢复了联系的那次谈话。因偶尔说及当年另一位同寝室女生芷琪的婚姻生活,恩娟带点狠毒地数落芷琪的丈夫,指责让她结婚的哥哥,还动情地说:“她那么聪明,真可惜了。”说得几乎掉下泪来。虽然明知道学生时代恩娟对芷琪有过同性的“单恋”,而这么多年后恩娟的态度,仍让赵珏感到了“震动”。过了好些日子,赵珏才算想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骇异恩娟对芷琪一往情深”。她记起自己从前也有过一个同性的“单恋”对象,后来因事而“反感”,中断了交往,但反感并不等于“淡漠”。二战后自己在兆丰公园远远地看到她时,却非但没打招呼,而且“完全漠然”了。为什么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恩娟却做不到呢?她写道——
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
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
是的。她不是不忠于丈夫的人。
赵珏不禁联想到听见甘乃迪总统遇刺的消息那天……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甘乃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原来赵珏当初的“震动”和“骇异”,在于她直觉地发现恩娟其实一生都不曾有过真正的恋爱;她与丈夫之间这么多年的“合伙营业”,也还不足以冲淡“她们从前那种天真的单恋”。
这样看来,得意非凡的恩娟事实上非常可怜。关于“甘乃迪”(即肯尼迪)的联想更说明问题:他一生轰轰烈烈他却死了,我在洗碗我还活着。这洗碗者不只是说赵珏自己,更是用来影射恩娟的,因其“忠于丈夫”的婚姻虽然“活着”却不会有真的幸福。作者笔墨的含蓄有力,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赵珏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她也得为改变即将到来的贫困境遇而努力。所以,当她“在《时代周刊》上看见恩娟在总统游艇赤杉号上的照片”时,那种一在天上一在地下的“云泥之感”,有如“当头一棒”,还是“够她受的”。作者由此点出人世间女性时时面临的两难困境。
如此看来,张爱玲在小说题目上,将老杜原诗“同学少年多不贱”改一字为“都”,必定不是笔误,而是故意为之。因为她们当年住读的是“贵族”女中,当然“都不贱”(此中无疑充满反讽);但后来呢,后来进入了漫漫人世,只怕都“贱”了。一个“都”字,点出了女性两难困境的难以逃脱,小说的深意正在于此。不过“贱”字也未必完全是贬,它在这里的本意,其实就是张爱玲倾其一生予以关注的“世俗”,或“俗世”。
以饱经俗世沧桑的眼光观照当年女中生涯,当然可以将少女的幼稚、单纯和尴尬看得很透;以女中时代的心理作对照,则更可看出今日人心之复杂、世故与难以相通。作品虽是小说,却有着极强的自传性(它写成之后被作者“搁开”,恐怕也是因其过于纪实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妨视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产生于海外的又一部“朝花夕拾”。
(写于二〇〇四年春)
2、尹雪艳的美丽阴影
“尹雪艳总也不老。”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开篇第一句,就显示了非凡的功力。这既是整个作品的提纲挈领之句,又涵括了小说在艺术尝试上的独到之处,还把最重要的意象推到了我们面前。但这又是极为平常的一句句子,没有任何华丽眩眼的字词。也许,这就是白先勇的风格。
小说写的是当年上海滩上的红舞女尹雪艳,她永远是那么年轻美貌,从上海到了台北,几十年过去,魅力丝毫未减。而当年捧过她的那些老板、官员、小开,一个个垂垂老矣,颓丧怨怼,叹老嗟贫,今不如昔。但她还是笑吟吟地款待他们,让自己的公馆成为他们安闲的乐园;当然,他们每次掷下的“桌面”也不低,总在两三千元以上。可是尹雪艳也有坏名声,就是谁沾了她谁都要倒霉,轻则去官破产,重则一命呜呼。在这篇万把字的小说里,作者不动声色地写了三个“恋爱”故事:一是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天天到百乐门门口候着尹雪艳转完台子,两人一起上国际饭店十四楼摩天厅去共进华美的宵夜”。他拼命投资,不择手段地赚钱,想把尹雪艳周围那些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当他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的那天,“尹雪艳在百乐门停了一宵,算是对王贵生致了哀”。另一个是上海金融界热可炙手的洪处长,休掉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把尹雪艳娶进了法租界一座华贵的洋房里;可他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理所当然地离开了他。第三个是近年的事,写得更为详细:台北水泥公司风头正健的经理徐壮图,才四十出头,偶然进入尹公馆,便迷上了对他体贴有加的女主人,从此经常夜不归家,脾气变坏,在厂里也惹了众怒,一次拍桌喝骂工人时,狂怒的工人突然拿起扁钻刺死了他。在灵堂上,被人视为祸根的尹雪艳居然一阵风般进来,签名,鞠躬,还跑到呆若木鸡的徐太太跟前握握手,然后踏着轻盈的步子飘走了。当晚,尹公馆灯火通明,笑声麻将声不断。
这个故事最为奇特之处,就是开头的第一句:“尹雪艳总也不老。”除此之外,可以说它是严格写实的。当年白先勇在台北办《现代文学》杂志,提倡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并列为台湾两大文学流派,二者不仅在题材与价值取向上有不同追求,在艺术形式上也有不少对立的见解。“乡土文学”派更倾向于传统与写实,奋力开掘本土题材;“现代文学”派则更强调世界眼光,关注当代的文学流变,艺术表现上也强调出新出奇,惟恐陷于陈旧和雷同。白先勇从小生活在十里洋场,还未成年就被叔叔大哥们带到百乐门舞厅去开过眼界,对奢靡的生活有感性经验。随父辈迁谪台湾后,他看到了太多不得志的大官阔佬渐渐老去,成天在怀恋和回味中过日子。对他们来说,舞池和麻将桌,还有年轻美貌的女人的陪伴,几乎是人生的惟一安慰了。这也是他们从上海到台北,从当年的烈火烹油之盛到现今没落颓丧的余生中,惟一不变的东西。于是,变与不变,转瞬即逝的荣耀繁华与看似永恒的舞曲麻将美女,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重要的意象,进行了自己独到的艺术转换,把不变的东西全部集中到尹雪艳“这个”舞女的形象之中,从而更为强烈地衬托出了吴经理、宋太太这群行将就木的旧日阔佬的悲哀。正是尹雪艳的“总也不老”,使这篇小说具备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的形式特征。
台湾女批评家欧阳子认为,尹雪艳是“死神”的象征。她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说:“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之意象,暗示她是幽灵……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之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但白先勇对这些评论的回答则很发人思索,在《白先勇与青年朋友谈小说》中,他说:“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什么象征意义,后来欧阳子说,我愈想愈对,哈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余秋雨的分析也许更有意思,他在《世界性的文化乡愁》中说:“白先勇先生在写作这些小说时未必有意识地埋藏了这些象征,如果真是这样他就无法流畅地写作了。只是因为他心中始终有蒙鸿的历史感和乡愁郁积着,一旦执笔描写具体人物时也就会有一种自然吸力把两者对应起来,对应得让白先勇先生自己也不太明白。”我想这应该是对的,只可惜说得有点玄。其实,以我之见,真要说象征,说“幽灵”,那尹雪艳未必一定就是“死神”,她更是一位“时间之神”,她“总也不老”,相对于他人的醉生梦死与转瞬老去,正应合着时间的概念;那一阵“风”的意象,比之于“死”,也不若比之于时间的飘逝更为妥贴。同时,也可以说她是“欢乐女神”,那种用以抵御内心无聊的寻欢,其最后结局,总是以生命的消逝为代价的;何况这样的欢乐只能是假欢乐,因为那保持着永远的笑脸的“欢乐之神”,恰恰是“无情”的。而在这种幽玄的多意性的背后,却有着明明白白的现实的支撑。是什么现实呢?我以为,就是作者的早期经验和他到了台湾后所见的那些颓唐的人生,也就是上文所分析的“变与不变”。
末了还有一个问题: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到底要讥讽或谴责谁呢?是吴经理、洪处长、徐壮图他们,还是“永远的尹雪艳”?在我看来,作者对双方都有很辛辣的讽刺。如在写了葬仪之后紧接着写道:“当晚,尹雪艳的公馆里又成上了牌局,有些牌搭子是白天在徐壮图祭悼会后约好的。”淡淡的不经意的语气中,其实把双方都一网打尽了。然而,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讥讽或谴责,这一点是需要特别弄明白的,不然读这样的小说,就无异于买椟还珠。作者更注重于表现人生的沧桑感,感叹生命的短暂与脆弱,感叹欢乐难留,欢乐不再,对浮面的欢乐和美丽表示他深深的质疑,也对人生的虚无表示他的惊讶和无奈。下面这一段关于打牌的文字,是这篇小说中“被引用率”最高的,诸看客不妨多留心眼:
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着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地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写于二〇〇六年初夏)
3、《铸剑》心解
《铸剑》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看的作品之一,其可读性与直接感染力,惟《伤逝》可与比肩。小说的情节十分精彩,大开大阖,每一步发展都出人意料;气氛上也是动静交织,紧张与荒诞相交叠,逼着你一口气读下去。但读完后,你既觉得充实,有一种审美的愉悦,同时却也会茫茫然,因为一下子很难弄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
小说中的眉间尺刚满十六岁,就被母亲派以重任,要他带上亡父生前铸就的剑,去找国王报仇;十六年前,因为宝剑炼成了,国王怕再有别人得到这样的好剑,就拿铸剑人的脖子试了剑锋;其实父亲早有预感,所以同时炼就雌雄二剑,而把雄剑留给了未出世的儿子;儿子上路了,但一切都不顺利,没找到机会不说,国王却已得到密报,派人来抓他了;这时出现了神秘的黑衣人宴之敖者,愿意替他报仇,但要借他的头和剑;眉间尺没有多犹豫,提剑从后面砍下了自己的头,把自己的“性命和宝贝”一齐交给了黑衣人;黑衣人带着剑和头,上门去为国王表演,让人头在煮沸的鼎里唱歌,当国王凑到鼎前观看时,一剑砍下了国王的头;两颗人头在沸水里互咬起来,眼看眉间尺要吃亏,黑衣人又举剑砍下自己的头,三颗头一起混战,终于把国王的头咬烂了;三个头颅煮成了骨头,分不出彼此,最终只能一同放进金棺落葬。
很多研究者都想从故事里找出意义来,有的将它归为“复仇”,有的将它提升为“革命”,还有人干脆称这是向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发出的复仇宣言。然而,鲁迅在文末明明写着“一九二六年十月作”。这离“四一二”还有整整半年。虽说他当时还没定稿,又把它从厦门带到广州,但最后也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三日定稿的(可参阅《鲁迅日记》),这离“四一二”还有九天,离国民党在广州发动的同样性质的“四一五”政变,则还有十二天。鲁迅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敏感如鲁迅者,一定也会体验到当时黑云压城的气氛,这在他的心理上和作品的叙述中,当会有所反映。这我们将在后文谈到。
至于“复仇”,当然是小说的题旨之一。但鲁迅花了这么多时间推敲,如此用力地写成的作品,如果仅仅就是为了演绎一个离奇的复仇故事,那又不太像是鲁迅的所为。有人认为《铸剑》是鲁迅创作的“武侠小说”,宴之敖者体现的是中国的“侠义精神”,我想,他也是把复仇视为作品的全部内核了。蕖的确有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就是为着津津有味地讲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故事,至于故事有无意思或意思的大小,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关切所在。但鲁迅绝不是这样的作家。
事实上,在复仇故事背后,还暗藏着一个故事,那是鲁迅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