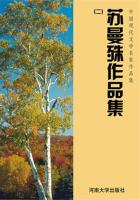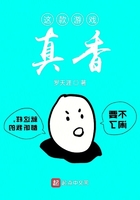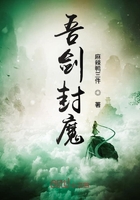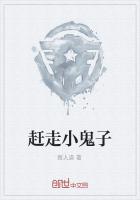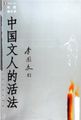(二)“国歌八论”之争
进入江户中期后,日本歌坛上爆发了一场称作“国歌八论”之争的大辩论。发生在荷田在满、田安宗武、贺茂真渊三人之间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一场儒家功用诗学与神道教审美诗学之间的对立,经过这次论战,儒家功用主义诗学在和歌创作领域失去了发言权,从此一蹶不振。在此后的和歌理论界主要分成两派,一派是以贺茂真渊为代表的国学者歌人构成,他们将和歌作为国学研究的工具,在和歌创作上坚持古典主义;另一派是以小泽芦庵为代表的注重现实主义创作的歌人们。
1742年,荷田在满(1706—1751)发表《国歌八论》,作者荷田在满否定了和歌对社会的政教功用性,强调和歌的消遣娱乐作用,作者对堂上和歌的权威性进行了抨击,他的目的在于将文学从政治、道德的功用论中解放出来,还诗歌以本来面目。田安宗武在《国歌八论余言》中,认为和歌不但没有政教功用性,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实用性,《古今和歌集》以后创作的和歌都是追求唯美风格的消遣娱乐之作。
贺茂真渊(1697—1769)是一个国粹主义者,对外来的儒家思想及佛教思想采取抵制的态度,主张诗歌与文章应复古,提倡“万叶古调”。他从国粹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主张复古,认为外来的儒释思想束缚了日本人思想,传统的和歌虽然质朴,但它可以真实地表达日本人的情感,但却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渐渐失去了活力,从内容到语言都变得混乱起来,片面地追求华丽的词藻,过分依靠技巧,而丢掉了原本宝贵的东西。因为和歌立足于天地自然间,应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就需要排除一切矫情造作,贵真尚实。只要自然是永恒不变的,那么返璞归真、回归古道、找回远古先民们的质朴率真并非不可能。贺茂真渊特别强调诗歌要表达的“意”(与“心”的日语读音相同,即指诗歌的思想内容)应自然而发,反对以理入诗;而田安宗武则坚持内容的“理”与形式的“技”并重的二元论,真渊对他这种将诗歌与政教功用等道德因素结合起来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作为国学家的贺茂真渊只是将和歌作为探寻古道的工具,并非将和歌作为艺术对象,但客观上起到了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贺茂真渊去世后,小泽芦庵继续对传统的歌学道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小泽芦庵(1722—1801)主张和歌创作的最高理想是不使用技巧,直抒胸臆。他说,和歌者自成其道,如果想从和歌中得到有趣或者珍奇之物者将一无所获,因为和歌之道乃自然之道,刻意求之则失去自然属性。他认为将心中所思所想,使用当代之通俗言语表现出来,只要能“闻其理”就是好和歌。小泽芦庵的这段谈话说的是诗人创作时应有的姿态,创作和歌时不能“思求”,即不能总想着如何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他认为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想法是有害的“邪道”,诗歌的创作意义与目的在于对生命力的某种感动,或是对心灵震撼的把握与表现,而对构思谋篇的思求、人工的雕琢粉饰,都会削弱诗人的感悟与灵性。在创作的方法上,小泽芦庵主张使用通晓明易的“今词”,让读者能读得懂是最主要的标准。在他看来,传统的堂上派和歌以及贺茂真渊改革派的作品都使人“不能闻”,即晦涩难懂。小泽芦庵反对古典主义的雕章琢句,主张使用通俗晓畅的语言进行创作,将平民大众作为诗歌创作的服务对象,具有现实主义的气息,而不是将诗歌作为自我娱乐、消遣养性的风雅之物。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练习对创作的重要性。小泽芦庵的诗学理论对江户后期平民化诗歌的兴盛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富士谷成章父子的另类歌论
国学者富士谷成章(1738—1779),代表作有歌学书《换玉帖》,为其遗稿,由其子成胤整理,分“境、旨趣、体、上”四部分,他的“体”的概念与《古今和歌集》的六体说不同,为五体,即直叙歌、袭歌(引用古歌的歌语)、守歌(用典)、寄歌(兴的手法)以及向歌(对偶句)。其许多研究都是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在今天看来仍有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富士谷成章父子的学说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富士谷成章采取的是客观归纳式的研究语法,其子富士谷御杖采用的是主观演绎法。富士谷御杖(1767—1823)与其父相同,1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受到其伯父皆川淇原和叔父小河成均的熏陶,曾师从于广桥兼胤、日野资枝等人,受到名师的指点。富士谷御杖的歌学理论具有日本神道教的特色,被称作“言灵倒语说”。“言灵”是日本古代的一种信仰,认为语言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所谓“倒语”,源自《日本书记》一书,即不直接说,而是使用反语或从侧面说明的一种表达方法。人如果在随心所欲的“偏心”状态下,将其思想付诸“为”(言行)的话,便是破了“时宜”。
此外,富士谷御杖在《真言辨》中进一步深化了其父学说,提出了“五典说”,即偏心、知时、一向心、咏歌、全时。他在上卷的“歌道之旨趣及恋歌之论、贤愚之则”中表明:原本诗歌是不可破坏“时宜”的,当“一向心”的情绪不可抑制时便咏言为诗。“时宜”与“一向心”(非诗歌则无以排遣之怀抱)两者相辅而成歌道。因此,有必要用神道来约束和安抚“偏心”。根据叶渭渠的解释,“偏心”是以自我为本位,明知是非,心却难以抑制,而且有时把“非”误认为“是”,心偏一方。而“一向心”则是说当理性压抑“偏心”时,所思非但没被抑制得住,反而受到强烈抵触,将郁情原原本本表露出来。如果“偏心”与“一向心”被付诸行动,则会造成严重后果,为此须借助神道的力量来抑制“偏心”,用歌道来化解“一向心”。也即是说神道的作用是安抚“偏心”,使之时刻不违正教;而歌道便是用来慰藉神道所不能抚慰的“一向心”,以全“时宜”,如同李卓吾所言“夺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而诗人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情怀,与其使用“倒语”形象地表达于诗歌表面,反不如化作灵魂留在诗歌内部,这样郁闷的情怀便更好地得到排遣,如此达到一种“真心”境界,也即是“物我一体”的最高境界,自然成全“时宜”。而“真言”是人达到“真心”境界时,情不自已而“咏言为诗”的诗语,它与日常的话语不同。
富士谷御杖用语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诗歌,《万叶集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富士谷御杖晚年时的著作,在对《万叶集》的注释上与贺茂真渊意见相反。贺茂真渊认为《万叶集》是古人朴素感情的真实流露;富士谷御杖认为只凭对诗歌表面的分析就可以理解诗歌本意的想法是极其幼稚的,应该考虑到作者生活的时代以及作者的文学主张,并结合诗序,才能解读出诗歌的言外之情。他的这种理论背后有其父的国语学、歌学,其伯父淇园的儒学,及中世的神道学、心学,甚至江户时代西学东渐的“兰学”等的影响。
(四)桂园歌派与“格调说”
香川景树(1768—1843)创立“桂园派”,以贺茂真渊的“真情说”理论为基础,辅以小泽芦庵的歌论,强调和歌的缘情性和音乐性。他认为饮食、男女、语言为天下之三大事,符合时代的潮流,诗歌是表现社会文化的最佳载体。与别的国学者不同,香川景树并不是将诗歌创作视为“余技”,而是将其当成自己终身从事的重要事业,他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巩固了和歌的文学地位。
香川景树在《调之说》一书中说道:“调者,扎根于天地,贯穿于古今,横亘四海统领异类(说)。由诚实而发言,其歌遂成天地之雅调。若出自诚实、真情而发之嗟叹,无论言词如何,皆可成雅调,可自成秀歌”。从这个意思上说,诗歌便是单纯地将情感“发言为诗”,这其中不可掺杂半点说理之词,不能以说理代替作诗。《随所师说》中有句名言说得更直接明了,“诗歌(的目的)不在于说理,而在于调”。那么,所谓“调”者何也?他的学生八田知纪解释说,调即是“姿”。而“姿”者,按照藤原公任及藤原俊成等人的说法,是指让人可感受到的和歌外在的风格或韵味,与“心”与“词”的完美结合所表露在外的风格,或香浓或妖艳或清丽,如同美女的风姿,给人以美妙的感受。我们认为诗歌的艺术形式最终还是要为思想内容服务,应根据内容需要灵活运用,不能不顾内容而炫耀技巧。因此,空海和尚在《文境秘府论》中说:“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这是很有道理的。
蔡镇楚先生说过:“格调说是明代诗学批评的最基本的范畴,源于高棅,成于李东阳,盛于明代前后七子。格有标格、气格、骨格、品格、意格、体格、句格、格式、格力等;调者有气调、意调、风调、律调、音调、句调、情调等。一般认为,体格、句格、律调、音调者主要指诗文的体裁、句法、音韵等外在的形式;而骨格、意格、气调、风韵等,主要是形容诗文内在的气度意蕴之属。故以格调品评诗文,应该注重诗文内在的气韵与外在的艺术形式的妙合无垠。”
香川景树说“调唯诚(真)也”,而诚即是真情,是人类共同的美好天性。所以说格调其核心内容是“贵真”、“主性情”,而缺少诗教的道德伦理属性,正所谓“发乎性情,由乎自然”。他说:“古之和歌,可谓自然成格调。惟用意而始成格调之说,实大谬矣”(《新学异见》)。其意是说和歌创作要反对人为的雕饰,推崇诗境的浑然天成,反对以理入诗。
在《歌学提要》中他说:“古昔之和歌在于格调与诗情兼备,而非为他义。人之真情发自诚实之心。因诚实之心而生成之和歌便为天地之格调,如风吹空物成天籁之音一般。风的存在因声响而得到证明,同理亦然,人的诚实无瑕之心也可通过体格声调得到表现。所以,当人的所见所闻或悲或喜,诗兴大发欲托物言志之时,因触景生情,柔情、感慨、悲怆之情愫瞬间涌上心头,而不加任何矫饰将这所谓‘初一念’表现出来便是一首绝佳的诗歌”。这种柔情感动就是香川景树所说的“诚实”,它泛指人类一切美好的情感,他认为通过诗歌的格调(声韵)可以表现出来。
正宗敦夫在《桂园一枝解题》(岩波文库)中评价香川景树时道:“在德川时代的私人和歌集中,不,即使对我国的和歌集整体而言,也没有几部可出其右者。”佐佐木信纲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格调的视角来整体概括歌学理论,简洁明了。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启蒙之物,极其有功。”香川景树用他的这套歌学理论指导众多的门徒,将《古今和歌集》的雅正歌风视为理想范式,把原本贵族化的和歌创作平民化,并使之风靡了当时的江户时代,扩大了创作队伍的范围,而且主张抒写性情,个性解放,将诗歌创作脱离了诗教伦理的束缚,为近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埋下了合理的内核。
在江户后期,围绕“格调说”,展开了一场论战,通过各诗歌流派间的争论,取长补短,人们对诗歌创作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和拓展。香川景树的学生内山真弓在天保十四年(1843)写成《歌学提要》一书,对香川景树歌论进行了一定的概括,整合了香川景树有些零散的甚至矛盾的理论体系,并有所发展。内山真弓认为诗歌是一种“嗟叹之音”,其“格调”主要是指格律声调,它是诗人情性的自然流露,因此只要是真情实感的表露,那么无论其词采优劣均可称为雅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和歌是语言的一种“精微之物”。我们认为内山真弓是根据香川景树的“格调”说而下此定义的。内山真弓认为和歌的雅与俗不在于句章词藻,而在于具备音调声律的诗歌是否出自真情,只要诗人是一个诚实之人,不矫情造作,而是“为情造文”,不拘泥于技巧与创意,就眼前情景有感而发,直抒怀抱,其诗境便可浑然天成。不过内山真弓的理论也有牵强之处,如他认为和歌创作不能有虚构,不能使用技巧,将俗语俚语入诗。这都难免使诗歌显得过于直白,索然无味,有因噎废食之嫌。
八田知纪(1798—1873)也继承了老师香川景树的学说,并有所创新。其主要著作有《格调之直路》,卷首即开宗明义:“和歌者乃歌咏人情也,非为说理。其格调惟真情流出,方合天赋自然之道,些许私意难入其中。师曰,离格调者,则失感哀之情,亦失歌之妙用。和歌者终究为咏嗟叹之音。喜悦之音闻之可感,悲哀之音闻之可悲,闻者皆可感之,姑且称之为格调。歌咏时,喉音多之和歌,其调高吭而尽兴”。天保八年(1837),他在《格调之说》中说:“欲咏诚之歌则无真心不可。其调者,属天赋自然独具之道,非由其外部所习得。然世风日下,言灵之道式微,不得已而姑且借修行工夫之手段,亦可明诚之道。雅调中有第一义与第二义者,风体(体裁形式)上的格调为第二义,嗟叹之音所引起的共鸣者方为根本。此真诚之音才是和歌之要旨,且和歌之境界可分为三,即天、修行地、病名门”。“天”是指天赋自然的真歌,浑然天成,不加矫饰;“修行地”是跟随师傅达到天的境界的途径;“病名门”则是过分注重学问而生出的弊端。
针对桂园诗派的主张,江户诗派进行了反驳。1802年,贺茂真渊的弟子村田春海与加藤千阴著《笔之性》,对香川景树的《和歌十一首》展开了批判,他们认为和歌应避免庸俗,而要追求风雅的风格,对香川景树诗作中的俗情俚语进行了讥讽;不久,小泽庐庵的弟子小川布淑著《雅俗辨》为香川景树进行辩护,他认为和歌无论是从表现的情感、内容,抑或是从表现的方式上来看,都不应该有雅与俗的对立,要根据所表现的内容,有选择地使用或雅或俗的语言形式,不能因为形式通俗就认为诗歌不好。而为了表现没有世俗功利性的真情实感,使用不同于今日的古昔文雅之词语,这就是“雅”。对此,村田春海在第二年著《雅俗辨之答》进行了反击,他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诗的词语表现,所谓“雅”即是指词藻富有文采,神思巧妙且具有情趣,虽然不应过分追求修辞华丽,但也不能不加修饰而过于直白,小泽芦庵提倡的“直言歌”(直抒胸臆)也只不过是和歌的一格而已,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另一位国学大师平田笃胤(1776—1843)的诗学思想也值得一提,他在吸取前人的基础上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其门人所写的《歌道大意》一书中。其思想的核心是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他站在国学者的立场上认为通过学习国学,使人在创作和歌时能“知晓诚之道”,和歌的本体是感物兴会,缘情而发。孔子说质胜文则史,文胜质则野,要文质彬彬,说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样道理,平田笃胤认为“雅”即指文采,和歌要五、七、五的格律音韵,这就是古人的和歌在今天仍有感染力的原因。通过“风雅之情”(和歌的情趣等方面)才可得“诚之道”。关键在于和歌要表现人的真实情感,墨守成规的“古今传授”是不足取的,而且将伦理道德、政教功利引入和歌创作也是错误的。男女爱情是最真实的流露,为了更好地表达真情实感,虽俗言俚语也可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