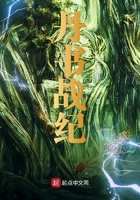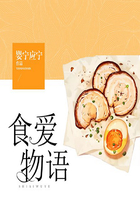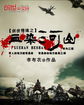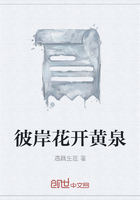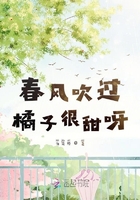(五)大隈言道的歌论
大隈言道(1798—1868)的观点来自对小泽芦庵、香川景树等人的现世主义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在他的歌论著作《去年之尘》(1839)中亦有所体现,这也来源于其老师广赖淡窗的学说,即注重实情实感,尊重个性的张扬。他继承了香川景树的学说,认为和歌是由“真心”流露出的“嗟叹”之音,在创作表现上主情贵真,反对摹拟古人。
大隈言道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日常身边事,视角独特,语言上采用俗言俚语,风格轻妙洒脱,有一种传统和歌中所没有的清新气息。他的主要歌论著作《独言》,为松散的诗话形式,他认为当时的人们因循守旧,受囿于古人、古歌,所创作的和歌并非真正的和歌,生于天保时代的人在创作时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要创作反映这一时代生活的作品,他有一句著名的话,“生于天保时代的人应写天保时代的世风民情,生于福冈的人应该写福冈地区的人事”。换句今天的话说就是艺术的创作不能脱离实际的生活,这在那个时代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大隈言道认为《古今集》序中关于和歌本质的论点“以心(情志)为种”,“感物而发之咏叹便是和歌”等,他认为无论任何时代这都是不变的真理,应立足于此,适应时代的要求进行可贵的创新,注重个性的提倡。他说:“人有千面,和歌也因作者不同而不同,人的性格就像松、竹、柳、梅,各为不同,不应任意改变,如教的人搞错了,将学生的柳之性变成松,将竹之天性变成梅;而学的人也认为理当如此,自己身上有优点,同时也有缺点,如不加分析地硬要改变它,这都是非常不应该的做法。”此外他还认为注重真实并不是一味地只要真实便好,那样的话就过于偏执,容易流于浅陋、空疏。所以当须认真之时要严肃,而应活泼之时则可出戏言,不要墨守成规,要给想象的翅膀松绑。和歌是“即物而发之咏叹”,所以没有时间去计较用词之新旧,不应好古而薄新,在遣词造句上可大胆创新,并且主张以周围熟悉的事物为创作题材。
江户中后期在诗歌理论方面流派众多,贺茂真渊代表的复古派和以小泽芦庵、香川景树为代表的现实派的对立,但在反儒家功用主义诗学的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只是贺茂真渊的县门一派以质朴雄浑的万叶歌风为审美理想;香川景树的桂园派则推崇平淡清丽的古今集歌风。这如同明清时期关于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论一样,只不过是对审美风格的喜好不同而已。但客观上两派的论争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他们相互取长补短,更加完善了日本的和歌理论。
四、反朱熹理学的古文辞派
除了日本国学思想外,儒学中的古文辞派也举起了反对朱熹理学的大旗。伊藤仁斋(1627—1705),古文辞派的创始人。早期的伊藤仁斋倾心于朱熹理学,后对朱熹理学产生怀疑,写成《儒学古义》、《孟子古义》、《中庸发挥》等著作,对朱熹理学进行批判。他认为朱熹的理学是借佛教道教思想对孔孟之道的解释,将孔子主张的道德实践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空泛之说。
伊藤仁斋主张不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验证和体验。他是以“道人情论”作为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对宋儒朱子学有违人情的论点持批判的态度。一是反对朱子学将人性分为“本然性”(天理)和“气质性”(人欲),以及它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二是反对朱子学将善恶作为对立面的见解,主张复古孔孟之道,将“仁”解释为爱,辅以“礼义”,以“忠信”为根本,以此来调和善与恶、天理与人欲的矛盾。他提出文学的“道人情论”,以“真”为本,以此贯于人的性、情,心,并辩证地解释三者的关系,即将心分为体用两面,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而心统辖性与情。心真,性与情亦真。其子伊藤东涯整理他的这一学说时,也反对朱子学把善、恶作为对立面的见解,并对性、情、心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心、性、情三者,人必有之,本无善恶之称。(《辨疑录》)
其子伊藤东涯在解说他的学术思想时,反复说明情是人之真实心,“《礼记》礼运篇的七情,即喜怒爱恶欲等七者,不学而能,好善厌恶也是真实心的话,那么好色嗜食也是人心之真实”(《训幼字义》)。由此,他强调学问要重活道理,不要守信理,即不以道德为目标,而努力追求人的自由发展,积极定人性、人情、人心的真实性。他的弟子中江岷山进一步解释:“圣人之道人情而已。异老佛以人情为恶。圣人以人情为善,顺善而尊之。此乃圣人邪说之所以由分也。夫人伦之以立者,以人情也。人生不能无情,是以圣人顺人情以教之也。”(《理气辩论》)
伊藤仁斋的学生荻生徂徕(1666—1728)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的学说,并有所发展。荻生徂徕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学家,他除了有所侧重地传承古学的精神之外,还受到中国明代拟古派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影响,他明确提出了以古典作为写作规范,恢复和发扬以《万叶集》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中反映出的未受到外来思想毒害过的大和精神。荻生徂徕肯定了人性的自然属性,他主张“人情论”,认为文学的意义全在于“主情”,为此他对林罗山为首的朱子学派主张的劝惩文学思想进行了批驳。
在这一点上,荻生徂徕与伊藤仁斋相同,他采取人情论的立场,强调诗是艺术,是以艺术表现人情之微妙。所以他主张文学是叙述性情,涉及人的情趣,而不在理论上解释义理和涉足人伦之道。他在《徂徕先生问答》中说:“认为诗歌是为了劝善惩恶之目的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想达到劝善惩恶之用意,诗歌之外还有许多更合适的形式。”其次,他在表现论上更重古典主义,主张尽人情世相,以尊重表现的体与格,即重修辞。他认为语言因时代变迁,“近言”(即今天的语言)与“古言”即(昔日的语言)不同,所以不像宋儒那样用“近言”来解释“古言”,而是主张要通过古代的独特修辞法来表现。他说:“辞者言之文者也,言欲文,故曰尚辞,曰修辞,说文以定言。”(《与平子彬书》)
五、本居宣长与“物哀”思想
本居宣长(1730—1801)提出了著名的美学理论“物哀”学说。本居宣长是在谈小说《源氏物语》时提出“物哀”说的(《源氏物语玉之小栉》)。他认为“物语”(小说)的本质在于:“物语之主旨为使人明晓物哀之本意而著也”,显示出其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思想。这种审美范畴后来被广泛地应用到各种艺术领域里,例如和歌、俳句、戏剧、绘画等等,“物哀”构成了日本审美意识中最具传统性的理论内核。
本居宣长所言的“物哀”表现出来的意象多具有哀婉阴柔,纤秾美艳,朦胧缥缈,极具唯美特征。“物哀”中的“哀”早在日本古代歌谣中就已出现,原本是对人或事物表示赞赏、亲情、同感、哀伤等感情时而发出的感叹语,类似我们古人发出的“呜呼哉”,后来演变为可以表达各种情感的抽象词语。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当人们无法用语言准确说出内心的感受时,或者当某事物触动了人内心深处的哀怜或怜悯等复杂情感的纤细神经时,“哀”便用来表达委婉情思的心绪。而“物哀”中的“物”是一种构词法的前缀,它接在“哀”的前面,泛指一切能引发“哀”感的世间万物,它类似于一种触媒,“哀”便油然而生。
“物哀”一词最早见于小说《源氏物语》,原意是指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内心世界。《徒然草》第十九段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惟四季变换者,令人哀时伤事,如人所言物之哀者莫过悲秋者。彼虽如此,而今内心喜悦则正因春色而起”。“物哀”中的物指一切自身以外之世界万物,也可指他人。当自己观察某种对象时,所引起的种种悲喜情绪都称作“物哀”。这在《诗品》序中也有类似的内容,“气动物,物感人。故性情摇荡,形诸舞咏”。但是钟嵘是谈风的意义和作用,其用意在于“风化”、“风刺”等道德内容。此外,“物哀”与刘勰的“物感”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只不过“物感”说属于诗歌的起源论,而“物之哀”则是文艺心理学的范畴。
“物哀”一词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见到用例,如纪贯之的《土佐日记》,“舵取り、物の哀れを知らで、おのれ酒をくらひつれば……”表现的是临别时朋友们互相吟诗作歌表达惜别之情,然而艄公却不解风雅,独自一个人只顾饮酒。我们可以推测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之间,“物哀”很可能是一个具有高雅脱俗等含义的日常用语,如果有谁不懂“物哀”,便会被讥笑为不解风情、不懂情调,便进不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圈,而且懂“物哀”者也自然会咏歌作诗。反之亦然,能作歌吟诗者也必懂“物哀”,也即是“知物哀”,但这时的“物哀”带有一种肤浅的华丽色彩。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1)后,这种符合贵族审美情趣的“物哀”与佛门的无常思想结合,形式的华丽色彩开始消退,转而多了些深刻的思辨与书卷气。至于江户时代的净琉璃(木偶剧)及小说中的“物哀”,其含义仅是一种对他人的体贴与同情,是普通日本人对“物哀”的通俗理解。
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论之后,它才真正成为文艺批评用语,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本居宣长的《源氏物语玉之小栉》中,“哀”与“物哀”还未能区分开。宝历八年(1758年),在其另一部著作《安波礼辨》中,本居宣长说:“哀与物哀之语意深长且多歧义,盖歌道者可由物哀一语蔽之,无余意可出其外者。至神代及今,更可及末世无穷,所吟之和歌皆可归于物之哀一语矣。然问及此道之极旨,则又无出物哀一语之外矣。”也即是说和歌的所有存在意义都可用“物哀”一词来概括。此外,本居宣长又认为:一切和歌皆因懂物之哀者才创作出来,《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皆是为了写“物哀”,并且为了人们知晓“物哀”而创作的。而缠绵悱恻的男女恋情往往成为表现“物哀”理念的绝佳主题,在小说《源氏物语》中“物哀”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人生的诸多情状,尽现于恋情中,苦涩、悲伤、怨悱、愤怒、有趣、欣喜等皆有之。若舍却恋情,则人情之诸多深细处,物哀之真髓,皆难以显现。”
早在数十年前,契冲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在《源注拾遗》书中道:春秋的褒贬是善人写其善行,恶人写其恶行,若人们知道了其恶,则作者的目的便达到了,此为劝善惩恶。然而此物语(指《源氏物语》)中的人物一人身上有善有恶,善恶相掺杂,岂可将此书与春秋之史书相提并论?他认为文学应有文学自身的价值与特点,否定了儒家功用主义的诗学观。本居宣长在宝历十三年(1763)论《源氏物语》的《紫文要领》以及和歌论《石上私淑言》等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物哀”。根据本居宣长的观点,凡天地间万物,皆有其灵性,即“有物”,知其者便与知“物心”与“事心”者同义,即是深刻地理解对象事物的本意,并与之处于一****感的关系。故感人心之深者皆可曰物之哀也。“应物斯感,可识其或喜或悲之情者,可谓知物之哀矣”。而“不识物之哀者,便是无心之人”(《源氏物语玉之小栉》),他认为读《源氏物语》就是为了懂得“物哀”。按照吉川幸次郎的解释,所谓“知物哀”,就是通过感动这一心理活动,认识事物存在的本质的一种行为,也是一种能力。
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在和歌与小说之间是相通的审美范畴,他从荻生徂徕、堀景山的诗论及契冲的歌论中受到了启发,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中世以来将《源氏物语》作为歌学研究对象的学术传统。但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又具有独特性,它将文艺创作从儒教、佛教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审美价值体系。
六、“劝善惩恶”思想
(一)“劝善惩恶”思想的起源
“劝惩”说发源于平安时代的小说《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提要》的作者今川范政、《细流抄》的作者三条西实隆等人认为《源氏物语》的创作目的在于“劝善惩恶”。但我们认为《源氏物语》中的“劝善惩恶”与诗教无关,它更多的讲述了佛门的宿命论与因果报应思想,这在短篇小说集《今昔物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劝惩”思想不同于中国的“劝惩”思想。“劝善惩恶”一语出自《左传》:“春秋之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真正意义上的“劝惩”说则出现于《诗经集传》序中,朱熹认为:“人心感物而言形为诗,心感有邪正,故言形亦有是非”,孔子删诗是为了“思无邪”,“得性情之正者可以足教,而不合者则足以为戒”。我们从这里丝毫看不出佛老思想的影子。
进入江户时代后,在林罗山、熊泽蕃山以及安藤为章等人的大力提倡下,“劝善惩恶”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的主流意识。林罗山是日本“朱子学”的首倡者,主张用新儒教来规范日本人日常的行为,在文学创作上坚持“文以载道”的诗教说,他认为载道的最大目的就是“劝善惩恶”。所谓“有道者有德,有德者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道德。四书五经谓之道德文章。学者习之哉”(《林罗山先生文集》第66卷)。林罗山将文学与道德伦理混为一谈,给文学增加了“劝惩”和“载道”两大重负,将道德放在第一位,文学放在从属的位置,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功用主义诗学思想。如他以此为衡量标准,将小说《伊势物语》说成是“****之物”;讥笑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是“喔咿嚅叽之语,冶容粉妆之态”(《徒然草野槌·序》)。
虽然林罗山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但他也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说:“凡作为文章,无常师,唯以古文为师。夫道德者我实也,文章者我华也。华也者史也,实也者野也。华实彬彬,然后我文我道,无蓁塞。谓之君子之文章矣。”(《林罗山先生文集》第66卷)也就是说好的内容要有好的形式来表现,词采华美,劝惩才能收到好的教化效果。从这一点来看,林罗山是出于政教目的,才将政教与审美结合在一起。
熊泽蕃山(1619—1691年)是另一位政教思想的鼓吹者,他接受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任职于冈山藩,政绩斐然,后因树敌太多而隐退。主要著作有《息游先生谈》、《三轮物语》、《源氏外传》、《雅乐解》等。写于1677年的《源氏外传》是他为《源氏物语》写作的评论,集中反映了他的儒家功用文学思想。他说,《源氏物语》表面上是写男女恋爱的小说,然而实质是在宣扬名教的经世致用思想,即所谓的“通达人情”。紫式部借写“好色之事”,欲表现古代礼乐之雅正、民风之淳美。例如,小说中的主人公光源氏没有因为末摘花(人名)的貌丑而抛弃她,熊泽蕃山认为作者这样写是为了表现光源氏具有仁爱之心。这与汉儒曲解《诗经》,将表现男女爱情的诗篇解释成臣子对君王的怨刺讽谏的做法如出一辙。
安藤为章的诗学主张与熊泽蕃山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体现在对《源氏物语》的评论中。小说评论《紫家七论》(1703)是实证研究方面的先驱,其对小说《源氏物语》及作者紫式部进行的研究,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捕风捉影式的旧观点,对紫式部的生卒及小说的成书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种实证式的研究意义重大。他指出《源氏物语》的真实意图并非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佛门的因果报应,而是借写虚幻的男女****来告诫女人应警惕爱情的陷阱,用日本社会的公序良俗进行道德说教。比如,他以为桐壶帝宠藤壶,成为天下之讥讽,以此来讽诫后人;源氏与继母藤壶私通,其报应是源氏之妻三公主与柏木私通生下熏君等,无不贯穿劝惩用意。这与熊泽蕃山所著的《源氏外传》有相通之处,但安藤为章所作的实证式研究则更胜一筹,他为后来的小说实证研究提供了借鉴。安藤为章的《源氏物语》评论是在儒教道德容许的情况下,将“慰み”(娱乐)作为恶(恋爱)与善(道德)的调和剂,通过调和两者,来达到寓意劝善的目的,这就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用安藤为章本人的话来说,《源氏物语》是“不以美辞表现而使读者判明善恶”。安藤为章不承认文学本身的价值,他将文学从属于道德和历史,过分注重内容的伦理性,而且用适度的“娱乐”形式加以表现,但这样做将有导致轻视甚至否定文学艺术价值的危险。
(二)曲亭马琴与《八犬传》
曲亭马琴(1767—1848),又名泷泽马琴,是真正将劝善惩恶思想自觉地应用到创作中且影响巨大者。曲亭马琴在《八犬传》序跋以及其他文章中所表述的劝惩主义文学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警世说
他将小说创作的目的放在“警己警人”上,尤其是首先放在警醒妇孺上。他认为稗史虽无益于事,但寓以劝惩,妇幼读之也无害,而稗史可看之处,也在于劝惩。警醒妇孺,去恶扬善。
2.善美说
马琴的“劝惩”思想的核心是“善”,强调善与美的一致,其次是强调善美与真的统一。强调有善才有美,有善美则无丑恶。他承认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关系,最后通过因果报应来扬善弃恶,这在小说《八犬传》中被具象化了,比如仁义礼智等伦常观念化身为八位剑士,通过八位武士的种种义举来进行道德说教。
3.****有害说
马琴重视文学的功利目的,而忽视文学的感情效果和审美作用,使感情受到道德的束缚,视****为邪淫,视****小说为有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德教功能。可以说,其功利的目的说,是其劝惩文学观的基点。因此他指责《源氏物语》时说:“紫家才女之书,虽为和文之规范,但有堕地狱之痛悔,乃关乎****玷污也。况后世诲淫浮艳之谈,于读者有害,作者应慎而慎之。由此饭台曲亭翁,尝耽于著书。每岁著小说,皆以劝惩为本。”(《石言遗响》)
4.戏作说
马琴将劝惩作为文学创作的第一义,只承认文学的“慰み”(娱乐)的意义,而不承认文学本身的价值,所以他认为自己戏墨是读书之余乐,不是他的真正的事业,而是赖以糊口之计和用以购买其所需要的书籍。他还认为文学创作并非是个好的技艺,劝其徒勿浪费光阴做此无益的游戏。他说:无劝惩之意,就不是戏文。(《曲亭传奇花钗儿》)
现代日本学者久松潜一认为:“人生是善与恶交错的现实,应作为一切表现的对象。表面支配近世生活的狭隘的道德观,视恋爱为罪恶,那么以劝善惩恶思想来作为调和两者的手段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即使描写恶,描写恋爱,也是通过它来寓劝惩之意。这在道德上是容许的。”
“劝惩”文学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它过分夸大教育功能的作用,将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道德的载体,形而上地对待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分割了真善美三者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尤其是在诗歌的创作方面,“劝善惩恶”思想受到了注重审美价值的“物哀”文学思想的激烈挑战,渐渐失去了影响。
(三)“劝善惩恶”思想的终结
北村透谷在《明治文学管见》一书中指出明治文学分裂成两部分,一是在儒教伦理的束缚下以实用主义为目的的武士文学;而另一部分则是追求精神自由和享乐的市民文学。北村透谷所说的“实用”与“享乐”之间的对立可以用劝惩主义的文学观与人情论的文学观之间的对立所替代,坪内逍遥通过发表《小说神髓》一书,宣布了人情论的文学观的最终胜利,他说:“小说的主脑乃人情也,世态风俗次之”。中村幸彦认为日本近代文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情论逐步战胜劝惩论的漫长历程。
以“人情论”(缘情说)为代表的文艺思想源自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人,随后又经过上田秋成、与谢芜村、为永春水等人的努力,渐渐地开始取代标榜劝善惩恶的功用主义诗学。“人情本”(言情小说)作家为永春水在《春色梅儿誉美》中说:“予著草子(小说),大都以妇人读者为对象,其言语拙俚自不必言”。他的小说多描写哀伤凄婉的爱情悲剧,借此表达一种平民百姓所理解的将“物哀”美学通俗化的处世哲学,同时也折射出一种游离于儒教伦理道德之外的市民阶级追求享乐的正当欲望。然而天保改革借对风俗的整肃之名,对市民文化的奢华进行了压制,戏作文坛中的代表人物为永春水等人受到了迫害与摧残,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被斥为“败俗之书”而受到禁毁,天保十年(1839)还发生了维护程朱理学、打击各种革新思想的“蛮社之狱”事件。
1868年,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至上而下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明治初期是日本近代思想的启蒙期,经过了福泽谕吉、西周等人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引发了对封建主义文学思想的清算,“人情论”及“游戏说”盛行,加之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也引发了文学界的大变革,但一直等到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的问世,日本文学才彻底摆脱封建文学思想的束缚。此后各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接连传入日本,日本诗学也迎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