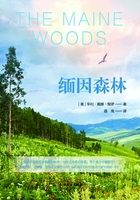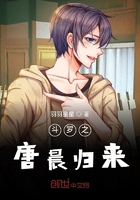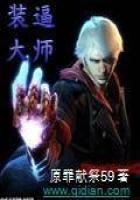这段话是针对柏拉图说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攻击史诗,说荷马描写的英雄阿喀琉斯性格暴躁,降低了英雄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荷马刻画的阿喀琉斯的性格惟妙惟肖,又予以了美化。
亚里士多德的“美化”,绝不是粉饰现实,把丑恶写成美,或宣扬现实中的丑恶。“美化”是指“理想化”,即通过艺术的摹仿使艺术的形象比实际生活更有集中性,更有普遍性。古希腊名画家宙克西斯曾把希腊克罗通城邦里最美的五个美少女召集在一起,画成他的名画《海伦》,亚里士多德对这种做法大加赞赏,认为这幅画既有现实的依据,又远比现实更美。他说:“这样画更好,因为画家所画的人物应比原来的人更美。”(《诗学》,第101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的目的绝不仅在于忠实地临摹自然的对象,而在于创造艺术形象。每一个别的东西都是物质和形式的结合、普遍和特殊的统一,艺术形象的功能在于通过特殊体来表现普遍性,宙克西斯所画的美人像不是表现个别的美女,而是表现女性美的普遍性,所以形象须优于现实。再者,一切事物形式上的有机整体性,实际上是它的内在发展规律的反映。按照当代系统论的理解,整体就是一个系统,可以看作是具有一定内在逻辑结构的各个部分的组合。亚里士多德当年已经朦胧地觉察到这一现代科学的原理了。他说:“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在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体。”他在《诗学》中更加明确地指出:
一个美的事物——一个活东西或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不但它的各部分应有一定的安排,而且它的体积也应有一定的大小;因为美要倚靠体积与安排,一个非常小的活东西不能美,因为我们的观察处于不可感知的时间内,以致模糊不清;一个非常大的活东西,例如一个一万里长的东西,也不能美,因为不能一览而尽,看不出它的整一性。
(《诗学》,第25—26页)
限于亚里士多德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当然不能从系统论的概念出发来论证他的有机整体性,而只能认为整体就是一个有头有尾有中间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在整体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并且不能随便变更秩序。这样紧密衔接的每一部分,从而显得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内在的合理性,这种结构就是美的。亚里士多德运用有机整体概念分析了希腊戏剧和诗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诗学。例如,关于诗他是这样说的:
在诗里,正如在别的摹仿艺术里一样,一件作品只摹仿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
(《诗学》,第28页)
(四)摹仿与悲剧、喜剧及传统题材
上文在讨论柏拉图时,我们已提到悲剧的起源,随着不断增生新成分,悲剧不断提高,直到发展出它自身的本质形式。公元前6世纪末,悲剧题材内容不再限于酒神故事,大多取材于荷马史诗、神话与英雄传说。从希波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希腊悲剧尤其兴盛,得到重大发展,以不同方式深入表现希腊人的现实生活,全面涉及命运、宗教、战争、民主制、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等内容。戏剧演出成为希腊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典古典时期悲剧名家迭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将希腊悲剧推进至辉煌峰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已发展出“本质形式”。希腊悲剧发展到欧里庇得斯,从神话英雄到尘世现实,从相信命运支配到认识人自己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正是人的摹仿天性即认识社会现实和人自身逐步实现、不断提升的结果。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悲剧发展中不断实现人的美感天性,摹仿手段与方式即艺术美的形式不断改进,人的审美能力得到提高。从酒神颂的单人即兴编诗答话,到悲剧根据诗人创作,由演员、歌队表演剧情完整的故事,演员人数增加,缩短合唱,对话成为表演的主要手段,并引进舞台布景,悲剧规模变得宏大,成为庄重的综合性艺术。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具有比史诗更多的艺术成分,如音乐、扮相等等,能使人体味“强烈生动的快感”,能以紧凑集中的情节、节省的时间达到摹仿目的,取得更好效果。他说,史诗成分悲剧皆有,而悲剧的成分,不尽出现于史诗中。“悲剧优于史诗,因为悲剧比史诗能更好地达到目的”(《诗学》第二十六章)。
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体现了人的摹仿和美感天性、审美能力不断进化。喜剧的希腊文komodia,原意是“狂欢歌舞剧”,古希腊喜剧起源于收获葡萄时节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公元前6世纪初,它已演变为表现神话故事和日常生活的滑稽剧。至希腊古典时期,喜剧兴盛,表现了比悲剧更为自由的创作手法,有种种政治讽刺剧、社会讽刺剧。关于喜剧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喜剧务求摹仿比今人为劣的人,并不是说喜剧是丑化现实的。他说:
如前面所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
(《诗学》第五章)
至于摹仿历史的或想象的现实,比如传统的题材,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应该有自由处理和有自由创造的权利。他在《诗学》的第八、九、十四章等处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荷马在写《奥德赛》时,“并没有把俄底修斯的每一件经历,例如他在帕耳那索斯山上受伤,在远征军动员时装疯(这两件事的发生彼此间没有必然的或可然的联系)都写进去”(《诗学》,第27页);对于传统的野史,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不应该随意篡改,应巧于运用传统题材:“流传下来的故事(例如克吕泰墨斯特拉死在俄瑞斯忒斯手中,厄里费勒死在阿尔克迈翁手中)不得大加变动。不管诗人是自编情节还是采用流传下来的故事,都要善于处理”(《诗学》,第44页);诗人“即使他写已发生的事,仍不失为诗的创作者”(《诗学》,第30页)。上面的论点告诉我们三点:一是去芜存菁的艺术提炼;二是说既要保存野史题材的要点,又必须有所创造;三是说历史事迹虽然杂乱无章,但是诗人可以经过处理而咏之于诗。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对待传统题材可以自由处理,而且应该有所创新。古希腊悲剧创作的实践,证明了他的论点。所谓“自由处理”,并不是说诗人可以任意篡改历史或事实,或者毫无根据地想入非非,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标准:情节必须合乎或然律或必然律,即必须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诗人认识了现实中事情发展的或然性或必然性,才能有处理剧情的自由。
(五)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摹仿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可以说是对柏拉图的反驳,美国文论家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诗学》就是针对柏拉图的论调写的部分答辩。”这个结论有些过于绝对。我们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中,不仅有自己的全面论述,而且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摹仿概念与柏拉图的摹仿相似,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在广义层次上,柏拉图的摹仿是哲学名词,一切事物的运动程式都可以与所意欲相似的对象建立摹仿关系:艺术、建筑、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有摹仿的存在。柏拉图在拒绝诗人进入城邦时,就夸赞自己的城邦是最好的摹仿。同样,亚里士多德的摹仿也有广义的用法,他的名言“艺术(技艺)摹仿自然”指的就是广义的摹仿,含有艺术与自然、技艺与自然并存,技艺可以起到自然所不具有的作用的含义。狭义的摹仿专指诗和戏剧的创作,柏拉图在使用这一层含义时,除了诗和戏剧的创作外,偶尔提到演员或其他人员的表演,包括一些取乐式的行为,这是他的一个贡献。虽然他的本意是对这些行为的贬低,却在历史上较早地把表演纳入艺术研究的范围,也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亚里士多德在使用狭义的摹仿时基本上与柏拉图是同一概念……他在讨论诗学问题时是与柏拉图进行无形的对话,沿用基本相同的概念是必须的。”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说的摹仿,有技艺摹仿自然的宽泛含义,而在《诗学》中,它是一个特定的美学范畴,指在“诗”这种创制技艺(艺术创作)中,表现人和人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包括一切艺术活动,“摹仿者”就是艺术家,这是亚里士多德特有的术语。柏拉图则没有这样的划分,例如,他常常把诗的艺术和烹饪的艺术相提并论。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扩大了“摹仿艺术”的范围。柏拉图把叙述的诗分为史诗、剧诗、颂歌三类:在史诗和剧诗中,诗人可以不用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是代表诗中人或剧中人讲话,即用直接叙述法,他称之为“摹仿”的诗;在颂歌中,诗人则完全用自己的身份说话,简单地叙述故事,即用间接叙述法,柏拉图称之为“非摹仿的诗”。亚里士多德认为,把诗分为“摹仿”的诗和“非摹仿的诗”在方法论上是不妥的,他首先用“摹仿”概括一切的诗:“这些艺术的第三点差别,是摹仿这些对象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假如用同样媒介摹仿同样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诗学》,第9页)显然,亚里士多德把颂歌也包括在“摹仿的诗”之内,扩大了摹仿艺术的范围。
在诗歌要不要反映现实的问题上,柏拉图的回答是矛盾的,他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文艺作品作为“影子的影子”,对现实世界应加以选择。人类的情欲,奴隶、妇女等等,凡属“丑”的东西不能摹仿,而那些能透过现实看到“理念”的现实,还是可以摹仿的,这个现实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神的意志的“磁”性传播。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不可靠,现实世界才是客观存在的,是第一性的,文艺是第二性的。“理”在“事”中,离“事”无所谓“理”,所以文艺应该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至于诗歌如何反映现实,这是亚氏和柏氏“摹仿说”分歧的关键所在。柏拉图所理解的摹仿只是感性事物外貌的抄袭,而且这种抄袭应有所选择。在《理想国》卷三里他向诗人们下了一道逐客令,如果有一位聪明人有本领摹仿任何事物,就要客客气气地把他赶出理想国。应注意的是,柏拉图的选择并非典型概括,而是站在贵族立场上的选择,在他眼里的美丑已深深打上贵族的烙印。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认为现实中的美丑皆可摹仿,关键是摹仿应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和规律,使现实丑变美,使现实美变得更美。诗的灵魂在它的内在逻辑,要表现出某种人物在某种情境的所言所行,都是必然的、合理的,具有普遍性的。这就替典型说打下了基础,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对诗学思想的最大贡献。
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的定义与诗的真实性
(一)诗的定义:诗是一种技艺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技艺。他曾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6卷中指出,“技艺就是一种创造活动”。他说:“营造术就是一种技艺,而且是创制的理性品质。如若不具备理性品质,创制也就不是技艺,这种品质不存在,技艺也就不存在。所以,技艺和具有真正理性的创造品质是一回事情。”正是基于技艺是一种理性的创制活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认为,诗并不完全依赖于灵感、直觉和幻觉,它也是一种理性的技艺活动。在《诗学》第一章的第一句话里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他所要研究的是诗歌的艺术即诗的技艺本身。诗的技艺本身就是指诗艺。在《诗学》里,poietes(制作者)是诗人的标准用语,而一首诗是poiema(制成品)。显然,亚里士多德把写诗歌视作一个制作或生产过程。诗人作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二者都凭靠自己的技艺,产生或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诗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属于理性创造的技艺——诗。“这样,与柏拉图把诗归于非理性的产物,从而否定诗相反,亚里士多德从理性的立场为诗辩护,把诗纳入了属于理性创作的技艺活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说的诗(创制技艺),不仅是指诗歌这种体裁,而是包括了史诗、悲剧、喜剧、酒神颂等当时古希腊所有的文学种类。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从不以单纯的戏剧家称呼古希腊作家,而总是要么以诗人相称,要么以悲剧诗人或喜剧诗人相称。他把当时一切种类的文学作品均归之于创作技艺这个类属。上一段我们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他在此书中要讨论的是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对技艺的划分方法,他将技艺分为两类:一类与人的行动有关,另一类与人的制作有关。制作又分为两类:一类产生各种器具和用品,另一类则以声音、节奏、音调、语音和色彩等摹仿自然和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和音乐都是一种利用特殊方式摹仿自然与生活的技艺,它们与农业、医术以及生产各种器具和用品的技艺的根本区别在于摹仿。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诗人与摹仿者是同一语。亚里士多德“摹仿”的真实含义,应是艺术对大自然创造过程本身的摹仿。这实质上是艺术家以出自心灵的形式之于创造材料的实现过程。《诗学》中关于诗的真实问题根本上不是诗人对现实反映的正确与否,问题在于诗人将其形式之于材料的实现方面是否达到整一、和谐,以体现出诗自身内在构成的可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二)诗的真实性问题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关于诗的真实性观念是建立在他的美学与诗学的核心概念——摹仿之上的。在《诗学》第一章,亚里士多德就将诗的本质规定为摹仿,即艺术摹仿大自然的创造过程。诗的创造目的在《诗学》中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诗人如何使形式实现得充分、完美;一是实现了的形式如何具有自身完善功能的目的,从而使悲剧去发挥悲剧应有的特殊情感效应,使史诗去产生属于史诗自己的审美功用。亚氏《诗学》中的主题可以说基本上是这两方面。
在亚氏看来,诗的真实与否的依据不是外在于诗的,不是以诗中的为形式所实现了的材料(人物、事件、细节等等)是否与诗之外的现成之物符合为准则;而是内在于诗的,是以形式是否完美实现于材料之中,是否能完善发挥诗的自身功能为准则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十五章中指出:“衡量诗和衡量政治正确与否,标准不一样;衡量诗和衡量其他艺术正确与否,标准也不一样。”这句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诗的真实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真实性是有区别的,虽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点。柏拉图指责诗人,说诗人缺乏专门技术知识,不知军事学而写战争,这是以自然科学的真实来要求诗。亚里士多德有针对性地指出:
在诗里,错误分两种:艺术本身的错误和偶然的错误。如果诗人挑选某一件事物来摹仿……而缺乏表现力,这是艺术本身的错误。但是,如果他挑选的事物不正确,例如写马的两只右腿同时并进,或者在科学(例如医学或其他科学)上犯了错误,或者把某种不可能发生的事写在他的诗里,这些都不是艺术本身的错误。
(《诗学》,第92页)
诗人不能在专门技术知识上犯错误,但即使偶或有错误,那也不是本质的错误,不能以此来抹杀诗的价值,因为诗的真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真,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真。因此亚氏认为“偶然的错误”与诗的真实性与否关系并不大——“不知母鹿无角而画出角来,这个错误并没有画鹿画得认不出是鹿那么严重”(《诗学》,第93页)。由于“偶然的错误”并不有悖于艺术创造的目的,他认为:“如果他这样写,达到了艺术的目的,能使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诗更为惊人,那么这个错误是有理由可辩护的”(《诗学》,第93页)。同时,亚氏又指出:“为了诗的效果,一桩不可能发生的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为可取”(《诗学》,第101页)。由此看来,所谓“偶然的错误”实在是算不上什么错误了,只要它有益于诗的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诗学》中关于诗的真实性标准是以诗的创造目的为依据的。
根据《诗学》中常出现的“或然律”和“必然律”这两个哲学概念及其与诗的有机整一性的关系,我们也能看到诗的构成上的真实性。可然律与必然律是《诗学》中常出现的两个概念。在《诗学》第七章,可然律与必然律初次出现:
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一件事物可能完整而缺乏长度)。所谓“完整”是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
(《诗学》,第25页)
一般的说,长度的限制只要能容许事件相继出现,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能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就算适当了。
(《诗学》,第26页)
所谓“自然引起他事者”,指事件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彼此相继,后一事必须合情合理从前一事产生。前事是因,后事是果,其间要有因果关系。这是悲剧情节的发展规律。很明显这里是就艺术逻辑而言的。其实《诗学》中二者的出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它意指诗人在创造中,依着诗的创造目的,如何处理在整体布局中诗的诸种要素(人物、事件等)之间,以及要素与整体之间关系合理性构成问题,实质也仍是形式之于材料的充分、完美的实现问题。因为充分、完美实现了的形式,就意味着合于诗创造的目的性,合于诗构成所应具有的前因后果、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秩序井然的或然性与必然性。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最强调诗构成的有机整一性,要求诗“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一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如果“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诗学》,第28页),就不能产生真实性。
综上所述,亚氏所谓或然性与必然性是诗自身构成的艺术逻辑,依此所构成的诗才可能合乎诗创造目的的要求,使诗符合诗自身的本性,符合诗之为诗的概念。因此,诗之真从创造构成的意义上看,在于诗的形式通过诗人充分完美地实现了自身。从接受角度上看,亚氏的诗的真实性在于诗的可接受性上,即诗的接受者的“可信”或“相信”,这是一种在对诗的欣赏状态下的接受者主观审美上认可的感觉。
三、亚里士多德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