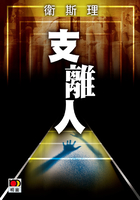那天,匡世宗正在园区工地上检查施工进度,三婶陶金凤急颠颠从河岸边的三码车厂跑来,老远就喊,世宗,不好了,住在烈士陵园的几位爷,今天早晨坐着匡石峁开的三码车,一块到省城为你申冤去了。匡世宗惊慌失措地问道,消息可靠吗?陶金凤说是石峁媳妇刚才亲口对她讲的,应该可靠。这帮爷!真能给添乱!匡世宗怪了一句,让三婶回厂里忙,自己从工地上找了一辆北京212牌绿色帆布篷吉普车,不顾一切地朝县城方向追去。绕过县城北环,在通往省城的国道上,世宗终于追上了他们。他扒着沾满粪疙疤的铁皮车帮,求情地说:“各位爷,听我的,都回去吧。”坐在车斗里的匡华堂、卢大旺、匡土根、三愣子、卢老七个个都沉着脸,完全不理会世宗的劝说。双方僵持了好一阵子,匡华堂才开口说话:“孙子,告输告赢是我们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回去吧。”匡华堂一边说,一边从屁股底下抽出拐杖,一手扶着车帮,一手用拐杖撑着他肥胖的身体从车斗上站起来,怒眉横眼地嚷道:“王佐他不就是个副厅级干部嘛,呸!爷我才不尿他呢!爷打小鬼子的时候他干啥了?世宗,俺们的事不用你管,省里告不赢,俺们就到北京找肖军去,我就不信扳不倒他一个小小的王佐!”见匡华堂这般理直气壮,其他几个老民兵也都跟着嚷嚷起来了:“干事的挨整,不干事的反倒成了精,天底下还有没有正事了?谁会闹谁就有理了?”疯疯癫癫的卢老七,从车斗里跳到地上,解开腰带,掏出裤裆里的家伙,站在马路中间就撒尿,一边尿一边喊:“老哥们儿,快瞧快瞧,咱村的墓地上又起旋风了,这下好了,世宗有保佑了,不用去告状了。”尿没撒到地上,却尿了一裤裆。他甩了甩像干萝卜头一样的******,边系腰边跑到三码车前,抽出发动柴油机的铁拐棒,颠颠着就往回去的方向跑。司机匡石峁追了过去,夺过铁拐棒,拉着卢老七就返了回来。
面对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爷爷,来硬的不能,来软的他们又不听,这让世宗好生为难。急切关头他不得不编出一套瞎话,说县里正在跟省里沟通,省里也基本同意了,很快就会让他官复原职,这个时候你们去告状,不仅起不到好作用,反而会帮倒忙。听世宗这么一说,老民兵们的火气马上就泄了半截。“你怎么不早说呀?早知如此,我们还不来呢。”这一手果真管用,只几句话,就把老民兵顺顺当当地给哄回去了。
尽管匡世宗受到降职处分没能让卢旺堆如愿以偿,但他仍然像一个打了胜仗的英雄一样而狂喜不已。他觉得,下一步只要略施小计,将匡世宗彻底赶下台,一把手的位置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打了胜仗自然要犒赏那些有功的下属。这天晚上,他让卢犬在自己家里摆了一桌酒宴,将卢早起、绿毛豆、小胖子等五个挨了打的有功之臣全都请来,要亲自为他们庆功压惊。
一开场,卢旺堆便慷慨激昂地说:“各位爷们儿,今天在座的都姓卢,都是没出五服的本家。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今天的这场酒,是我和卢犬副主任专门为大家设的一场庆功宴,没有你们几个的冲锋陷阵,没有你们冒着带伤挂彩的风险去跟他们斗,他匡世宗的下场也不会有今天这么惨。来来来,大家都端起杯,让我和卢副主任敬大家一杯酒,感谢大家了,干!”
有大队长亲自出面宴请,卢早起几个人早已被这从未有过的超规格待遇搞得受宠若惊了。几个人慌忙端起酒杯,有的叫叔,有的喊爷,连连恭维道:“打虎亲兄弟,战场父子兵,打江山不靠自家人靠谁呀?山水轮流转,匡家峪的江山不能只由他匡家人坐,也该到咱们卢家出人头地的时候了。你能当上一把,我们都跟着沾光,一人举官,鸡犬升天,这不是应该的嘛!”听了这些话,卢旺堆高兴得嘴都咧到耳根叉子上去了。“说得好!说得好!干!”卢旺堆一干,几个人跟着都喝干了。
卢早起和绿毛豆的头上还裹着包扎伤口的纱布,雪白的纱布上被血洇出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红圆点,跟日本的太阳旗蛮相似。卢旺堆走到他们跟前,一边察看伤情,一边关心地询问:“伤得要紧吗?要不要到县医院看看?”两个人嚓啦一下就把纱布扯下来了,伸着脑袋让卢旺堆看伤,说:“就擦了一层皮,早都没事了。”小胖子有点纳闷,说:“伤好了咋还不把纱布拽掉,跟戴孝似的。”卢早起瞪着小胖子红扑扑的圆脸蛋,嗔怪道:“你就知道吃,吃得跟小肥猪似的,只长肉,不长脑子!你懂不懂,这可是大队长的指示,戴着它,等于头上顶着一只喇叭,走到哪广播到哪,要让全村人都知道,是他匡世宗挑动职工将我们打成了这个样子。”小胖子晓得了其中的奥妙,连忙赔笑自责。卢旺堆吩咐卢犬:“找个名义,回头从大队财务上支些钱,每人发给他们三百元疗伤费,就说我说的。”大队长如此关爱,几个人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卢早起转身跑到厨房,搬来一摞卢犬家吃饭用的五只大瓷碗,在桌上一溜摆开,抓住酒瓶子咕咚咕咚挨个儿倒满,五个人一齐端起,举到卢旺堆的脸前,感激涕零地说:“旺堆叔,卢犬哥,一个卢字掰不开,今后有用得着小子们的地方只管吩咐,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谁要是眨下眼,谁就不是娘养的。来,你们两个喝小杯,我们五个喝大碗,干!”
卢旺堆狡黠地笑了笑,说:“怎么?你们喝大碗,让我们喝小杯,是不是看我老了,不中用了?”就让卢犬再拿过两只大碗来,满上酒,当啷一碰,就跟大家一起干了。酒喝到这份儿上,已经是情意交融彼此不分你我,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了。盛满酒的大碗碰得当当响,倾出的酒水像一堆蚯蚓一样在桌面上四处蠕动,盘子里的菜倒腾得烂糟糟的,六七双筷子在盘子里交叉飞舞,猪头肉、卤鸡腿、黑牛肝、红狗肺、火腿肠、白菜豆角花生米,随着如同机械手一样的筷子的翻飞,被准确地送进一张张油汪汪的大嘴里。
酒喝到凌晨三点方才结束,七个人足足喝了七瓶半,合每人一斤还要多。卢早起躺在地上,一边大口呕吐,一边号着肚子疼,吐得满屋子都是酸臭味。卢犬今天喝的最多,趴在桌子上,脑袋在一边歪着,嘴里流着腥臭的白沫,打着呼噜睡觉。绿毛豆和小胖子将卢犬的老婆菜花抱到炕上,一个拱着亲嘴,一个把手伸进女人的怀里,像掏鸽子窝一样乱摸,松软的乳房像两包兜着水的塑料袋,在女人的胸前颤巍巍地晃来晃去。卢旺堆仰在椅子的靠背上,只觉得周身麻木,天旋地转,若似腾云驾雾一般。恍惚间,一个女人的笑声像鸟叫一样钻进了他的耳眼,他呼隆一下折起身子,伸着脖子朝门口窥视,门口果然站着一个年轻女子。只见她倚着门框,两臂抄在胸前,杏眼迷离,玉齿微启,向他暗送秋波。他禁不住叫了一声“仙桃”,问她为啥站在这里?女人只管抿着嘴笑,不予作答。卢旺堆抬起屁股,伸长脖子,像螳螂捕蝉,痴迷地盯着前方,慢慢向门口凑近,当他伸手去抓那美人时,却撞在了冷冰冰的门框上,眉头顿时起了个疙瘩。他摸着伤痛的眉头,跨出门槛,在院子里四处寻觅,却看不见仙桃的身影。正要返身回屋,女人的笑声突然从街门筒子里传来,脆滴滴,轻柔柔,爽朗朗,酸溜溜,甚是迷人。他反身来到街门洞,门洞里黑黢黢的,伸手不见五指,他一边亲昵地喊着仙桃,一边沿着墙壁用手摸索,摸了一圈,依然不见仙桃。他抬腿就往街门外走,没小心脚下的台阶,一脚踩空,如青蛙跳水,老虎捕食,扑通一下便跌趴在台阶下,磕得满嘴流血。他像只受伤的黑狐狸,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站在胡同里向大街望去,就见胡同口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在向他招手。“仙桃,仙桃,是你吗?你等着。”他发疯似的向大街跑去。大街上阒静无声,寂寥得像一座昏暗的岩洞。吊在电线杆上的灯泡,像几只未熟透的小西红柿,在微风中悠闲地摇曳着。他摁着装满酒的胃口,感觉像是揣着一窝小老鼠在肚子里踢腾打闹。他忍着翻肠倒胃般的难受,歪歪扭扭地四处搜寻仙桃,结果又是一阵失望。他终于忍不住老鼠们的折腾,腹腔一抖,脖子一伸,哇的一声,一股酸臭汤便夺门而出。他眼前一黑,倒在地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女人的浪笑突然从四面八方齐声荡起,“旺堆儿——咯咯咯咯——你在哪儿——咯咯咯咯——我在家里等你——咯咯咯咯——快过来啊——”女人的叫声像百灵鸟一样从昏睡中将他唤醒。他想爬起来,四肢却不听使唤,软得像一摊泥。不过他并不笨,他有分身术。他把自己像死尸一样的肉体留在大街上,魂魄从肉体上分离出来,忽悠悠飞到空中,依照他熟悉的航向,踩着云,随着风,像神武老道一样飞向了位于村后的仙桃的住宅。他飘飘然从空中降到天井,化作一缕蓝色的烟雾,从门缝直接飘进屋内。见仙桃恬静地睡在炕上,心里就想,刚才你还笑得浪气冲天,现在我来了你却又装睡。想睡就睡吧,睡美人玩起来更别有一番风味,平时放明枪,这回我可要打暗炮了。他钻进被窝,抱着白嫩娇柔的仙桃,哼哼唧唧地就亲吻起来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从温存甜美的梦境中渐渐恢复了一点意识,他半醒半睡地眯着眼,喃喃着,用力扯拽身旁的仙桃。他抱着她,手在她的身上摩挲着。蒙眬中他好像有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仙桃浑身长满了粗糙的皮毛,扎得他浑身刺痒。他不由得睁开一双惺忪的眼,定睛看时,不觉吓了一怔,原来他怀里抱的并不是仙桃,而是一头肥大的老母猪——猪因为吃了他吐出的酒食,醉倒在了他的身旁——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像鲤鱼打挺一样跳了起来,掂了掂裤子,慌慌张张就走开了。
鸡打五更,一位起得早的拾粪老汉,走到醉猪身旁,望着已经离去的卢旺堆的背影,叹息道:“自己醉不算,还要把猪醉成这个样子。”他一边自言自语地囔囔着,一边兴高采烈地将猪屁股下面的一摊稀粪装进粪筐里,似乎有种一大早开门见喜般的得意。然后他便蹲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猪腚眼,看着咕嘟咕嘟继续向外冒着的稀屎,用手拍打着猪的臀部,催促说:“快屙,屙出来会好受些,你屙得越多,我的地就越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