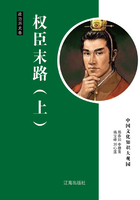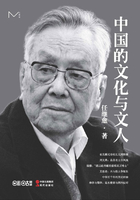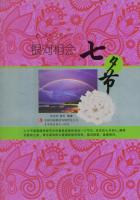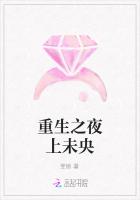大观园即随园说辟谬
――从随园历史说到新发现的《随园图》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订稿)》中说:“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以信此话不是假的。袁枚的《随园记》说随园的本名隋园,主人为康熙时织造隋公。此隋公即是隋赫德,即是接曹的任的人。袁枚作记在乾隆十四年己巳,去曹卸织造任时甚近,他应该知道这园的历史。我们从此可以推想曹当雍正六年去职时,必是因亏空被追赔,故这个园子就到了他的继任人的手里。”这一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没有提出任何资料,只不过抓住袁枚一个自吹的话(“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加以“推想”罢了。
现在,我根据文献记载,证明随园与曹家毫无关系;根据新发现的《随园图》,证明随园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毫无相似之处。
(一)
先探讨一下随园的来历。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二有随园六“记”。第一记即《随园记》,说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小仓)山之北巅,构堂室,缭坦牖,树之千章、桂千畦,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购以月俸,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这一段话,说出了随园的前身是酒肆,酒肆的前身是隋园。但隋园的前身是什么,没有说明。
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隋赫德(绥赫德)于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接任江宁织造。袁枚说“康熙时”隋赫德建筑隋园,是错误的。
又据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他于“戊辰秋”即乾隆十三年秋购随园。从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三年,连头带尾,仅有二十一年。袁枚说“三十年”,又是错误的。
还有一些资料,谈到随园的来历,可补《随园记》的不足,如:
一、袁枚辑《〈随园雅集图〉题咏》)载沈德潜文,文中说:“随园在小仓山旁,前明焦弱侯故址,同年袁太史子才葺而新之者也。”袁枚接受沈德潜这个说法,并进一步考证出明代焦园也叫随园。
二、袁枚编《随园续同人集?过访类》载张坚诗,诗题为:《白门有随园,创自吴氏,余少时往游,其间兴废不一,近为简斋先生所得,余喜复游其地,读先生自为记,敬呈一诗》,诗中说:“瞬息四十年,园林数主易。”这“四十年”,是从吴园创建到随园兴起的历程。(批《随园诗话》的舒坤,也说“随园之先,故属吴姓”,是抄袭张坚的诗)
必须指出,裕瑞《枣窗闲笔?〈后红楼梦〉书后》所云“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间”,是不足为据的、“失实”的“传闻”。
按张坚的说法,隋园的前身是吴园;按照裕瑞的说法,隋园的前身是曹园。将两说进行比较,张说可靠。因为:张坚的时代较前,又游过吴园。他的诗,是读了《随园记》之后所写,也就是为了补充袁枚之说而写。袁枚将张坚的诗,放在《随园续同人集》的第一篇,可见此诗是有分量的。裕瑞的时代较后,他所谓“闻”,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能是因为曹家被抄家,家产“赏给”隋赫德,从而推测隋园是曹园“故址”。
胡适没有见到这些材料,就“推想曹当雍正六年去职时,这个园子就到了他的继任人的手里”。真是胡说。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分析,将随园的来历,作出如下的简表:
(明)(清康熙时)(雍正时)(雍正、乾隆时)(乾隆时)
焦氏随园――吴园――隋园――酒肆――袁氏随园
还需指出,清代的吴园、隋园、随园虽在同一地址,但其建筑是大不相同的。一、张坚诗:“吾少日过此,入门嫌径窄。邱壑一目尽,蓁莽未全柞。”可见吴园是简陋的。二、袁枚《随园杂兴》:“当年隋大夫,对山初作屋。父老为我言,此公殊不俗。”可见隋园是在吴园旧址重新建筑的。(这也可以说明隋赫德不是接收曹家的园子。如果是曹园,不至于荒芜如此)三、袁枚《随园老人遗嘱》:“随园一片荒地,买价甚廉,我平地开池沼,起楼台,一造三改。”可见随园又是在隋园旧址重新建筑的。
(二)
随园是袁枚一家居住、游览、娱乐的场所,是剥削劳动人民建筑起来的。随园不仅是一座园林,又是一所庄园。劳动人民的血汗,喂养着袁枚一家。随园的建筑史,就是一部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血泪史。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九《瘗梓人诗》的小序,说:“梓人武龙台,长瘦多力,随园亭榭,率成其手。癸酉七月十一日病卒,素无家也,收者寂然。余为棺殓,瘗园之西偏。”随园是包括武龙台在内的南方木匠、瓦匠、花匠们的劳动成果和智慧结晶。在考察随园的形成历史和建筑艺术时,不应忘记他们。武龙台生前没有家庭,死后没有葬地。由于袁枚对他剥削极为残酷,使他穷得一无所有,劳瘁而死。但袁枚并不以为这是自己的罪恶,反而吹嘘他把武龙台埋葬了是在行善。
袁树(袁枚从弟)《红豆村人诗稿》卷十一《折杖偈》自注:“以菊花贻随园主人,覆书云:‘早间为种菊,呼奴不至,打折拐杖一枝。一旦毁折,悔之无已。弟忽送菊来,可以小偿余愤’。”袁枚用拐杖打花匠,把拐杖打断了,表示惋惜,而把“奴”打伤了,是无妨的,还余愤未泄。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随园园丁、花匠遭遇的一斑。
袁祖志(袁枚孙,袁通子)《随园琐记》卷上《记?邱陇》:“祭田六十余亩,在园之东西,计佃户十三家,有稻田,有柴山,有鱼池,有菜囿,有竹木果实,收租取实,极称其便。”同书卷下《记轶事》:“附园东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户承领种植,主人遇有吉凶喜庆等事,即招十三户中人供役。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年终之鸡豚等类,均属各户排日按年承值供给。”这十三家佃农,承担了袁枚全家食物、燃料的供应,还要服劳役。在剥削者的袁家“极称其便”的后面,就是被剥削者的十三家佃农受尽了压榨,流尽了辛酸血泪。
以上,只是袁枚、袁树、袁祖志偶然留下的片段记载,但已可看出袁家剥削、虐待劳动人民的情况。自命“清高”“以官易园”“享林泉之福五十年”的袁枚,其实是一个吸血鬼。
(三)
袁枚和他的后裔,请人绘过不少的“随园图”,图中表现的什么“雅集”“话别”等等,虽是宣扬官僚地主的生活场面和思想情调,但描绘随园景色的图画,对于研究古典园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下面先将见于文献记载的几种随园景色图,略作介绍:
一、袁祖志《随园琐记》卷上《记图册》:“随园五图者,乃图绘园中之景,五人笔墨,合装一卷者也。一为吴江张看云栋,一为扬州罗两峰聘,一为山〔江〕阴沈凡民凤,一阙名,一为叔祖香亭公也。”(蒋敦复《随园轶事》卷六《图画有存有亡》:“先生尝以随园全景,倩人各绘一图,共得五图,合装一卷。”全是抄袭袁祖志的话)
二、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九《随园!》:“当时沈补罗山人作图最早,园中景未备,寥寥短幅,罗两峰所作,偏写北冈西隅之景,略于南山。张翰〔看〕云所作,重图南山诸景,略于北山,因天风阁写长江入图,未免收景过远。项莘甫作粉本未就,其弟子王春波成之,诸景错落,西山不分,盖四家于一览之余,各出心裁,以意挥洒……形似未得,即身居园中者,披图亦莫名其处。其后香亭观察绘一图,极形似之致,居北面南,写柴扉于卷末,然自以倒置为嫌,欲重作,未果。”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随园五“图”的画者是:一、沈凤(凡民,补罗);二、罗聘(两峰);三、张栋(看云);四、项穆之(莘甫)和王霖(春波);五、袁树(香亭)。《随园琐记》所说“一阙名”,其实不缺。这些人,是当时的“名家”,其生平,在袁枚的诗文和一些画史中有记载,今不赘述。
窦镇评袁树的山水画“简静浑脱”,李之评袁树的山水画“饶有士气”。可见袁树的画,是所谓“文人画”,不是界画。柴萼说袁树所绘《随园图》“极形似之致”,乃是捧场,不能轻信。
随园五“图”于咸丰、同治时毁掉(一说遗失)。袁起(袁枚族孙)“追忆(随)园中泉石”,绘成《随园!》,请曾国藩等题句,还将图画和题句刊印出来。
除了袁枚请人绘制的随园五“图”以外,当时还有慕名而来绘图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六《八十自寿》自注:“甲辰春,和致斋相公遣人来画随园图”(和字致斋),就是一例。和从北京派人来画随园图,可见该园名声之大。
游览随园之后,绘图留念的,如麟庆《凝香室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下册《随园访胜》,以及清人《载酒访随园图》等。
还有专门描绘随园中一亭一榭一花一木的图画,对于研究随园全貌的参考价值不大,就不详谈了。
(四)
有比较才能鉴别。我根据文献,介绍随园景色图的几种情况,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新发现的汪荣所绘《随园图》的价值。
陈从周发现一幅古典园林画卷。绢本,设色,长173.4厘米,高49厘米。画卷上没有题字,仅有“汪荣之印”一方。画卷后,有纸本所写随园五“记”,署名管镛。此图现为同济大学图书馆收藏。陈请我鉴定,我看,这是一幅《随园图》。
汪荣,一般画史中没有汪荣的名字。嘉庆时吕燕昭、姚鼐等修《重刊江宁府志》卷四十三《人物?技艺》:“汪荣,字欣木。六合县诸生。工画,烟云变幻,颇得二米之法。曹秀先督学江苏,以‘深山藏古寺’题试诸生之善画者,以荣为冠,兼工写生。”(光绪时谢延庚、姜士彬等纂《重修六合县志》卷八《附录?方技》介绍汪荣,与此相同)曹秀先于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为江苏学政,汪荣是乾隆、嘉庆时人。
管镛,字西雍,号桂庵、退庵、斋。是袁枚的学生。冯金伯《墨香居画识》卷十:“管镛,字退庵。上元岁贡生。丁卯春日,曾访之于城北双石鼓,而不知其能画。近于朱炼师乐园扇头,见其写梅花一枝,精妙绝伦,题句书法亦工,几令人摩挲不忍置。”“丁卯”是嘉庆十二年,管镛也是乾隆、嘉庆时人。
汪荣工画,这幅画卷应是他游览随园后所绘。管镛工书,画卷后的随园五“记”写得很好,肯定是他的真迹。(管镛只抄了随园五篇“记”。因第六“记”系谈坟茔,与园林无关。汪荣既不画随园外的袁家坟茔,管镛也不抄《随园六记》。)
管镛在抄完《随园五记》之后,题了几句跋语:“随园夫子居随园四十余年矣,名家五为之图,先生六为之记,皆足以传世而宝贵者也。乾隆辛亥年七月,桂庵管镛书并识。”“辛亥”是乾隆五十六年,汪荣绘图当在此年或稍前。按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余得随园之次年,即乞病居之。四十年来,园之增荣饰观,迥非从前光景。”“次年”指乾隆十四年,四十年后为乾隆五十四年,正是汪荣绘图前两年左右。可见,这幅画卷反映了随园全盛时期的面貌,比上述那些随园景色图更具有研究价值。所谓“名家五为之图,皆足以传世而宝贵者也”,不过是一句客气话。
这幅画卷的前半段,描绘的是园外景色;后半段,描绘的是园内景色。都与袁枚、袁祖志等所记载的随园相合。为了避免叙述的繁琐,试用表格将画卷与文献资料对照如下:
经过对照,可以进一步肯定,这幅古典园林画卷,毫无疑义的是《随园图》。从研究园林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说,这幅《随园图》的价值,不是上述那些随园景色所能比拟的。因为:沈凤等绘的随园五“图”是写意之作,而汪荣此图是写实之作;麟庆所刊《随园访胜》图是小品(册页),而汪荣此图是长卷。
(五)
南京小仓山的随园,是袁枚的私园。小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元春的“行宫”(省亲别墅)。两者性质不同,布局不同。例如:
《红楼梦》第十七回,描写“大观园”:“(贾政)只见正门五间,上面筒瓦泥鳅脊;那门栏窗?,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随园“四面无墙”,仅有篱笆,大门是柴门,二门又小又低。两者有哪一点相似?
《红楼梦》又说:“(贾政)遂命开门,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随园大门内是竹林,二门内是梧桐,没有山。两者又不相似。
《红楼梦》中描写“大观园”的正殿――“大观楼”:“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金辉兽面,彩焕螭头。”在“大观楼”前,有“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随园内哪有这样的建筑?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随园图》,与“大观园”没有相似之处。无怪袁枚之孙袁祖志要删去《随园诗话》中“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两句,认为是“吾祖谰言,故删之”。
游览过随园的麟庆说:“虽无奇伟之观,自得曲折之妙,正与小仓山房诗文体格相仿。”可见,随园是按照袁枚的理想建筑的。阅读过《红楼梦》的“二知道人”说:“大观园之结构,即雪芹胸中邱壑也,壮年吞之于胸,老去吐之于笔耳。”可见,小说中的“大观园”是按照曹的理想塑造的。两人的理想不同,两园岂能混为一谈。
总之,袁枚的随园,是一个具体的园林,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曹从当时名园,选取素材,经过加工、改造,运用文学语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大观园”不是反映某一个具体的园林,而是当时南北园林优点的综合,比具体的园林,更典型,更理想。
枕霞阁与李煦茅亭
张云章《朴村文集》卷十一《御书修竹清风图记》云:
“织造之职,盖古司服之遗,历代加详,国朝仍明之旧,江宁苏杭,各遣内使以督理之。昌邑李公之莅吾吴也,于今十有四年。上供之物备具,而益饬机匠女工,不伤其力,所出者各以时,咸合典式。又十年之中,三奉巡幸,公与其僚,奔走先后,悉给而不扰于民。天子嘉之,用周汉进律增秩之典,爵公为大理寺卿,而以监察御史督理两淮盐课,俾与江宁织造曹公,分年兼领,所以宠任之者至矣。御史虽曰巡视两淮,实所统辖跨四省三十六府之地,商纲亭户,赋敛出入,舟樯往来,飞符走驿,常在江湖数千里外,供是职者,亦云难矣,又况其兼官者哉。公之始至苏,以其署为上之所驻跸,加辟而增新之,敞以亭阁,延以廊庑,翠竹碧梧,交荫于庭,清风徐引,则飒然衣袂间。三十八年,驾果复幸,圣心怡悦,因题‘修竹清风’四字为额,以锡诸公。四十二年,其地建为行宫,复改筑焉。乃择其工于画者,绘图以荣上赐,并志其景物,以示永久。初公于郊外种竹成林,结屋数楹,杂村墟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至是以其地远,别购南城废畦一区,流水萦其前,编篱缭其外,中为堂三间,复作茅亭于其东,皆无栌节?之华,以公自所憩息,崇其俭也。四围惟多植竹,以隔市尘。春秋佳日,率宾佐僚吏,觞咏其中。遇清风之来,披拂琅,戛击锵鸣,则欣然喜曰:吾以此当上之旧赐额所矣。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谨书于李公之仪真署中。”
这虽是一篇捧场的文章,但对研究《红楼梦》,颇有用处。
(1)它介绍了清康熙年间江宁、苏州织造以及两淮巡盐御史曹寅、李煦的一些情况,对李煦的介绍较详,还说出李煦自号竹村,从而证实了《楝亭诗钞》中《竹村大理寄洋茶、滇茶二本,置西轩中,花开索诗,漫题二首》《桃花泉(并序)》《竹村惠砚》《苦雨独酌,谢竹村使君见贻盆兰有作》《六月十日,竹村大理、南洲编修、勿征君过访真州寓楼有作》等诗,皆是曹寅与李煦唱和之什,这对于研究曹、李两家的关系,是重要的线索。
(2)《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回廊,也是跨水接峰,后面又有曲折桥。众人上了竹桥,一时进入榭中,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贾母……向薛姨妈道:‘我先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第四十回:“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第七十六回:“池沿上一带竹栏相接,直通着那边藕香榭的路径。二人遂在两个竹墩上坐下。”红学界公认:《红楼梦》的史氏,其取资和运用素材是和李煦家有一定关系的。张云章《御书修竹清风图记》说出李煦在苏州南城有一所园林,“流水潆其前,中为堂三间,复作茅亭于其东,四围惟多植竹”,与《红楼梦》中史家的水亭子枕霞阁,景物相似。曹借用史家的茅亭来描写贾家的藕香榭,渲染竹桥、竹案、竹栏、竹墩,可能是参考了自号竹村的李煦的爱竹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
周汝昌将此文载入《红楼梦新证》,并赋诗云:“一记《清风》字未昏,葑溪修竹自成村。枕霞旧阁依稀在,多感琼瑶证梦痕。”
宁、荣二府与阮元东、西第《红楼梦》宁、荣二府中间夹一祠堂的建筑结构,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现存的古建筑中,这种式样是不多的,在扬州发现一处,特撰此文。
(一)
宁府与荣府《红楼梦》第三回:“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自上了轿,进入城中,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道: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这是《红楼梦》中描写宁、荣二府建筑的一段重要文字。曹借初进荣国府的林黛玉的一双眼睛,将宁、荣二府的位置,介绍给读者。再参照下面两段文字,对宁、荣二府的布局,就更清楚了。
“先令匠人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然这小巷亦系私地,并非官道,故可以连属。”(第十六回)
“因二府之门相隔没有一箭之路,所以老嬷嬷带着小丫头只几步便走了过来。两边大门上的人都到东西街口,早把行人断住。”(第七十五回)
宁府的会芳园与荣府的东大院相连属,这个标志很重要。
贾氏宗祠《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照,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次日,且说宝琴是初次,一面细细留神打量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青绿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上面悬一九龙金匾,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填青匾,里边香烛辉煌,锦幛绣幕,虽列着神主,却看不真切。众人围随着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幔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的无一隙空地。”这是《红楼梦》中描写祠堂建筑的一段重要文字。曹借初次进祠堂的薛宝琴的一双眼睛,将祠堂的式样,介绍给读者。再参照下面一段文字,对祠堂的位置,就更清楚了。
“就在会芳园丛绿堂中,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扇开阖之声。”(第七十五回)
贾氏宗祠紧靠着会芳园,这个标志很重要。(曹在第十六回已经说过,会芳园扩建为大观园。此后,宁府中就不再存在会芳园了。可见,第七十五回所说贾珍等人在会芳园丛绿堂中夜宴,是漏洞。这个漏洞,反映出大观园是虚构的,但不妨碍我们研究贾氏宗祠的位置。)
综合以上,《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宁、荣二府的位置、布局是:二府同在一条东西大街上,坐北朝南。宁府在东,荣府在西。宁府的会芳园,与荣府的东大院相连,中有小巷,系贾家私地。二府之间,还有一个不大为读者所注意的祠堂。祠堂的大门,在府内,不在街上。
宁、荣二府与贾氏宗祠的位置,不出以上三种式样。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式样,都能说明贾氏宗祠在宁、荣二府之间。在北京、南京、苏州、扬州这几个与曹家有关的历史文化名城里,有没有两所住宅中间夹一祠堂的建筑结构呢?
(二)
在明、清两代,扬州城分为旧城与新城。在旧城太傅街(毓贤街),有阮元的住宅。太傅街是一条东西大街。阮宅在街北,坐北朝南。我在学生阮荣的陪同下,参观了阮元故居。今天的样子,虽然不完全是阮元时的原样,但还可以看出一些规模。东边是一所住宅,西边也是一所住宅,中间是祠堂。两所住宅,各有大门和外照壁,外照壁上都嵌着“御赐(横)出门见喜(竖)”六字的砖刻。祠堂无门通向街道,无外照壁,有内照壁,上嵌“福”字砖刻。祠堂共三进房屋。
阮荣又陪我访问她的“老祖”(扬州人称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一辈为“老祖”)阮朋三老人。从老人的谈话中,我又了解到几点情况:(1)阮元原住旧城福寿庭,俗称“阮家大院”。在新城康山也住过。两所住宅都失火,后住太傅街。(2)太傅街住宅是买的常遇春家和曹家的旧宅。(3)阮元先在太傅街建立祠堂和家塾,后住家。东西两宅都有门通祠堂。(4)阮元官高自爱,把祠堂建在宅内,免得祭祀时惊动来往于太傅街的文武官员,要下马下轿。
我又查考了文献,据阮元《经室二集》卷二《扬州阮氏家庙碑》:“嘉庆九年,乃卜地于扬州府旧城文选楼北兴仁街,鸠工庀材,越九月,庙成。”《扬州隋文选楼记》:“嘉庆九年,元既奉先大夫命,遵国制立阮氏家庙,庙在文选楼文选巷之间。庙西余地,先大夫谕构西塾,以为子姓斋宿饮?之所,元因请为楼五楹,题曰隋文选楼。”《扬州文楼巷墨庄考》:“元居扬州文楼巷文选楼侧。”《经室四集》卷二《扬州隋文选楼铭》:“予之宅为选巷旧址。嘉庆十年冬,遵先大大遗志,于家庙西建隋文选楼,楼下为庙之西塾。”所谓“文选巷”“文楼巷”是古地名。兴仁街后名太傅街。《清史稿》卷三六四《阮元传》:“(道光)二十六年,乡举重逢,晋太傅。”
又,王振世《扬州览胜录》卷七《旧城录》:“阮太傅故宅,在旧城太傅街。宅为清阮文达公元之居,建于乾嘉间。东为太傅东第,西为太傅西第,中为家庙。”
综合实地观察、口头访问、查考文献三方面的收获,发现阮元故居的建筑结构,与《红楼梦》中宁、荣二府中间夹一祠堂的式样,颇为相似。
(三)
有人要问:你把乾隆时撰写的《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与嘉庆时建筑的阮元住宅,对照起来研究,有什么意义呢?请看如下的分析:
(1)扬州旧城三元巷东有旌忠庙,奉祀南宋抗金将领魏俊、王方。据说“明太祖尝梦俊、方助国”(《扬州府志?祠祀?甘泉县》),所以为他们立庙。康熙时,曹寅在扬州,曾发起修理这个庙。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九《重修江都县旌忠庙碑》:“历年久远,庙圮不治。今通政司使、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曹公谒庙下,语守者曰:‘斯境内之神,吾民祈报于是,旌忠故典,修举不可缓也。’乃稽谋于众,攻金攻木,给以饩廪,取陈丹暗粉一新之,属其友秀水朱彝尊考两侯之遗事,撰碑文勒诸石,兼作歌以侑神焉。”曹寅做这件事,是为了博取当时具有遗老、遗少气味的南方士大夫的好感。直到嘉庆时,阮元还记得这件事。《经室三集》卷二《重修旌忠庙记》:“扬州旧城旌忠庙,康熙间盐正曹楝亭寅修之,朱检讨撰碑文,载在《曝书亭集》。余谒庙,庙毁甚,象亦坏碎,求检讨碑不可得,岂当时未刻石耶?嘉庆十二年秋,予鸠工重修之,立其象,设其主,与知古好义者同祭而落之。”在阮元的心目中,曹寅是个“知古好义”的前辈了。
(2)扬州城东里村(六里村)有东园,是康熙四十八年盐商乔豫(逸斋、逸园)和他的儿子乔国桢、乔国彦(俊三)所建。曹寅在东园住过(《江都县续志?古迹,东园》),为东园品题了八景(《江都县续志?艺文上》张云章《扬州东园记》),还写过一些诗词,如:
《和乔俊三东村书屋诗》(《楝亭诗钞》卷六)
《逸园新戢闻其东村之胜与客潜访反值泥饮戏拈柳字用少陵韵》
《东园看梅戏为俚句八首》
《真州西轩行药念俊三病书此代问时将归金陵》
《寄题东园八首》(以上《楝亭诗钞》卷七)
《和乔俊三东村书屋诗》
《六月廿五日大雨同鹿墟九迪子鱼植夫吹万滕友小酌分韵前一日,允文序皇又昭上若俊三先归扬州却寄二首》
《西轩同人将别用和蕉饮原韵醉中语无伦次兼简鹿墟右诚蒿亭元威俊三庵吉云尚中四首》(以上《楝亭诗别集》卷四)
《疏影(俊三索题东园看梅词不暇应秋中真州雨窗赋寄)》(《楝亭词钞》)
曹寅与乔氏父子的唱和,选入诗词集中者,就有九题之多,可见他与这个盐商关系的密切了。阮元对曹寅这件事也很注意,他在《广陵诗事》卷六写道:“《东园八咏》:其椐堂、几山楼、西池吟社、分喜亭、心听轩、西墅、鹤厂、渔庵,此别一东园,为乔氏别墅。吴梅查《郡中废圃诗》四首,一曰东园,‘乔逸斋先生别业,曹楝亭鹾使尝寓于此’。又云:‘东园岩际椐木大十围。’”在阮元的笔下,是作为曹寅的一件雅事来记载的。史称阮元“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清史稿?阮元传》),如果阮元不赞成曹寅与盐商往来,就不会记载这件事了。
(3)阮元是江春的“甥孙”(见《扬州画舫录?桥东录?阮元》)。江春是个什么人呢?阮元《经室再续二集》卷二《歙县江鹤亭橙里二公传》:江春“祖演,侨居扬州。父承瑜。皆以盐起家”。江春“治鹾业,上官知其能,檄为总商,凡重事皆与擘画”。“公运盐之号曰广达,每鹾使者出都,必谕曰: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商办”。“乾隆十六年,上巡幸江浙,扬州迎驾典礼,距圣祖时已远,无故牍可稽,公创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又见阮元《淮海英灵集》戊集卷四《歙江氏诗?江春》)。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二《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四十年来,凡供张南巡者六。”乔氏江氏都是盐商,曹寅与乔氏来往多,与江氏不可能一无往还。江氏三代行盐,江春身为“总商”,六次接驾,对于时代稍前的鹾使曹寅,也不可能一无所知。
江春住在康山,阮元也住过康山,可见两家关系密切。阮元从“喜吟咏,好藏书,广结纳,主持淮南风雅”(阮元《歙县江鹤亭橙里二公传》)的江春那里,能听到曹寅的遗闻佚事。
(4)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17《江宁织造曹覆奏家务家产摺》,曹寅有“扬州旧房一所”。从曹寅的为人来看,为了不惊动来往的官员百姓,把祠堂放在住宅内,是可能的。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可为旁证。
(5)阮元在太傅街的住宅,是买的常遇春家和曹家的旧宅。常遇春是明代开国功臣。当是常家破落后,辗转卖给曹家。这曹家是不是曹寅家呢?在未找到“房契”或其他物证之前,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我只在这里作两种推测:
甲曹寅主管的“盐院”(“盐法察院”),在扬州旧城开明桥东南(《扬州府志?公署》),院大街上(《扬州画舫录?小秦淮录》)。院大街与兴仁街(太傅街)距离很近。曹寅为了到“盐院”方便,可能买下常遇春在兴仁街的故居,作为住宅。(赵执信《饴山诗集》卷十二有《端午抵扬州假寓于使院之前鹾贾之馆颇宽洁有竹数十竿》诗,这是盐商为了联系方便,住在“盐院”附近的一例)兴仁街距离旌忠庙也很近。曹寅如住在兴仁街,闲暇时到旌忠庙,看到“庙圮不治”,对“守者”说出“斯境内之神”一段话,更觉得合情合理了。
雍正五年,曹罢官。六年,籍没家产,赏给隋赫德。扬州“旧房”当然也赏给隋赫德了。雍正十一年,隋赫德到北京之前,“曾将官赏的扬州地方所有房地,卖银五千余两”。曹寅“旧房”当然也被出卖了。以后,可能辗转为阮元买去。(《扬州览胜录》卷六《新城录》:“康山,在新城徐凝门东,清乾隆间,江鹤亭方伯:就康山构为家园。鹤亭身后,因欠公帑,园乃入官。道光间,阮文达公领买官房,则康山正宅,园在其侧,时已荒废。”从阮元买江春故宅来看,不是不可能买曹寅“旧房”。)
乙阮元所买,不是曹寅的住宅。但曹寅在扬州有一所“旧房”,是肯定无疑的。阮元不但距离曹寅时代近,他原住福寿庭(新华东巷),就在“盐院”(新华中学)的旁边。阮元对曹寅的情况不应陌生。曹寅“旧房”的建筑式样,阮元能亲眼看过或听人说过。阮元向往曹寅的为人。(如《广陵诗事》卷六:“康熙间,通政曹公楝亭于沙漫洲上建亭,曰渔湾,尝集渔人打鱼于此。二十年后,鞠为茂草,惟存老树数株。乾隆癸卯,黄北过此,有诗吊之。”)他的住宅,模仿曹寅的“旧房”结构(或模仿《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结构)是可能的。
附记:拙文发表后,听友人说,北京原马神庙东街有清贵族傅恒宅,建筑格局与宁、荣二府之间夹一祠堂相似,惜今已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