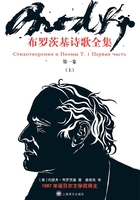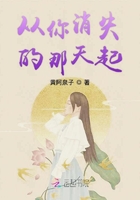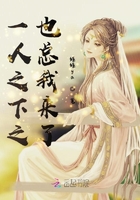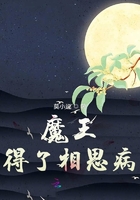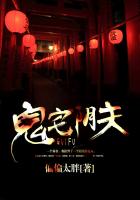西渡
1989年被许多诗人视为一个重要关口。一代诗人在此面临着抉择。这一抉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由几方面的原因一起带来的。在此前后,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是由一场被命名为市场化的渐进革命所引起的。这种变化使80年代的某些写作顿然现出苍白的原形。要想在变化了的历史境遇中维持写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我们的写作不得不面临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与此同时,在8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先后步入了中年,这一诗人群体的年龄构成的变化带来了对青春写作的合法性的质疑。而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说,经过80年代狂热的形式实验的酝酿,至此也恰好面临其中对蜕变的召唤:进入一个更加开阔、成熟的境界。
艾略特在评论叶芝时曾说,一个作家到了中年只有三种选择:完全停止写作,或者由于精湛技巧的增长而重复自身,或者通过思考修正自身使之适应于中年并从中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60]鉴于以往文学史的经验,这种中年意识首先是作为一种紧迫的危机感渗透到90年代的诗歌意识中来的。而这一时期诗歌意识的转换过程,似乎证实了一种论点:一个诗人要想在中年以后继续写作,获得某种恰当的历史感是必不可少的。在90年代最为流行的诗歌批评词语(本土化、个人写作、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无不渗透了对获得这样一种历史意识的期待。这可以说是90年代诗歌区别于80年代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80年代强调的是诗歌对历史的超越,强调诗歌独立的审美功能,主张一种“非历史化的诗学”。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歌对历史的处理能力被当作检验诗歌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评价诗人创造力的一个尺度。但是需要加以辨析的是,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与历史的关系中,绝不是要回到反映论的旧调重弹,或者取消诗歌审美的独立性,而是诗歌审美为历史留出了空间。这里的历史并不是先于写作而存在的实现,而是在写作中被发明出来的,它拓展了诗歌审美的资源,丰富了它的可能性。这种历史意识不仅表现在这一时期诗人的诗学理想中,也充分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文本中。欧阳江河写于1993年的诗学文章《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61]是对这种期待的较早的明确表述。他曾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但是当诗人面对某种可怕的历史景观,他发现“抗议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其可能性已经被耗尽了”,因此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朦胧诗人”的对抗主题,诗人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参与到“诗歌写作的历史转变”中。同一时期,王家新、萧开愚、孙文波、臧棣、陈东东、西川、桑克等主要诗人都表述了类似的对诗歌的历史境遇的关注。王家新提出“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一种历史化的诗学,一种和我们的时代境遇及历史语境发生深刻关联的诗学”[62],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引马克思的话说: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孙文波强调诗人“必须关注生活”[63]。萧开愚要求诗人“研究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寻找中国的诗神’,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树立起当代中国诗歌的形象”。臧棣在其重要的诗学论文《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中将之进一步概括为一种总体性的倾向:“在20世纪中国诗歌的写作上,没有哪一代诗人比后朦胧诗人更迫切地渴望加强诗歌同我们的生存境况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还必须显示出直接性、本真性、体验性和实验性的特征,不再受制于以往唯我独尊的文学的经验性”,由此显示了这一代诗人的伟大的诗歌抱负——“就像130多年前惠特曼对美国诗歌感受力所做的修正:亦即怀着巨大的热忱,在新时代感性的基础上,使诗歌表现力充分地活跃起来”[64]。
这种迅速增长的历史意识,使90年代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根据我的观察,将之粗略地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从题材上说,本土化和关注日常生活的倾向得到广泛的响应。宏观叙事和泛泛的、空洞的抒情被多数诗人所拒斥,诗人所关注的题材越来越具体,有时甚至显得琐碎。但是,题材的具体化并没有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使诗歌沦为“私人性的吟咏”“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也没有使诗“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因为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中,融进了诗人的深刻的历史意识:只有在具体的细节中,历史才能得到恰当的呈现(王家新所谓:当你挤上北京的公共汽车,或是到托儿所接孩子时,你就是在历史之中[65])。臧棣通过楼梯上烧坏的灯泡发现了一座居民楼的良心,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良知发明了恰当的隐喻。[66]王家新在谈及孙文波90年代的诗歌写作时说:“他一再从具体的生活事件出发,写出来的却是灵魂的遭遇。”[67]至少在90年代最优秀的那部分诗人的写作中,并没有导致一些论者所担心的“对无中介的原初经验的迷信”(姜涛语),而能够超越细节本身,把读者引向对细中所包含的特殊历史境遇的关注。臧棣的写作可视为这方面的范例。“当代生活是一种反英雄主义的生活,它对于人的要求是将理想主义转化为现实主义。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下,诗歌写作对于英雄主义的认同,……是在现实的仔细解析中,找到理解现实的钥匙。”[68]理解现实并非对现实的简单认同,而要求诗人在一种崭新的历史境遇中(这种境遇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一种失重状态),对现实有所承担。这种承担也许比在以往任何沉重的历史境遇中更艰难,更需要非凡的耐心和毅力。这正如王家新所感觉到的“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不能至死和某种东西呆在一起,我就会漂浮起来”[69]。当一切都像膨胀的气泡往上漂浮的时候,敢于抱住石头往下沉的人才是勇敢的。诗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关注是这些可能抱住的石头之一,也是维持诗歌在这一特殊历史境遇中的有效性的合理的方式。“诗歌的‘胃口’还必须更为强大,它不仅能够消化辛普森所说的‘煤、鞋子、铀、月亮和诗’,而且还必须消化‘红旗下的蛋’,后殖民语境以及此起彼伏的房地产公司。”[70]这样的写作抱负对80年代诗歌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2)从叙述的策略上说,抒情的成分减退,而叙事的成分得以增强。诗歌中的抒情倾向在80年代曾经有过其辉煌的深刻(如海子的抒情诗写作),但是随着趋之若鹜的模仿,那种滥俗(烂熟)的抒情再也不能满足诗人对创新的渴望了,事实上,它也不再能够包容诗人新的写作抱负(对当下存在和历史境遇的关注)。于是,叙事作为一种重要手段被引入诗歌中。王家新通过《瓦雷金诺叙事曲》《词语》《临海的房子》《纪念》等一系列诗,逐渐增加了诗歌中的叙事成分,他甚至要求诗歌“讲出一个故事来”[71]。与王家新相比,孙文波诗中的叙事倾向更为典型。他是最早将这种倾向引入当代诗歌中的诗人之一。他写于1986年的《村庄》已显示了清晰的叙事意识。写于90年代初的《在无名小镇上》《在西安的士兵生涯》等诗中的叙事技巧已相当成熟,在诗歌圈内和普通读者中都产生了影响。萧开愚写出了《地方志》《来自海南岛的诅咒》等有力的诗篇,通过叙事和细节达到历史和现实的把握。臧棣将他的一部近作命名为《燕园纪事》。张曙光甚至宣称要完全用陈述句式写出一首诗(他也是这批诗人中较早对日常生活和细节加以关注的诗人之一)。桑克的写作显示了对细节的独特的感受力。在一些一直有叙事倾向的诗人身上,也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如在翟永明身上,这种变化相当明显,在她近作中,原先的自白语调被一种更加客观的叙述方式代替。[72]这种叙事观念的形成,也对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杜甫很受一些诗人的推崇。杜诗的“诗史”性质和精湛的叙事技巧,为当代诗歌的叙事性提供了经典性的榜样。在文言诗歌和白话诗歌的关系史上这几乎是唯一的一次。
(3)80年代的总体特征仍然是崇高和悲剧性的,90年代歌却在严肃的风格中羼入了喜剧性的因素,以在挽歌和喜剧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反崇高”“平民化”或任何一种单纯的风格的胜利,相反形成了一种更加精微而感人的风格,我相信它和悲剧性的崇高一样高尚。这种风格体现在陈东东的《喜剧》中,也体现在臧棣、孙文波、萧开愚、张曙光等人的近作中。80年代尽管提出了诸如“反崇高”“平民化”“口语化”等具有反理想主义色彩的口号,但从那个时代为诗歌提供的阅读期待和想象空间而言,仍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特征,这从那个时期诗歌的革命色彩中可以得到证明。改革、开放等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为大众提供了对未来的美好许诺(包括对个性解放的许诺)和强烈期待,诗歌中的理想主义特征恰好适应了这一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进入90年代,迅速市场化的经济兑现了它的部分诺言,但与之相伴而来的阴影和代价也随之变得清晰可辨。市场的老虎开始吞噬人的个性,在一个高度物质化的世界中,精神的边缘化倾向越来越显眼。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诗歌话语方式被取代已经势所难免。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迅速成长为一个讽刺和喜剧的时代。诗人年龄构成的变化也助长了这一趋势。
(4)由此产生了90年代诗歌一个显著的风格特征:综合性。它总是动用尽可能丰富的语言手段来表达当代人复杂多变的意识和经验。对此萧开愚表白说:“我长时期地训练各种手艺,就是希望培养综合写作的能力,为写一些大型的题材作准备。”[73]以往那种单纯的主题几乎不存在了。臧棣认为“90年代的诗歌主题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74]。而诗歌中的情感“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混同于公众心理或情绪的情感,而是对人所可能有的情感的一种概括”[75]。这种无主题化的倾向造成了阅读上的某种困惑,只是因为公众的阅读定式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改造。
(5)就文本效果而言,90年代的诗歌显示出一种包容性的倾向。诗歌的文本特征变得驳杂,它融入了散文、随笔的文本特征,甚至小说、戏剧的文本特征也被吸纳进来。王家新、西川的一些诗,也不妨归入散文或随笔的体裁内,孙文波的某些诗也不妨说是戏剧独白的片段,萧开愚《来自海南岛的诅咒》等诗则引入了类似小说的叙事性结构。
90年代诗人兼事批评成为风尚,这部分可以归因于批评对解读当代诗歌的无力,更加有趣的是,我发现在诗人的批评术语和批评家的术语中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诗人从自身写作出发的批评对写作的复杂性和辩证性有更充分的认识,而在批评家那里却常常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不能辩证地认识相反的因素,而是简单地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可能也是我们的批评始终不能深入地解读诗歌文本的原因之一。譬如对“个人写作”的理解,在诗人那里始终和时代的历史语境和特殊的话语场相联系,它反复强调的是“历史的个人化”,而在许多批评家那里这个已被诗人赋予了独特含义的诗学概念,却常常被简单地解读为“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对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譬如对诗歌中叙事因素和抒情因素的理解,批评家往往将它们对立起来,好像90年代诗歌特征就是叙事,舍此无他了。而在诗人的理解中,两者的关系却始终处于对立的统一中。孙文波诗歌中的叙事特征在90年代中是相当突出的,但他却一再拒绝将他的诗歌特征概括为“叙事”,而宁肯将之称为“亚叙事”,甚至说“它的实质仍然是抒情的”[76]。他一再强调,在他的诗中“并不存在过去意义上的那种对故事本身的强调,而更多的强调是写作对于事实的叙述过程的重视”[77]。王家新强调在诗中“讲出一个故事来”,他的诗却仍然体现了强烈的抒情性,甚至很难找到故事的影响。作为一个诗人,他很清楚在诗中讲故事的代价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批评家却往往上当。再譬如对于写作的具体化问题,批评家往往将之等同于细节的罗列和堆砌,而没有看到细节中的抽象。他们总是抱怨当代诗歌被无数平庸的细节压垮了。在被举为写得具体的张曙光那里,诗人的努力却是在“具体和抽象之间”,在“多少保持对象的一种原生态”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主观感受进行大胆的夸张和变形”[78]。又譬如对崇高和喜剧、讽刺成分的理解,批评家也总是把它们对立起来,好像当代诗歌一引入喜剧成分就失去了崇高的资格。这种批评对理解当代诗歌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批评界不断以读者的流失责难诗歌,但是这种对诗歌的粗暴解读是否也应该为读者流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我甚至怀疑我们的批评界是否还有能力对精微、复杂、辩证的当代诗歌作出恰当的解读!
原载《诗探索》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