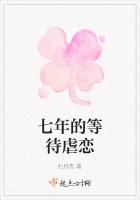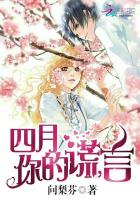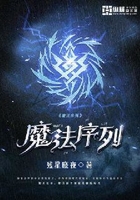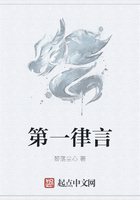李少君
一九九六年初,我得到两本颇有分量的民间诗刊,一本是广州的《声音》,另一本是北京的《标准》,我在仔细读过这两本诗刊之后,发现这两本一南一北的诗刊中部分诗作竟然有着惊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共同的倾向:对现实与当下的关切。这里的现实,不是那种高调的伟大的所谓历史性事件的“现实”,而是一种切近自身与个人经验的或切近生活的客观现实,我想称之为“现时性”特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用“现时性”而不用“现实性”这个词,是因为“现实”主要是空间概念的,多与梦境或虚构相对,而“现时”是时间概念,具有痛切的个人体验中的当下性与现实性。下面,我还是从这两本诗刊和其他一些报刊上的具体的诗作的分析入手。
先来看桑克的《公共场所》(刊《标准》创刊号):
那人死了。
骨结核,或者是一把刀子。
灰烬的发辫解开,垂在屋顶。
两个护士,拿着几页表格。
在明亮的厨房里,她们在谈:三明治
这种火候也许正好,不嫩,也不老
一个女人呆坐在长廊里,回忆着往昔:
那时他还是个活人,懂得拥抱的技巧
农场的土豆地,我们常挨膝
读莫泊桑,紫色的花卉异常绚丽
阳光随物赋形,挤着
各个角落,曲颈瓶里也有一块
到了黄昏,它就会熄灭
四季的嘴时间的嘴对着它吹
阴影在明天则增长自己的地盘
药味的触角暂时像电话线一样
联起来,柔软、缠绵、向人类包围
谁也不知道什么戏公演了。肉眼看不见
平静中的风暴,相爱者坐在
广场的凉地上,数看裤脚上的烟洞究竟有多少。
这不是我们见得较多的那种抒情诗,而是一首描写客观现实的叙事诗,因为个人的情感在其中是不强烈的,但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我们分明感到了某种阴影的逐渐渗透。读这种诗,我们不会像通常读诗时那样随同诗的情感节奏强弱与作者同一节奏起伏,一气读完,而是随同作者的视线移向不同的场景:医院——长廊的女人——阳光——广场的相爱者……我们一个一个场景地看完,诗也就读完了,但我们心底分明涌现出一种阴郁低沉的东西,甚至是尖锐而细的痛与无边的苍凉。
读完桑克诗,我突然联想到近年来诗风大变的于坚,于坚的近期部分作品中坚持用一种“物性词语”的堆积来处理所谓“事件”与“事物”,如“事件系列”诗歌,此一手法至《0档案》发展到极端,相对而言,他的《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刊《诗探索》1995年第2辑)类似我要谈的“现时性”的特点。全诗如下:
这天下午我在旧房间里读一封俄勒岗的来信
当我站在唯一的窗子前倒水时看见了他
这个黑发男子,我的同事,一份期刊的编辑
正从两幢白水泥和马牙石砌成的墙之间经过
他一生中的一个时辰,在下午三点和四点之间
阴影从晴朗的天空中投下
把白色建筑剪成奇怪的两半
在它的一半里是报纸和文件柜,而另一半是寓所
这个男子当时就在那狭长灰暗的口子里
他在那儿移动了大约三步或者四步
他有些迟疑不决,皮鞋跟还拨响了什么
我注意到这个秃顶者毫无理由的躇踌
阳光 安静 充满和平的时间
这个穿着红色衬衫的矮个子男子
匆匆走过两幢建筑物之间的阴影
手中的信 差点儿掉到地上
这次事件把他的一生向我移近了大约五秒
他不知道 我也从未提及
我们比较桑克的《公共场所》来看,于坚的诗更客观、纯粹、具象,类似所谓零度写作,按于坚的说法,是“不要想,而要看”,相对而言,桑克的诗还有些个人的怜悯之情。但显然,这两首诗在某些方面的追求是一致的,即对现实生活的贴近与把握,还有物性词语的较多使用,以及诗人视角的冷静、客观,我称这种诗歌写作倾向为“现时性”追求。那么,何谓“现时性”?就可概括为:诗歌写作中,以一种从个人视角出发的相对客观态度对现实进行描写、叙述和勾勒的处理手法,从而凸现现实生活的“真”的一面,亦即透过表象作被遮蔽的本质的呈现。在具体的写作技巧上,多采用对事物、事件保持一定距离的照相似的或相对的客观显现,但真正的目的,却是透过表象,以现实生活的裸露,显现生活的“真”的残酷之本质,予人以震惊之感。
那么,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这种新出现的“现时性”特征是如何而来又为何而来的呢?
首先,我想要指出的是,“现时性”写作并不是韩东、于坚早期的“口语叙事诗”转化而来的。因为韩东、于坚“口语叙事诗”一般是有一种所谓的对生活概括性的寓言性特点,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个人独特体验和经验,同时也不是具体事件具体场景的展现,因而“口语叙事诗”发展到后来极易雷同,重复,自行消失了。最早清醒地注意对现实题材的处理,并有意识地追求叙事性与经验性诗歌写作的是孙文波和萧开愚、张曙光等。
早期也是抒情诗人的孙文波和萧开愚以及欧阳江河等在一九八九年就创办过一本《反对》杂志,第二年又结集出版一本《90年代》杂志。在这两本杂志中,他们有意识地以“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特征来反对中国当代诗歌中长期占据主要地位的“青春写作”即抒情传统,努力寻求“将诗歌词汇扩大到非诗的性质并将诗之活力注入诗的反面——世俗生活”。孙文波先后创作了《搬家》《还乡》等诗,萧开愚创作了《来自海南岛的诅咒》等诗。诗人柏桦在他的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认为:孙文波的此类诗作具有特有的现实意义,因而也获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柏桦还认为:孙文波诗中的“现实”,或萧开愚、欧阳江河诗中的“现实”并非十九世纪的“现实”,也不是庞德所说的“现代主义”的“现实”,更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某种带有或综合了后现代色彩的“现实”。孙文波本人也表示:“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中反理性的势力仍然占有上风,很多人都要求能够在一瞬间进入写作的中心殿堂……我个人感到是对各种问题的夸大,是心态的浮躁和另一种想建立功名的功利意义:人人都在谈论庞大的体系,谈永恒的主题,甚至谈绝对的形式,似乎中国诗歌真要在一代人手中写到顶峰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并没有越过世界范围的诗歌的六十年代。”因此他主张“写一种更实际的、更不哲学化和更进入我们的处境,或者说写一种干脆就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诗”。萧开愚干脆概括其为“要活生生的,要正在发生的,要要发生的”。在具体的写作中,他们都主张“质朴、节制、准确、直接”。
孙文波与萧开愚等的追求影响到了一批更为年轻的诗人——或可称为“九十年代的诗人”,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诗歌写作成熟于九十年代的诗人,他们使“现时性”的特征更为突出出来,下面我们来看余弦的一首名为《第三者》的诗(刊《标准》创刊号):
秋风中,桂巷新村的电话亭
像一只空洞的信封。一个女郎
一个年轻的女郎向这里奔来,亲爱的,
我不是故意的,而你,也缺乏
足够的耐心。她对着电话辩解,
吐露委婉的心声。粉红色的睡衣
像欲望的亲戚,也许,在她床上,
还留着臀部的形状。什么,
你说什么?要我给你……,给
你一个惊喜,她吃吃地笑了,老练地
掩藏这小小的秘密。一只蟋蟀,
真像一只蟋蟀——她放下话筒的瞬间
BP机又在腰上响起,呵,
诱人的腰。
这是现实中非常平常的一个生活场景,诗人以细致的叙述和描写使这一场景凸现出来,虽然具体到每一个词语和每一句诗不一定有诗意,但整体的氛围却予人以一种新鲜而醒目的感觉:场景的画面感是清晰的,诗人的笔触又是有选择性的,使其活跃灵动起来的,甚至对话的选取也颇有意味;而在这平常画面之下,在细致描述勾勒之外,我们可以感到一种生活的小小的情趣和心底的微微的波澜。这就使得电影镜头似的生活片段具有了诗意,读者读过之后也会有所触动,联想并印象深刻。显然这一类看似平淡的现实题材的处理并不是可以轻易地做到的,它需要语言绝对的准确,诗人的视角独特和观察力敏锐,并采用灵活的叙事的修辞技巧。
另外,九十年代诗人的“现时性”特征显然颇为彻底,对现实也有更准确的领会与处理,对照孙文波与萧开愚的诗来看,如萧开愚的《偶记》(刊《诗歌报月刊》1996年第7期):
有一次我沿着凯江散步,
直走到浓雾散去,远离县城,
看见一群鸭子上河跑向
空旷的河滩,一个男人驱赶,
另一个男人折树枝哼歌
烧饭,我赶忙掉头回走。
本阶级的幸福风景会用爪子
死死抓住它的成员,死死地;
而实际他终生属于另一阶级。
后来河滩在记忆中日益旷阔,迷人,
炊烟的绞索常常系住我的脚踵。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萧开愚的诗中,仍然残留有较强烈的个人抒情情感,由于其自身原是从抒情一派中蜕变而来的。事实上,在孙文波和萧开愚的诗中,每一个词语与诗句都有一定的诗意,萧开愚的诗因此显得很华丽和喧杂,如他的长诗《来自海南岛的诅咒》等。孙文波的诗则呈现庄严肃穆之感,这显然也是因为他早期抒情背景赋予的色彩,因此孙文波曾称他与萧开愚的诗具有“乌托邦”色彩,“现实”不过成了一个构成这一“乌托邦”的手段。
而九十年代的诗人们是与之有所不同的,他们首先放弃了对所谓“乌托邦”的幻想,以真正现实的平视的态度(孙文波与萧开愚更多对生活是俯瞰的态度)来看待现实与生活。他们真正有价值的只在于他们以敏感的心灵和深刻的直觉与洞察力触摸到了生活的真相与本质,所以,对待具体的事件与事物时,他们总是首先将热情冷却,将个性消解。但这种诗歌写作中,需要真正的灵魂与现实的摩擦,因为现实经诗人们处理后,呈现有一种凸度,一种类似版画中的凸现的东西,但那却是刀子一笔一笔地刻划出来的。而在其凹陷之处,则显现一种深度,因为那是灵魂被烙过的痕印。在这样的诗里,也才真正提示出存在之真的东西,诗的深度也才在其中显示。如鲜例写的《铁路处》(刊《青年文学》1996年第6期):
废弃的铁路道旁,这是城中乌鸦
聚集的理想场所
贫穷、凶杀的肮脏的滋生地
已经播种过许多个夏季
它们是些没有户籍的居民
靠拾荒和偷盗来生存
它们只知道行动,不会言说
头发、面颊总是布满灰尘,伤痕和晦暗
它们通常暂住,在
被接受和驱赶的交叉地带
那里是阳光忽略的地方
由此穿行而过的人
总是尽快地逃离,像是在躲避一场即将发生的瘟疫
这样的诗里,才真正显现出一种生存的残酷与真实,呈现出城市中艰难、为人所忽略的一面。而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城市景观中,原来还藏着另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早已存在,只是我们的感知早已麻木,但诗人们却将目光投向了那里,因为诗人用灵魂去感知,去提示被遮蔽的存在之“真”。
九十年代青年诗人的创作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州青年诗人凌越的一部长达47节800多行的长诗《虚妄的传记》(部分章节见《天涯》1996年第4期)。这首长诗本身又可以单独构成一部真正的完整的诗集,这样的形式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先锋诗歌创作中极为罕有。因为诗人们的探索性诗作往往是以单首或最多是组诗的形式进行,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即以前的所谓史诗性创作太重激情,而激情无法持久。而凌越以细腻、全方位的城市生活的展示,他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地叙述、转换、描写,就使得诗本身既有整体感又有连续性。《虚妄的传记》可谓穷尽了年轻一代的当下生活与现时经历,这也可以称为另一种史诗——真正的对于现时性记录和揭示的具历史感的诗歌。其中,场景的捕捉,片段的定格,人物的忽现忽隐,幻想与现实的交叉错杂,时间与空间的随意穿插与拼贴,使得这首长诗真正成为后现代生活经典似的记载。由于全诗太长,我仅摘选一段以作赏析:
第一次置身事外,我尝到甜头。
嗨!真是难得。
女人,爱情以及乱七八糟的政治
被我一起扫进了空无一物的地下仓库
这正是一个理想的场所,我这样想着
一边带上门
对付空洞的早晨,我另有绝活:
我写诗,像一个诗人一样。
诉说痛苦,打发时间,(还真灵)。
有时,也能听到人们在相互抱怨“好家伙!房价涨到了四千五”。
……指针在旋转,已经是九月。
可爱的季节
并不代表难以捉摸的喜悦,
干净利索地,我清除了身上的污垢,
我变得轻松,像一只投身梦想的鸟儿;
但时光盯住了每一个人,喂,你们这些忧郁症患者
怎么样?“还能怎样?”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具有对于当代生活非常敏锐的捕捉力,语言也非常准确、质朴,动用了不少以前诗歌写作中很少使用的修辞技巧如对话等,且与当下生活非常贴切。而整体地看来,这首诗无疑表达着年轻一代在当下生活中的迷惘、困惑与随便,而这是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现时性”写作中,来自生活深处的素材与灵感才真正源源不断,使持久的写作成为可能,也使真正的史诗(这里指对当下历史的诗性处理)的写作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时性”写作真正为中国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持久的动力,因为现实生存的原材料俯首可拾、遍地皆是的。实际上,“第三代”诗人中很多完成自己写作的转变也是借助于这种“现时性”材料的。
“第三代”诗人中,除了于坚、孙文波、萧开愚、张曙光等人以外,同样完成了一种巨大转变的还有翟永明。翟永明早期是一个坚决的女性自白派,高亢、抒情和激烈,所以她新近完成的《咖啡馆之歌》等诗令人大吃一惊,她的诗中也有一种“现时性”的写作倾向,我们试引《咖啡馆之歌》几段:
忧郁,缠绵的咖啡馆
在第五大道
转角的街头路灯下
小小的铁门
依窗而坐
慢慢啜秃头老板的黑咖啡
“多少人走过
上班 回家 不被人留意”
我“昨天 我愿
回到昨天”
一支怀旧的歌曲飘来飘去
“本可以成为
一流角色 如今只是
好色之徒的他毛发渐疏”
我低头啜饮咖啡
……
你还在谈着你那天堂般的社区
你的儿女
高尚的职业
以及你那纯正的当地口音
暮色摇曳 烛火撩人
收音机播出吵人的音乐:
“外乡人……”
“外乡人……”
这首诗整个展现的是一种缠绵伤感的异国生活,但透过细腻的描写、叙述,分明展示的是无根的灵魂的漂泊,甚至也可以说是喻示人类的整个灵魂无处栖息的状态。这种诗是有一种更本质的真实。在修辞上,这首诗有一种“小说化”的叙事方式,追求“戏剧性”与“事件性”,也是以前的诗歌少见的。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诗歌中确实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注意当下生活的把握、领会与处理,以一种叙事的方式,语言要求精细、准确和贴切,甚至还讲求诗中的故事性、情节性,这无疑使得激情写作正日益变得空洞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获得了一种新的推动力与内在的生命力。那么,为什么这种写作一直到九十年代才呈现潮流趋势,又为什么这种写作在当代诗歌写作中成为必要?
首先,我们注意到中国传统诗歌一直较为注重空间感,而忽略时间性(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中,时间似乎也是静止停滞的),以至我们重温无论唐诗宋词,抑或杨炼、海子、骆一禾等的诗歌,印象中留下的只有山水、月亮、花、风景、麦子和美人这些空洞的意象与概念;而很少有什么诗作触摸和深入时代之深处,揣摸普通人之心理,关注灵魂与时代碰撞之深刻际遇,传递时代之普遍情绪。当然,这可能源于中国传统上经济自给自足,社会结构处超稳定状态,文化因而相对封闭并具内在恒定性,诗人们因此翻来覆去重复相同的题材并一直讲究所谓出处、典故,而对时间性及时代变化一向不予重视。而进入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九十年代初以后,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变革之迅速,运动、速度、时间变化之空前急促,乃至空间、场景之快速转换,诗人们更多地感到了时间之流的强烈冲击力,并且意识到不能老是只对所谓的永恒、宏大、庄重的空洞而抽象的主题作反复的摹写,而应对所处之时代作出敏感的反应,把握生活中的变动、实在及新的经验。这就导致了诗歌写作中对于“现时性”的强调,并使诗歌写作演绎化为真正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当下反应,当下创造,当下写作——而非传统诗歌中对共同题材的重复性摹写。这种“现时性”写作坚持经验的绝对现在性,即与时代现实的同步感与即刻性,并呈现出一种流动、敞开状态,具有一定的诗艺上及感受上的延续性,保证了诗歌从时代及具体生存经验中汲取永不停滞的活力,同时也激活了语言的应对能力和开放性,使之不致枯竭。而且,这种“现时性”写作导致的时间上的延续性也使得诗艺能获得持续的递增与变革,使诗歌趋于日臻精粹。在这里,需要加以区别和说明的是,此前,亦有评论家注意到这一现象,如以往的诗歌往往寄望于所谓伟大的激情与天才,这实际上是一个伪造的神话,所以有评论称之为“神话写作”,而将“现时性写作”称为“反神话写作”;同时,“现时性”写作由于来源于时间的急剧变异与空间的不断迁移,因而也就摒弃传统诗歌写作注重的所谓空间感产生的整体感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摒弃了对某些评论家所称的“史诗写作”的追求,而相对的视“现时性”写作为“反史诗”写作,当然,这些均只突出“现时性”写作的某个方面的特点,还未能提示现时性写作最重要的特征是:时间性及与此紧密相联的现实性。
另外,从诗自身的历史来看,若考察中国自白话诗以来的历史,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诗人们在遭遇现实事件时的无力感。迄今为止,可以说尚未出现过一部堪称深入幽微地揭示一个时代之隐秘的诗歌,无论是郭沫若,抑或是何其芳、卞之琳,不是肤浅地对现实的讴歌,就是囿于个人的浅斟低唱似的歌吟。中国诗人在真正需要潜心把握现时代之脉络与探究现时代人之潜幽心态尤其是具体的个人性事件时,总是显得窘困和尴尬,这到底是现代汉语这一刚刚创生的语言本身的表达力有问题,还是现当代诗人的质素本身有着缺陷?而且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诗歌现象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另外,如果说徐志摩、穆旦、冯至、艾青等人的努力对现代汉语的成熟都有过不小的贡献,并真正地激发了白话这一语言内在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北岛、多多、食指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彻底救活了一度陷入窒息状态的汉语言,使之潜在的表现力,内在的张力和伸缩性都达到过一个白话诗诞生以来的高度。但当代诗歌同样又遭遇了现代诗歌在现时性问题上的困境,北岛巧妙地以个人高亢的抒情来避开对现时性事件与遭际的揭示,顾城干脆转入梦幻般的呓语,即使到了“第三代”诗人手里,情况也未见得更好,海子、西川、柏桦、吕德安们继承的是传统的抒情特长,在他们的诗中,看到的仍然只是空旷的呐喊抑或哀婉的回忆。而韩东、于坚、李亚伟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他们只能对现实平面的客观的描述或是概括性的寓言式的影现。因此,“口语叙事诗”后来实际上地泛滥成为“口水诗”,连普通的刊物都对之加以拒绝,海子似的抒情诗命运相对地好一点,因为里面毕竟有些诗意和修辞上的讲究,因此,现时性的把握和处理成了当代诗歌发展最需突破的障碍。也就是说,“现时性”写作可视为诗人随时随地面临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具体事件,但这种日常生活和个人事件决非对生活和事件的简单的概括,而应当是灵魂在此种生活和事件中的际遇和处境的审视和内省。我们知道,激情的时代,诗歌可以不依赖日常生活的原料,而专注于内心想象力开创性的拓展与延伸,但平庸时代的诗歌如若不以个人经验与内心生活为依赖,就会变得空洞可笑,海子们所处的时代毕竟过去了,严酷的现实逼迫诗人们面对平庸琐碎的事实。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诗歌可获得更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以往的历史中(五四以来),诗艺磨砺与精湛,尤其是向深度的拓展(在这里,深度是作为与激情诗歌所追求的所谓高度相对立的一个词),一再地被血与火的历史所打断,现在,似乎是沉下心来解决当代汉语如何适当而恰如其分地揭示日常生活和个人事件真相(这里的真相,可作存在主义术语中的“真的事件”的替代词)的时候了。这是更难的,也是一定要迈出的一步,否则,汉语就会失去其内在活力,重新变得空洞、自大而实际上内无一物。
还有,从另一方面来说,或者说从诗人自身来说,实际上所谓的抒情相对来说是容易一些本能一些的,抒情本身即是一种青春性的主要特征。一般人身上都潜在地隐有这一特征,如初恋的狂热等,都可算是这一特征的外在流露,而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他应该越过稚嫩的尖细的大惊大怪的空洞的青春的高音,而进入成熟的沉稳低沉的中年的低音,(欧阳江河也曾将这两类写作加以过区分,前者为所谓“青春写作”,而“现时性写作”为“中年写作”);他也应该更加精湛,更注意技巧与修辞,有处理现时性题材的能力与灵活,这在诗艺上才是一个成熟诗人的标志,这也是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看看盛唐与晚唐诗歌的变化,杜甫早期与晚期诗歌风格的内在嬗变,就可略见一斑:看看欧美十九世纪雪莱浪漫主义与二十世纪中艾略特等诗的不同,也可以看出这种区别来。尤其联系到现代,中国诗人一向擅长写抒情诗,郭沫若也好,艾青也好,何其芳也好,海子也好,骆一禾也好,但中国一直没有成熟的叙事诗人,并很少关注现实的生存与日常状态,有过的只是一些写假大空题材的所谓叙事诗,例子我不再多举,例如歌颂某一重大节日之类,艺术上极为幼稚可笑,完全没有成竹在胸、谨慎细致的成熟风度。叙事一路的诗歌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始终是弱的,这也表明了现当代汉语诗歌的不成熟,不能如欧美诗歌在二十世纪以来取得长足的进展和稳定持续的发展。
所以,“现时性”写作的出现,可以说不仅仅表明中国当代诗歌一种新的倾向,也表明当代汉语诗歌正在走向真正的成熟,而为之付出努力的青年一代诗人的工作是尤其值得称道的。这种努力也将挽回八十年代末以来当代诗歌陷入低谷的趋势,使当代诗歌写作获得一个更长久和更实在的基础和源泉。
原载《山花》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