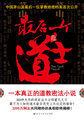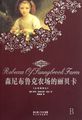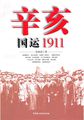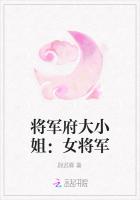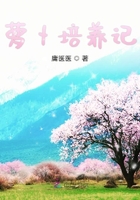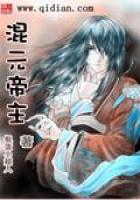前清秀才张泽
在我故乡祖茔累累的坟包中,我所能说出来的辈分最高、名气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坟墓的主人公,恐怕就是这位老先生了。他是我祖父的祖父。他是我的高祖父。
在我父亲生前保存的相册中,居然奇迹般地保存着这位老先生神采奕奕的照片。照片上的他长袍马褂,瓜壳帽,小山羊胡,手捧一本厚厚的《康熙字典》,端坐在太师椅上,脚下是一盆半残的菊花,旁边是一个摆放着地球仪、座钟和茶具的高脚茶几。从这张照片上,我看不出他是否留有辫子,也看不出他的确切年龄,但从这张照片上,我能够看出他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小村庄的地位和身份。确实,在一百多年前,对于李鸿章、张之洞一类的大人物,拍摄一张照片似乎并不稀奇,但对于一个乡下人,却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顺便提一下,就在十年前,在我母亲生活最为困顿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收古董的贩子出一百元想收购这张照片,被我的母亲拒绝了。我不知道母亲当时是出于什么心理拒绝的,但我知道母亲不经意间的那次拒绝,却为我今天能够大言不惭地炫耀我的家学渊源、书香传家留下了生动的证据。
从族里的云谱中,我了解到我的这位高祖姓张名泽字润田,小名仁义,排行老三,娶妻黄氏,享年七十三岁。从叔祖父不太系统的述说中,我还知道这位高祖曾经中过秀才,并且曾是代州童试中的第三名;又说当年报喜的人半夜进村,铁炮放得惊天动地;又说当年老先生曾在崞县意大利人教堂授国学,每月十二块鹰洋,后来意国人曾劝他入意大利国藉,被他严词拒绝,又劝他改信耶稣,他说吾学儒学,吾信孔子;又说老先生勤俭持家,平日洗脸拧毛巾上的水时舍不得用劲,怕把毛巾拧破,只是用手攥得挤水等等。这些我都不曾亲见,而且也无法想象出当年那些生动、鲜活的细节,但老先生用积攒的鹰洋盖得房子和置买的土地,我却亲见过。据我叔祖父讲,老先生盖房子的时候,他刚会搬砖。
那是三间平平常常的旧式瓦房,有一个用砖雕刻着琴、棋、书、画图案的较为精细的照壁。包括我这一辈的子孙后代在内,那间老宅曾经庇护过老张家上上下下五代近百口人,而且,直到今天,尽管已经久无人居住、修缮,但它依然傲立风雨中,散发着某种神秘久远的气息。
而且,一直到1992年春天搬出这所老宅住进新居前,我和我的父母以及姐弟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就留在了那里。搬出老宅一年后,我的父亲身患绝症,一病而去。又十年,我的母亲在新居中苦度八年孤独、凄苦的寡居生活之后,也撒手西去。
同样还是据我的叔祖父讲,老先生生前在用从意大利人那里挣来的鹰洋盖起三间瓦房的同时,又购置了村东的近一百亩水地、旱地。这些土地,儿时的我可能曾经在上面打过猪草,然而迄今为止,我仍然不得而知它的确切位置。但是后来因为这些土地,我们家被划为富农,以至于在我六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祖父被抓出来批斗时的情景,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据说我高祖父去世的时候正闹日本人,准备为他做三周年时立得的墓碑已经雕刻好,但因为兵荒马乱始终没有立成,最后,成了“农业学大寨”时村里修红旗幸福渠时的一块普通石料。我的舞文弄墨一辈子的高祖父,终于同他的乡邻们一样,躺进了一座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最普通、最不起眼的土堆下面了。但是,他在他的后世子孙尤其是包括我父亲和我自己在内的子孙后辈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苦恼——那就是,他让我们时常告诫自己,我们是读书人家,万事不可大意;族无犯事之男,家无再婚之女;大块文章光吉地,山河锦绣壮幽居。
我的高祖父生有二子,长曰化龙,次曰佑龙。佑龙大名为张鸿栋,字子国。
他就是我的曾祖父。
汝深肖汝祖
一生以读书人自居并自傲于偏僻小村的高祖父,一定对于他的儿子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从他为他的儿子起的小名佑龙、大名鸿栋、字子国可以看出来。但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中,一个人想靠读书来实现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也就注定了我的曾祖父尴尬但又很富有幽默和人性的一生。
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属于那种严肃、严谨的人,或许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从他们嘴里,我几乎得不到一点关于我的先祖们的信息。但是我的叔祖父,却总喜欢津津有味地向我讲述那些关于我们家族的久远的故事。我的叔祖父在讲起他的秀才祖父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一种不知不觉的崇敬和自豪,但讲起他的父亲的时候,虽然没有不恭,却总免不了有一丝揶揄和善意的调侃。
很小的时候,听我叔祖父讲高祖父的故事,不由人不油然而生一种振兴家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听讲曾祖父的故事,却会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轻松和会心的微笑。有好多次,当我绘声绘色地向我不苟言笑的父亲转述我听来的故事时,我的父亲都会爽朗地大笑,并亲昵地说,在诸多方面,汝深肖汝这位先祖。
叔祖父给我讲述的有关我的曾祖父的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拴驴的故事。他说,那时我的曾祖父也就是他的父亲大人,也曾子承父业教过一段时间私塾,但由于嫌弃学生们的读书声吵得耳乱,又说批阅文章时学生们乱糟糟的文学搅得眼花,于是不到四十岁他便辞职赋闲在家。夏天,他会躲在树阴下摇一把鹅毛扇子;冬天的时候,他便坐在向阳的地方晒一晒肚皮。发生拴驴事件的具体时间,大约是在一个初夏暖洋洋的下午,因为据我叔祖父讲,那时洋槐正开花、农事正忙,村里静悄悄的,老老少少都下地锄头遍玉米去了,我的曾祖父像往常一样睡足一个时辰午觉后,一手拿一个小抿壶,一手拿一把鹅毛扇,例行公事般地踱步到不远处的场院里,去喂他挂在楸树上的鸟笼子里的胡伯劳。推开场院门,他看见我家那头黑毛驴正挣开缰绳,旁若无人地啃食种在墙角的金针花——那是我曾祖母的命根子。据说,我的曾祖父看到这个情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而是只犹豫了片刻,便转身轻轻关上场院门,不紧不慢地踱到村东边,去叫他正在忙着锄头遍玉米的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回家去拴那头脱缰的驴子。据我后来推断,那时我的曾祖父年龄不足四十五岁,远不到拴不住一头毛驴的年龄。而且,后来我也曾就此事向我的祖父证实过,我的诚实沉默的祖父只是笑了笑,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想这件事大约就是真的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我这位处惊不乱、超然物外的曾祖父悠闲高雅的魏晋名士风范和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的叔祖父给我讲述的有关我的曾祖父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给我祖父娶亲时发生的一些故事。
据我叔祖父讲,我曾祖父对家务事无论巨细,从来都不去过问哪怕一点,但当我祖父娶亲的日期定下来之后,他却主动过问过一次,并且很认真地把日子记在了纸上。这件事很让大家惊奇和感动,大家都觉得不管我曾祖父平日怎样闲散怪诞、万事不管,但对于自己长子的终身大事,毕竟还是很当回事儿的。可是,到了我祖父准备迎亲去的前一天,也就是亲戚朋友们准备来家里上事宴的那一天上午,我曾祖父却突然把自己的铺盖卷打包好,说是要去村外的奶奶庙找看庙的老头去住,他的理由是害怕家里这几天吵闹得他休息不好。我曾祖母从来都是顺着他的性子,这次变了脸跟他理论,他却背了一段《好了歌》里的“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临末,他又举例说,岳飞岳鹏举未出世便丧了父,照样娶了县太爷的女儿做娘子,又立了惊天动地的功业,我这次只是出去躲几天清闲,又不是出家,你们阻拦我干什么。大家看看拦不住他,便任由他去。
就这样,在八十年前那个风和日丽初夏的上午,我的曾祖父牵着我家那头黑毛驴,驮着他的那卷简单的行装,在众人哭笑不得的表情中,大摇大摆地消逝在了我们村外那片淡烟似的小柳树林中。
许多年后,读嵇康的《幽愤诗》,读到“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句子,联想到我的叔祖父说过,我的高祖曾多次责备他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李、杜,喜阮、刘”,我似乎忽然理解了,我这位在族人和亲人眼里放诞怪异的曾祖父丰富的内心世界。
据说我这位曾祖父行为虽然有些怪诞,为人却是极其温和宽厚,一生中几乎从未与人争执过,也从未责骂过他的儿女和子侄。又据说老人家不到五十岁便患了高血压等多种心脑疾病,而且一生中既没有吃过什么药进行治疗,也没有看过什么大夫,但一直活了八十多岁,最后无疾而终。
我的曾祖父娶妻何氏,一生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小名张保堂、大名张烈,是我的祖父;次子小名张俊堂、大名张熙,就是我的叔祖父。
祖父和两个祖母
回望我的祖父和他的两任妻子的故事的时候,正是谷雨刚过的日子。
遥想此时我的故乡,满村的枣树应该刚刚发芽,村边的宾果树粉白的花朵也应该开得正盛。但是,屈指算来,我的第一位祖母,也就是我父亲的生母去世已经六十五年了,而晚她四十年去世的我的祖父,去世也近二十五年了。回想这二十多年来,总是用一次次的泪水,送走一位又一位的亲人。
那些真正爱过我和我爱过的人们,正在一天天减少;那些亲切熟悉的场景,也正在一天天远去,抚今思昔,怎不叫人黯然魂断。
一
在我们崞县那一带,有一句民谚说,愣头老大二奸臣,三阎王四判官。意思是说,每户人家家中的老大,往往都是忠厚老实的,而越往后排的儿子便越刁钻奸猾。我在这里引用这句民谚的意思,并不是因为我是老大而想有意抬高我们做老大的地位,贬低那些次子三子四子等等,我只是想以此引出我祖父的故事。
我祖父从小老实、勤快、寡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任劳任怨。据说,当年服侍我曾祖父时,我叔祖父虽然也算孝顺,但累得烦了的时候,总免不了发几句牢骚,而轮到我的祖父时,无论我曾祖父一夜折腾得要换几次被子,喝几次水,从来都听不到他老人家说一句怨言。再比如,那时候,我们家喂着两头毛驴,割草、起粪、半夜喂草等苦差事、累差事,一般都是由我祖父来干,而冬闲时把驴拴到场院晒太阳或者正月里牵着毛驴去游喜神一类的轻活、闲活,则由他的弟弟——我的叔祖父理所当然地来干。但是我的祖父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怨言。
当然,类似的事情一定还有很多,而那时我还不曾出生,没有亲见,而我的祖父又不愿讲,我的叔祖父又不肯主动讲,所以,在这里我也不便妄断。
我叔祖父跟我讲过的是,据说那时我的曾祖父在他们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对他们说,你们也已经粗通了文墨,这世道这么乱,再读多少书也没有用,再说一户人家如果连着三辈教书,恐怕想喝西北风也喝不饱,你们还是学习种地或者经商吧。就这样,我的以书香门第自居的苏鲁老张家,长子张保堂种地兼开了酒坊,次子张俊堂到老崞县城学做了买卖。而那时他们的祖父,也就是老秀才张泽公给他们起的大名——张烈和张熙,除了许多年后贴在寿器上,至死也再没有使用过。并且,除了他们自己,同村里的男女老少更是无一人知晓。
二
我没有问过我的祖父和父亲,但据我推断,我的祖父娶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我父亲的生母任家沟郭氏贵桃的时候,他大约二十四岁,他的妻子大约十九岁,据说那是个性格温和、体态轻盈、肤色稍有点黝黑但长相标致的女子。据说我的祖父很喜欢他的妻子,他们结婚十余年间几乎没有争吵过一次,也不曾红过一次脸。但是,在我父亲九岁那年,我的祖母却忽然患了伤寒,为防止传染给他,被送回五里地之外的娘家救治,结果,被邻村庸医两副虎狼药下去,气若游丝,命似累卵。我祖父领着村里人半夜心急如焚地赶去,只用门板抬回一具已经渐渐僵硬的尸体。我的祖母就这样直至去世前,也再没有跟他心爱的丈夫和儿子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道上一个别。
我遥想六十五年前的那个初春的夜晚,在远处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和屋内油灯如豆的灯光下,我的年仅二十九岁的祖母,临咽气前那一刻,一定心存不甘、死不瞑目。
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允许再进祖宅的。因此,我的祖母当天半夜被抬进离我家祖宅不远的场院内,入殓在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中。我无法想象六十五年前那个初春的夜晚,面对这猝不及防的灾难,我的能干又要强的曾祖母和她沉默寡言的长子——我的祖父是怎样挨过的,我也无法想象我的超然物外的曾祖父,面对他温顺恭谦的长媳突然去世作何感想,但我知道,那时我的也在病中的父亲是被瞒着的。
据说我的祖母发丧那天,我的父亲听到隐隐约约的唢呐声,问看护他的本家的一位老奶奶这是谁去世了,那位老奶奶别过脸去含泪告诉他说是本家的一位老爷爷去世了。我的父亲再没有问什么,但半月后,当我的父亲病好了的时候,却再也找不到了他的知冷知热的娘亲。
据说,那时每到我父亲哭着找娘亲的时候,我的叔祖父就领着他到村外一个废芜的园子里去摘杏花或者去村西的小树林里去捕小鸟。直到半年后,我的父亲才被领到村东边寄埋着他的娘亲的孤零零的坟包前,那时的坟包经过一整个夏季和半个秋季的装点,已经芳草萋萋。我无法想象那时我父亲幼小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撕扯和震撼,但后来翻阅我父亲少年和青年时的照片,从他沉静的眼神中,我总是能读到一种无边的忧郁和哀伤。
而且,我永远也无法忘记,25年前,当我的祖父去世,需要把我的祖母从寄埋的地方迁回祖坟与他合葬时,我的父亲背着盛放着他母亲骨殖的小木盒,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时的苍凉的背影。那时,我父亲已经头发花白,那是他同他魂牵梦绕的娘亲分别近四十年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三
据说,那段时间,沉浸在丧妻悲痛中的祖父,更加沉默寡言,也更加疼爱他与爱妻伉俪情深的唯一结晶——我的父亲。并且,据说他曾暗下决心此生再不续弦。但是,到底架不住夜深人静时年青健壮的肉体的苦苦折磨和旁人的一再劝说,两年后,他再一次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悲伤地做了新郎。新娘是年近三十的我的第二个祖母。据我父亲回忆,初婚时的新母亲对他还算不错,但当陆续有了自己的子女时,情形便有了不同。
我自己从小在父母亲切的呵护下长大,没有体验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我们乡里有一句老话,叫做宁跟叫街的娘,不跟做官的爹。大概就是这种饱尝血泪的人们总结出来的。
我祖父生前最喜欢看的戏是晋剧《芦花》,那是一部反映一个继母和两个不同儿子之间故事的传统剧。我不知道我祖父看它时,怀有着怎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情。据说,那时我的祖父也曾经努力过,想竭力维护一个公正的丈夫和父亲的形象。但是,婚姻家庭里的事又是那么扯不清、道不明,而一个男人在家庭中又不具体掌管琐碎细微的事情,而一个孤儿的心灵又是那么敏感、细腻和脆弱,因此,要想让我父亲重新感受到过去那种幸福和温馨,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并且,据我父亲后来回忆说,凭良心讲,要说他的新母亲曾经怎么打骂过他或者虐待他,那倒也确实没有过,但心里总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沉思了一会儿,他忽然叹了口气又说,大人磕打小孩哪还用专门去磕打,平日里,什么事儿也记不起你来,你就算完了。我一直无法准确地理解和领悟这句话,我想这样的体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大概是很难感受和想象得到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祖父是很勤快和俭朴的,也是很慈祥与和善的。至少,他从小到大没有责骂过我哪怕一次。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他总是戴一顶草帽,在广阔无边的田野上劳作,即使收工回了家,手里也总有干不完的家务活。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据说生活作风也十分过硬,用我们村一位读过《红楼梦》的老先生的话评价,苏鲁村除了东庙上那两只石狮子干净,就数大南胡同的老保堂干净。
那是一位很刁钻的老学究,我想他如果能给我祖父这么高的评价,那说明我祖父一定是名副其实的。直到此刻,闭上眼睛,我还能看见我祖父站在小巷深处,远远看见我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和欣慰;我还能看见六岁那年的正月十五,祖父背着我去崞县城看烟火时的情景;我还能看见每年八月十五时,祖父架起炉子给我们打月饼时的情景。那时有一部叫做《马背上的摇篮》的电影,里面有一首插曲唱道:“八月十五月儿圆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甜又香呀,一块月饼一片情呀……”
我想,如果没有后来的事情,祖父慈祥的笑容和这首歌曲亲切优美的旋律,一定会永久地留存在我心灵深处最温柔的地方,没有一丝瑕疵。
四
祖父给父亲和我心灵上留下的一些伤痛是在他去世前那几天。那是1984年的初春,我发现我们家族的许多事情,都喜欢发生在这么一个生气盎然的季节。
春风的时候,我祖父还能下地去松土撒粪,清明的时候忽然感到浑身无劲,而且眼白和皮肤逐渐泛黄,嘴里发苦。我父亲和叔父都吓坏了,赶忙领他到地区医院去检查。那是距我们故乡近六十公里的一个中小城市,当年的忻州行政专署就设在那里。当日他们父子三人合住在一个三人间,一直充满亲情和伤情地聊天到深夜。据说我祖父甚至交代了后事,他说我父亲一个人靠教书挣得那点钱,供两个孩子读高中和养家,负担很重,希望我叔父能帮一帮我父亲。他甚至还交代两个儿子关于身后一些遗产的处理情况。说着说着,父子三人都哭了,我父亲和叔父安慰我祖父安心治病,说一定不会有什么大事,而当时他们自己也确实不相信会有什么大事。现在想来,那大约是我父亲有生之年与他的父亲和弟弟最后一次最充满亲情和感情的一次聚首。
第二天是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当第二天的黄昏快要降临的时候,我父亲和他的同父异母弟弟不得不面对一个冷酷的现实:他们一向勤快健壮的父亲被确诊为肝癌,而且最多还有三个月的生命。背着我的祖父,他们兄弟二人相对而泣。那一年,我祖父七十二岁,我父亲四十六岁。而十几年后,当我和我的弟弟面临同样的灾难的时候,我才二十六岁,我弟弟十六岁。
我那被医生判除了死刑的祖父镇定自若地回到了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几乎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就和我的祖父母分院另住着,我记得那些日子,每次周末放假回来,我都和我的姐姐去我们祖父母家中看望我们病中的祖父。一开始,他还能坐在街门口,再后来,只能坐到屋檐下,最后,就只能坐在炕上了。
当我们走的时候,他也不流泪,只是坐在玻璃窗前静静地望我们。当我们走很远了,还看见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于是我们的泪便流满了一脸。那时我们幼小的心中真的充满了一种很深刻很深刻的伤痛。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了解我的祖父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天,对我的父亲说过些什么。但我记得,在祖父去世前两天的一个凌晨,我的父亲伺候完他回到家里,面容枯槁,神情沉痛,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而且,一进家门,就抱着头蹲在地下失声痛哭,仿佛一个受了欺侮无处诉说的无依无靠的孩子。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那样孤立无助和痛不欲生。
两天后,我的祖父带着他的全部秘密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七十二岁。
如今,我的父亲长眠于在他父亲的身边也快十六个年头了,我不知道在这16年中,他们是否父子情深如初。我也不知道,我的祖父是否向他忍辱负重十几年的儿子解释了当年责备他的真正原因,但无论怎样,十六年来,每到清明节去他们的坟前祭祀的时候,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种无端的悲凉和苦涩。
五
我的第二个祖母同我的第一个祖母去世时一样,也是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初春季节。但所不同的是,她的寿命比我第一个祖母超出近两倍。那是2000年初春的黄昏,当下地春播晚归的村民们进村的时候,忽然发现住在离村口不远的我的祖母的院子里烟雾滚滚,仔细看看又不像是晚饭的炊烟,冲进去一看,我祖母一人居住的小屋火光闪闪,我八十六岁高龄的祖母倒在地下,身边是一小堆划过的火柴梗和燃烧的柴禾及方便面塑料包装袋。
噩耗传来的那天,我正好也在故乡。我寡居的母亲听到与她多年前有隙的婆母去世的消息,没有流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表情,相反表现得极为惋惜和不安。按照我父亲生病及去世时的先例,许多人劝我母亲不要再去管这件事情,但我的母亲还是郑重地找出那些孝衣孝帽,让我穿戴好以后,按一个长孙的身份前去守丧。那个黄昏,我在许多村里人和族里人惊愕的目光注视下,跪倒在我的第二个祖母的灵柩前。我没有失声痛哭,但我的眼里淌下了泪水。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泪水。毕竟,从我记事以来,我就是喊叫着这个如今长眠在这里的逝者“奶奶”长大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谁也免不了要有私心,谁也免不了要犯一些常人都可能犯的错误。
死亡,以及共同经历和体验过的不幸,终于使两个心存很深芥蒂的婆媳和解。回想起我的祖父母与我的父母生前的许多往事与最后几年的恩恩怨怨,心中总有无数的唏嘘与感慨。作为我同样的至亲和逝者,在这里,我无意评判他们的对错是非,我只是尽量根据我的记忆,把他们较为客观地记述下来,以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不得不说一说我的叔祖父
在我家族所有的长辈中,我的叔祖父大约是在我的文章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
确实,在我的童年乃至整个青少年时期,他也是给我讲述家族兴衰史和灌输家族荣誉观最多的一个长者。在这方面,甚至超过我的祖父和父亲。我记得在我祖父临终的时候,对于我——他的长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如果我一旦考不上学校,将来娶不下媳妇该如何是好。而我的叔祖父,对于我关心最多的却是能否光宗耀祖,振兴家声。我猜想这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概是与我作为农民的祖父和作为商人的叔祖父,他们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阅历和见识有关吧。
我觉得相对而言,我的叔祖父的梦想更高远,而我的祖父的梦想则更实际。
前面已经提到过,我的叔祖父大名张熙、小名张俊堂,排行老二,属兔,享年92岁,自称为苏鲁老张家有史以来第一位男寿星。他一生的性格跟他的属相一样,聪慧、善良而又胆小谨慎。终其一生,他的人生定位不过是一位个人资本不超过五百块大洋的小商人。
但是,上学时,每每读到韩愈《左迁至蓝田示侄孙湘》那首千古名篇的时候,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这位或许连韩愈这首诗也没有读过的叔祖父。我的叔祖父也是早年丧子,视我这个侄孙如嫡孙一般,在这一点人生际遇上与韩愈相同。尽管除此之外,我的小商人叔祖父与韩退之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圣贤无法相提并论,但在对我个人的人生影响上,我觉得我的叔祖父甚至远远超过这位百世宗师。
那一年,我叔祖父按照他父亲弃文经商的思路,十几岁便到崞县城当小伙计学做买卖,一做就是三十余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的时候,他们的小店已经积累了上千块大洋的资产。后来,随着进一步的“国进民退”,到他快五十岁的时候,他便被早早劝退,闲赋在家,成了一名每个月领二三十元退休金的商业系统退休小职员。按我的推算,我的叔祖父并没有认真地读过多少书,但对于国家大事、社会道德和千年百代的旧事他却特别关心,尤其对于家族,他仿佛有一种特别强烈、与生俱来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由于他的儿子在二十岁时因病不幸去世,对于我,他的长侄孙,他便抱有了太多的希望。小时候,他经常向我讲述他的秀才祖父的轶事,反复给我灌输光宗耀祖的思想。当我考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他更是兴奋不已,逢人便讲老张家的祖宗,积下了德,祖坟里有风水,并从自己不多的退休金中拿出一点钱资助我上学。从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到他八十五岁以前,每到大年初二,他总要亲自带领着我们去祖坟里祭祀。他把我们领到每一位先人的坟墓前上香烧纸,然后向我们讲述墓主人的历史。归去的路上,他继续向我们灌输光宗耀祖、振兴家声的思想,并指着一个个无人祭祀的荒坟,叹息地说,你看这户人家绝了后嗣,断了香火。有时他也给我们背诵一些诸如“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鹿得食而寻群,蚁得食而报众”一类的不知是古诗还是古训的东西。
同时,或许是当过几天公家人的原因,我的叔祖父虽然崇尚祖先,但很少相信鬼神。据说那一年盖房子,别人都劝他看一看阴阳,择一择日子,他却说共产党盖了那么多房子,从来不看阴阳,只插几面红旗就行。于是他也只插了几面红旗,结果,他刚刚订了婚的儿子在房子盖好不久,却很巧合地一病不起而逝。我的叔祖母跟他大闹一场,埋怨儿子是他害死的,他自己也十分哀痛,但依然不肯相信世间有鬼神之事。
那一年我父亲病重,我叔祖父和叔祖母每天柱着拐杖相互搀扶着来探视。我父亲去世的那天早上,一大早,我年近八旬的叔祖父就老泪纵横地赶来,拉住我的手反复哀叹,天塌下来了,天塌下来了,老天杀人没深浅呀!
这一幕至今还映在我脑海中,常常让孤立无助中的我深感亲情之温暖。
那一年,我的叔祖父已经84岁了,但他依然头脑清晰,身体硬朗,一顿饭能吃二十多个饺子,只是视力越来越差,用他的话说仅能模模糊糊通路而已。正月初二,他领着我们去祖坟祭祀,祭祀完后,无限伤感地说,这是最后一次领你们上坟了,下一次来,恐怕就是被八个人抬着来了。然而,第二年,也就是他八十五岁那年,他依然领着我们上了一次坟。那一次大概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就在那年正月过完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生活了八十多年的村庄,被接到崞县城的女儿——我的姑母家安度晚年。
他和我的叔祖母是哭着离开村庄的。在日薄西山的垂暮之年,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熟悉的小院,离开安息着自己祖先和儿子的村庄,我叔祖父心中的那种伤感、哀痛和无奈,大概不是常人所能体验的。
从那以后一直到去世前,我的叔祖父和他相依为命的老伴——我的善良慈祥、后来有一点老年痴呆症、总嚷着回家的叔祖母,几乎再没有回去过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和亲亲小院,直到相继去世后灵柩被运回去。那时,每次我去看望他们,作为一个孤儿的我和作为一对游子的他们,总是在无限伤感的泪水中匆匆地相聚又分别。
而且几乎每次,我的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的叔祖父,总要摸索着把我送到街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2006年春天,我的叔祖父像一个安静的孩子一样悄然离去,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园,回到了他的先人和子侄们安息着的亲亲祖茔。在他临去世前那一年,他为自己拟定了两副丧联和一通碑铭,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能够用上。
他自拟的第一副丧联是“为国家勤劳服务,蒙邓恩幸度晚年”,第二副是“过光景节约俭朴,做事情小心谨慎”。他为自己拟定的碑铭是“例可杖于国故显考张翁讳熙字子明之墓”。
他特别强调,按照古代惯例,年龄超过八十岁的老人上朝廷见皇帝时,就可以拄着拐杖不用下跪了,因此,他的墓碑上一定要刻上“例可杖于国”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