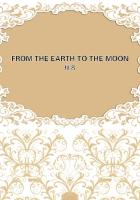张仃被捕后被判刑三年有半。因为不满十八岁,有关方面“念其幼小无知”,也因为各类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实在没有张仃的位置,只好将张仃送往苏州的“反省院”了事。张仃调皮、聪明、个子又小,再加上他年龄尚幼,正处在发育中,怎么看都是个孩子,让任何人都难以将他和坏人或者“赤色分子”挂上钩。因为在上世纪30年代国统区的许多人眼里,赤色分子就是坏人,最不济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幽灵”——即一般中国人心目中的鬼类或神秘之物。对30年代国统区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赤色分子是传说,是谣言,人们仅仅是在风闻中听说过它。而传说中的幽灵,无一例外总是张牙舞爪、青面獠牙和凶神恶煞的形象。但苏州反省院中的张仃,却是一个瘦小、白净、满脸稚气的孩子。张仃的如许形象,很快就使看守们放弃了应该具有的警惕,更有甚者,张仃还很快和反省院的看守结成了要好的“哥们儿”关系——这差不多算得上一个“剿匪”不成反被匪“剿”的小小的、成功的战例。这一有趣的成功战例,使张仃即使在反省院也未曾放下过画笔。当1935年他被保释出反省院时,居然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带出了创作于监狱的三四十幅漫画作品。
事情说起来还真是有趣。就是在苏州的反省院里,张仃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上海著名漫画家张光宇、鲁少飞主办的漫画杂志,尤其对杂志中张光宇的漫画作品印象深刻。张光宇的漫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仃后来尖刻、犀利的画风。这恐怕更是“剿匪”者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将张仃误做赤色分子、革命志士抓进了监狱,却没有想到后者径直把监狱处理成了自己的大学,而且还有人管吃管住,站岗放哨,享受的竟然是高等学生的待遇。这是一件非常具有幽默性质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张仃的漫画虽然毫无幽默感,或者很少具有幽默感,但他的漫画经历、人生经历,却从来都不缺少幽默感。苏州反省院中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一个开端罢了。
张仃带着他的漫画从他的“大学”毕业出来了。但此时此刻漫步在街头的张仃,除了那几十幅漫画,早已身无分文。生计问题又一次被摆在眼前,成了必须要妥善解决的头等大事。联想到自己是左派,自己也是以左派的名义被误关进局子里去的,张仃于是就将一幅以水灾为主题,一幅以罢工为主题的漫画,寄给了当时相当有名的左翼刊物——黄士英主编的《漫画生活》。一方面是想找“同志”(假如同志真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糊口。没想到最后左翼拒绝了左翼,看来国共两党在左翼的标准问题上,和在其他事物的标准问题上一样,还相当的不一致,还须长久地切磋、商榷和谈判。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特别难以理解。当时的共产党正处于地下状态,蒋介石正在拼着吃奶的力气围剿共产党的“苏区”。而在国统区内,共产主义分子被统称为“赤色”人士。在国民党的宣传中,这伙人实行的是“共产共妻”的政策。相较于正常的人性,相较于国统区内绝大多数正常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这确实有些骇人听闻,也确实有些大逆不道。因此在国统区内,许多人闻赤色变。而“赤色”人士这个“雅号”的得来,排除其他所有可能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党旗是红色的。一件事物的外表的颜色总是最打眼、最直观的,哪怕它仅仅是一个象征物的颜色。确实,共产党的党旗和国民党颇具中国特色的青天白日旗在颜色上恰成比照。虽然张仃漫画画的是水灾和罢工(这是地下共产党最喜欢的题材),但张仃擅长的黑白色块,却使他的漫画太具有悲怆的气质,和红色所显透出的邀请语气、煽动性质和蓬勃激情大相径庭,也和纯正的红色所要求的战斗精神大相背离。张仃被革命的、火红的《漫画生活》拒绝,似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张仃的漫画的主色调不符合革命或者革命语义的要求。它们确实太灰暗了,尽管它们确实太真实了。鲁迅精辟地说过,真实是漫画的命脉,正如毛主席在几十年后正确地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样。鲁迅还说,正是因为真实,所以漫画才有力量。但力量作为一种观念产物(而不是自然物),在不同的人那里从来都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含义;力量希图达到的目标,在不同的人那里,也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想利用它改朝换代,有的人想借助它攻克碉堡,有的人不过是想仰仗它混一碗好饭,甚至是讨一房福晋。而革命的宗旨和远大理想首要的、初步的目标就是改朝换代。既然如此,革命从来就不需要悲观和悲怆。悲怆的力量不是革命的力量,甚至不是革命所需要、所特别倚重的力量。悲怆的力量只是革命的力量的“偏师”和补充。它的性质与革命的力量的性质,如果不是背道而驰的,起码也是有较大距离的。因此,《漫画生活》代表革命语义拒绝张仃的漫画,也就是相当有道理的了。
迫于严重的生计问题,在万般无奈之下,张仃只好将这些画投向了“资产阶级”的“右翼刊物”——著名漫画家张光宇先生主持的《上海漫画》。没想到很快就被重点采用了,而且两幅画都被制成彩色珂罗版。这件事情让张仃觉得太有幽默感了。直到几十年后接受笔者的采访时,已经年逾八旬的张仃还对此念念不忘,也禁不住轻微地摇头。他感到了不可思议。但他是否也感到了这件事对他的人生运程具有的某种提示?在采访中,我们没有问过他。
但这件事对于张仃却是一个重大的转机。正是著名漫画家张光宇和他主编的《上海漫画》,适时地接纳了和推出了一个新人,也是张光宇和《上海漫画》将小小年纪的张仃,推到了漫画家的位置上。这不仅一举解决了张仃的生计问题,还使张仃借助这个转机,把自己逐渐修炼成中国漫画史上——又岂止是漫画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重要的人物。
职业漫画家
张仃在1936年颇富戏剧性地一夜成名后,在漫画界一些前辈画家——比如张光宇等人——的帮助下,开始成为职业漫画家。他马不停蹄地为《扶轮日报》和《中国日报》画时事漫画,一方面发泄了心中的愤懑,另一方面,也为糊口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爱好的渠道。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重要收获,就是认识了后来的张夫人陈布文小姐。但张仃的职业漫画家生涯只持续了短短两年时间。迫使张仃中断职业漫画家生涯的原因是日本人的大举入侵,以及日本军队对南京(那是《扶轮日报》和《中国日报》的所在地)、上海(那是漫画家和漫画杂志最集中的地方)的占领。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两年内,不足二十岁的张仃以凝重的笔触,画出了一大批颇具影响力的漫画。《春劫》(1936年)、《玩偶大观》(1936年)、《看你横行到几时》(1936年)、《同志》(1937年)、《乞食》(1937年)、《休息》(1937年)、《野有饿殍》(1937年)、《日寇空袭平民区》(1937年)、《蹂躏得体无完肤》(1937年)、《战争病患者的末日》(1937年)、《兽行》(1937年)……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这些漫画中,“现实主义精神,单纯的写实加上强烈的夸张变形,黑白色块的对比浓重,冲击力极强。”(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第22页)这些漫画构思巧妙,形象独特、打眼,画面非常拥挤,颇有民间水陆画的风采,几乎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毫不犹豫地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视觉效应。但绝无丝毫快乐的成分,就更不用说有闲阶级愿意欣赏到的狂欢和具有搞笑性质的幽默感了。
黑白色块是世间最常见的颜色(假如白色能够被称为颜色),但也是互相“敌对”的颜色。它们都是颜色中的极端分子。将它们放在一块儿,对比也就分外强烈。张仃用这两种颜色作漫画,虽说是受了墨西哥画家维拉和珂弗罗皮斯的影响,也部分地接受了德国画家乔治·格罗斯和美国画家威廉·格罗拜的启示,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恰好在于:身处一个国破山河在的惨烈年代中的画家,尤其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忧心如焚的画家,似乎不大可能动用更鲜艳的色彩来描写现实,因为现实首先就是昏暗的、悲惨的、暗无天日的。虽然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但那是正在变黑、变暗、走向衰亡的太阳;虽然月亮每逢十五就圆,星星仍然在天际摆出一副天女散花的架势,但那是惨淡的、打上了悲惨时代中人浓墨心理底色的月亮和星光。它们在心理效应上几乎就等同于鬼火。因此,在张仃那里,颜色不仅具有视觉心理学上的意义,更具有视觉伦理学上的意义:该种伦理学要求一个真正的、诚实的、愿意凭着人性的基本要义介入现实的画家,真实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容不得一丁点粉饰。相对于惨烈的现实,五彩缤纷确实是不道德的。
张仃的漫画的这一特质,几十年后在他夫人陈布文先生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质朴的描述:“一般说来,观画应是一种欣赏,常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休息与享受。但是,看张仃漫画,却令人一下子回到黑暗时期的旧中国,感到异常的沉重与窒息。”这就是真实裹挟而来的力量,它能让人越过时间的长河,仍然感受到当时的暗无天日和惨淡无光。
虽然现实生活内容进入艺术的文本空间——哪怕它叫漫画,从来都有着多种渠道,但画家最终选择哪种具体渠道,则和画家本人的天性、禀赋和气质关系重大;虽然现实生活场景进入艺术空间需要多重转换,但怎样转换、按照何种方式转换,却需要画家的心灵进行过滤。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特殊的、精致的、对艺术有效的心理机制。那时张仃年轻、冲动、偏执、易怒,像几乎所有的同龄人一样(他还不足二十岁)。所以张仃在职业漫画家阶段所画的漫画,几乎每一幅画中的人物、场景、车轮、手势、步伐、面容、服饰、某些可诅咒的人士的獠牙甚至空气、阳光(假如它存在)、街道、土地……都充满了胀鼓鼓的力量,似乎要冲破画面直立行走。它们都是饱满、充沛、充盈的形象。在这些画面中,无论是被画家痛斥的对象(比如《看你横行到几时》中的日寇),还是被同情的对象(比如《野有饿殍》中饥饿的城市贫民、《休息》中在路边沉睡的黄包车车夫等),都是黑色的,都充满了胀鼓鼓的仇恨。甚至连懒洋洋的沉睡者(比如《休息》中的黄包车车夫)也肌肉僵硬,随时准备冲起来为生计赶路。但这首先是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情感亢奋的画家内心的仇恨:是画家面对现实所产生的巨大内心张力,使画面中的各色人等、各色场景、各式道路和各种线条都充满了力量。这不是一般的力量,而是愤怒的力量,悲怆的力量,同情的力量,痛苦的力量,仇恨的力量,但同时也是关于愤怒的力量,关于悲怆的力量,关于同情的力量,关于痛苦的力量,更是关于仇恨的力量,它是张仃向这个非人的、地狱般的世界投出的黑白交加的诅咒。这是真实的诅咒,但首先是因为现实比现实应该得到的诅咒更真实。正是因为真实,所以才拥有了穿透纸背的力道。
但这种力量在红色的、具有爆发力和冲击力的革命的力量眼中,也许只能算是革命的前奏力量,革命的准备力量。它是革命力量的萌芽。在这一点上,拒绝过张仃的左翼杂志《漫画生活》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愤怒的力量、悲怆的力量、同情的力量、痛苦的力量、仇恨的力量在其来源上,还只不过是对悲惨现实的真实观察和描摹,而反抗这种现实、改造这种现实的力量,还处在密谋状态、萌芽状态。它只是革命力量的胚胎。但并不是说这种胚胎状态所具有的力量就是无力的力量,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另一种力量而已。
张仃在漫画中大量使用黑色是正确的,也是相当准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黑色是最悲哀的颜色,几乎没有人在葬礼上穿大红大紫而要穿黑色的服饰,也许就不失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对视觉的心理效应进行过哲学论证的休谟和贝克莱,深知这中间的猫腻,我们在有空闲的时候也不妨向他们咨询。而张仃的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恰好是悲哀的中国。至少张仃在苏州反省院的狱友艾青,就是这样来描写他们的中国的。只不过艾青使用的是分行文字。但那仍然是黑色的分行文字——艾青在他的诗歌中就多次用“黑色”来指称中国和中国的土地、人民、山川、树木、独轮车甚至太阳。在艾青的诗中,这些事物一忽儿被冠以“黑色”的名号,一忽儿又被授之以“悲哀”的徽章。在这个重要的参照系下,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张仃使用黑色描述他眼中的中国、他的中国,确实是准确地对应了现实生活的悲惨境遇。
而黑色同时又是最痛苦的颜色,是最丰腴的颜色。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色彩的大家族中,或许只有黑色才能准确描写中国人最丰富的痛苦。这种痛苦的丰富性,按照古波斯诗人的话说就是:“论灾难,我们自有取之不尽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表达反抗现实的力量的密谋状态的黑色,完全对应了张仃作为艺术家的诚实、正义和良心。他对得起他赋予色彩的伦理学基因,因为他的漫画从骨头到面孔都是真实的。